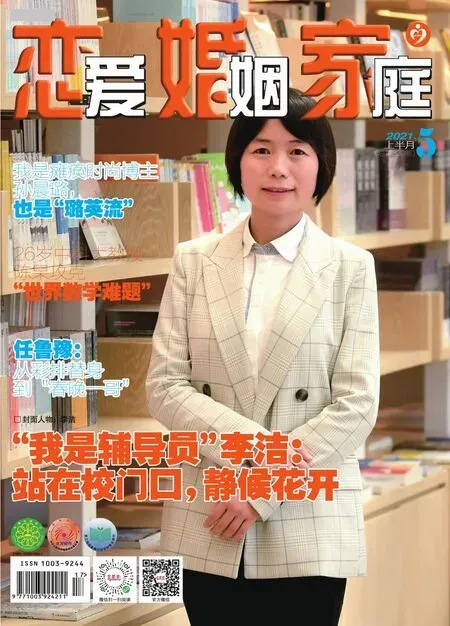『人民教育家』于漪:學(xué)生就是我的天下
●文/吳雪
她為自己準備了『兩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別人的優(yōu)點,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

本文主人公
自從走上教師崗位,于漪就從未離開過基礎(chǔ)教育的三尺講臺。她胸懷江河世界,渡人無數(shù),桃李萬千;她堅持教文育人,寫下數(shù)百萬字的教育著述,促進教育改革,將各種“不可能”變?yōu)榭赡堋?/p>
于漪獲得“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但她最喜歡的稱呼還是“老師”,她用一生踐行著“讓生命與使命同行”的誓言。
教師首先是個大寫的人
1929年,于漪出生于江蘇鎮(zhèn)江。在她8歲時,日本侵略者鐵蹄長驅(qū)直入,家鄉(xiāng)危在旦夕,于漪就讀的薛家巷小學(xué)即將解散。在最后一堂課上,音樂老師教同學(xué)們唱《蘇武牧羊》,喚起了于漪幼小心靈的愛國意識。連天炮火中,于漪輾轉(zhuǎn)考入鎮(zhèn)江中學(xué),在老師的悉心教導(dǎo)下,她深刻認識到求學(xué)的目的正是解救苦難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從愚昧走向文明。
于漪15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告訴她,做人是最重要的:第一要心地善良,這才叫人;第二要勤勞,自己吃點虧、吃點苦沒有什么大不了,只要力所能及都要幫助別人。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于漪的一生。她經(jīng)歷過坎坷,是教育給了她力量;在此后的歲月里,她又把這種力量,賦予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青年。
1947年,18歲的于漪考入復(fù)旦大學(xué)教育系。在大學(xué)里,曹孚、周予等教授嚴謹治學(xué)的品格和精神,深深地影響了她。大學(xué)畢業(yè)后,于漪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師范學(xué)校擔任語文老師。第一次登上講臺,她非常緊張。一課終了,教學(xué)組長徐老師說:“你雖然在教學(xué)上有許多優(yōu)點,不過語文教學(xué)的這扇大門在哪里,你還不知道呢。”
在后來的教學(xué)生涯中,于漪常常反躬自省:入門了沒有?用心了沒有?語文教學(xué)的大門,于漪一輩子都在尋找。從復(fù)旦第四宿舍到幾條馬路之遙的四平路,于漪走了整整34年。穿過忙碌的人潮、喧囂的市聲,她的腦海里卻上演著課堂上的一幕一幕。“每天早上走一刻鐘的路,就在腦子里過電影,這堂課怎么講,怎么開頭,怎么鋪展開來,怎樣形成高潮,怎樣結(jié)尾……”
于漪為自己準備了“兩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別人的優(yōu)點,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白天,她站在教室窗外,看別的教師怎么上課;晚上,對著參考書仔細琢磨。就這樣,精彩的思考成了她教學(xué)中的養(yǎng)分,缺點也慢慢被克服,教學(xué)育人漸入佳境。
1977年,電視里直播了一堂于漪執(zhí)教的語文課《海燕》,許多觀眾守在電視機前,爭睹她上課的風采。在語文教師們的眼里,于漪老師就是教育界的“明星”。就在那一年,于漪帶教過的77屆兩個畢業(yè)班,原本底子薄弱的學(xué)生們竟然在畢業(yè)時100%考取了大學(xué)。1978年,工作突出的于漪被評為全國首批特級教師。
于漪說:“教育的秘密在于從來不以分數(shù)評判學(xué)生,而是提倡‘教文育人’。”同年,報告文學(xué)《哥德巴赫猜想》發(fā)表,興奮的于漪找到學(xué)校的數(shù)學(xué)老師,說:“我們唱個‘雙簧’,你給學(xué)生講陳景潤的科學(xué)貢獻,我講陳景潤為科學(xué)獻身的精神。”在于漪看來,語文教育一方面要教會孩子理解運用語言文字,更重要的是建設(shè)其精神家園,塑造其靈魂。
學(xué)生就是我的天下
憑著超前的教育理念,于漪走上上海第二師范學(xué)校校長的崗位,進行大刀闊斧的顛覆性改革。她讓教師實行坐班制,學(xué)生一剪頭發(fā),二穿校服;抓兩代師德教育,規(guī)定社會上流行的,學(xué)校不一定都提倡;請盲人樂隊講述生活強者,請離休干部作革命傳統(tǒng)教育……
于漪對教育的初心不改,她柔弱的身體迸發(fā)出旺盛的生命力。她常說,“師愛超越親子之愛,學(xué)生就是我的天下。”她教過的學(xué)生,十幾年后再來看望她,還能把她在課堂上講過的話一字不差地背出來,有的還能記起當時她在黑板上的板書。
一位青年老師聽了很多節(jié)于漪的課,發(fā)現(xiàn)她每節(jié)課的內(nèi)容都不重復(fù),哪怕是一篇課文教第二遍、第三遍都不一樣。
于漪覺得,“我講你聽”的傳統(tǒng)教學(xué)應(yīng)改為網(wǎng)格式的互動教學(xué)。她認為學(xué)生是可變量,老師的任務(wù)正是用敏銳的眼光讓每個學(xué)生都成為發(fā)光體。上海市特級教師王偉,曾是于漪教過的學(xué)生,他說:“于老師教我的3年里,有許多個印象深刻的‘第一’。”
王偉記得在一堂公開課上,于漪給同學(xué)們布置了題目為“一件有趣的事”的練口作業(yè),他第一個舉手走上講臺演講馬戲團猴子爬桿,得了80分的高分,“這個80分給了我自信與勇氣。”每堂課前,于漪只布置一個任務(wù)——預(yù)習(xí)課文,認真朗讀,仔細閱讀,課堂上提出問題,最好能提出難住老師的問題。對王偉來說,這是對語文學(xué)習(xí)全新的認識顛覆。
“那時沒有網(wǎng)絡(luò)和參考書,同學(xué)們私下你追我趕,在一堂《變色龍》的公開課上,同學(xué)上臺板書后沒有波瀾,而于老師改完后全班掌聲雷動。”于漪總是在不動聲色中把學(xué)生的問題解決了。
教學(xué)工作之余,于漪利用課余時間學(xué)習(xí)教育理論。蘇聯(lián)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要使孩子的心同我講的話發(fā)生共鳴,我自身就需要同孩子的心弦對準音調(diào)。”每次讀到這句話,于漪就會想起自己一次難忘的教育經(jīng)歷。
于漪教過的一個女孩做操不認真,反復(fù)指導(dǎo)還不予理睬。情急之下,于漪竟然叫出了這名學(xué)生的外號,而她一直告誡學(xué)生不要以外號稱呼同學(xué),但是自己卻沒做到。事后,于漪真誠地向這個同學(xué)道歉,這份歉意來自她內(nèi)心深處對人性的尊重。
從教以來,于漪沒有罵過任何一個學(xué)生,沒有挖苦過任何一個學(xué)生。她認為:做老師,必須有寬廣的心懷,要包容各種各樣的學(xué)生,而這種包容不是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而是走到學(xué)生的心里,與他平起平坐,體會他的情感,體會他的想法。
一個男孩是班級里有名的調(diào)皮大王,甚至連他的父親對他都徹底失去了信心。男孩父親對于漪說氣話:“這個兒子我不要了!”于漪并沒有推托,而是把這個“爸爸不要”的孩子帶回了家。
“沒有愛就沒有教育,只有把真愛播撒到學(xué)生的心中,學(xué)生心中才有老師的位置。”于漪說,“要感動學(xué)生,首先要感動自己。”
一次家訪中,于漪看到學(xué)生一家五口,住在只有12平方米的破房子里,難過得流下了眼淚。在那個經(jīng)濟條件普遍不寬裕的年代,于漪把所有的積蓄都用在學(xué)生身上,對自己的孩子卻一再省儉,她的兒子黃肅直到28歲結(jié)婚前都沒穿過一雙皮鞋。
一輩子學(xué)做教師
到了耄耋之年,于漪開始研究起周杰倫和《還珠格格》。因為她發(fā)現(xiàn),孩子們都被新生代歌手和新的影視作品“圈粉”了,而自己喜歡的一些資深的歌手卻很難引起學(xué)生共鳴。有學(xué)生直言:“周杰倫的歌好就好在學(xué)不像。”
于漪找出學(xué)生喜歡周杰倫的兩個原因:《青花瓷》等歌詞是從古典名章中尋找靈感,借鑒了傳統(tǒng)文化元素,所以學(xué)生樂意親近;現(xiàn)代獨生子女無人傾訴,煩悶時哼哼周杰倫的說唱音樂是很好的宣泄。許多學(xué)生感覺被于老師理解了,師生老少笑作一團。于漪正是憑借對語文教育的精神追求,與學(xué)生共建一幢立意高遠的精神大廈,啟蒙一代代學(xué)生獨立思考、得體表達,成長為豐富有智慧的人。
有一年大年初二,媒體記者到于漪家采訪,一開門,滿屋子的學(xué)生十分熱鬧。跟年輕人在一起,為他們搭建成長平臺,是于漪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所有年輕教師來我家請我給他們的新書作序,我從不拒絕。現(xiàn)在的年輕人想要成長、要出頭不容易,我們要拉他們一把。”
于漪剛退休時,就有民辦學(xué)校開出60萬元年薪聘她作“特別顧問”,被她婉言謝絕。當時,于漪的退休金每月只有一千多元。談及為何將高薪拒之門外,于漪說:“我還有點本事,能夠培養(yǎng)師資,我?guī)Я藥状丶壗處煶鰜怼R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成為大家的墊腳石,我終生有幸。”
于漪首創(chuàng)“師徒帶教”模式——師傅帶徒弟、教研組集體培養(yǎng)、組長負責制,親自帶教全國各地的青年教師。于漪連續(xù)8年擔任上海市語文學(xué)科德育實訓(xùn)基地的主持人,培養(yǎng)遠郊區(qū)的年輕教師,每月一次8個小時的活動,她一場不落。
于漪80歲時,有一次活動在遠郊金山的華師大三附中舉行,大家都勸于老師不必親自到場,于漪卻不肯:“只要是我基地學(xué)員所在的學(xué)校,即使再遠,也不能落下。”
一大早,于漪準時來了,她坐了近兩個小時的面包車,腿腳浮腫,可一到華師大三附中,她就一頭扎進教室聽課。中午時分,她快速扒了兩口飯,撂下筷子趕去教室,和同學(xué)們見面。孩子們的問題像連珠炮似的,于漪對于孩子們的請求從來不會說“不”。
在于漪的精神感召下,一批批青年教師脫穎而出,形成了全國罕見的“特級教師”團隊,涌現(xiàn)出一批知名的教學(xué)能手。于漪既感慨又欣慰:“真的很累,但我覺得能把自己有限的經(jīng)驗,在別人身上開花結(jié)果,這就是一種幸福。”
在新教師培訓(xùn)中,于漪多次引用英國小說《月亮與六便士》:首先心中要有月亮,也就是理想信念,去真正敬畏專業(yè)、尊重孩子,還要有學(xué)識,如此才能看透“六個便士”,看透物質(zhì)的誘惑。“滿地都是便士,作為教師,必須抬頭看見月亮。”
要想走進學(xué)生的內(nèi)心,必須“一輩子學(xué)做教師”。于漪告訴青年教師,最重要的是在實踐中不斷攀登,這種攀登不只是教育技巧,更是人生態(tài)度、情感世界。
于漪的孫女黃音,如今也投身于教育事業(yè),在她幼時的記憶里,奶奶在做完家務(wù)之后,總是坐在臺燈旁,邊翻閱資料邊做筆記,沉醉其中。而不足3平方米的陽臺上,爺爺?shù)奶僖巍⒁槐緯⒁话巡鑹兀褪且粋€充滿了書香的下午。“從小到大,奶奶像一盞燈塔,指引著我。”
于漪家里有一本她專用的掛歷,掛歷上幾乎每一個日子都畫上了圈,不少格子里還不止一個圈。她用“來不及”形容自己的工作,因為有太多事情值得她“較真”,中國教育必須有自己的話語權(quán)。
當教育日趨功利化,家長忙于幫孩子報補習(xí)班,學(xué)校只盯著升學(xué)率的時候,于漪呼吁:“教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學(xué)生學(xué)會做人。”看到小學(xué)生寫下“祝你成為百萬富翁”“祝你成為總裁”的畢業(yè)贈言時,于漪深感憂心,“‘學(xué)生為誰而學(xué)、教師為誰而教’這個問題很少人追問,教育工作者應(yīng)該在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動機和動力方面多下點功夫。”
時光荏苒,2021年,于漪已是92歲高齡,從受業(yè)于師到授業(yè)于人,她從未離開過講臺。于漪說:“老師使我從無知到有知,從知之甚少到懂得做人的道理。做老師是件了不起的事,是我這輩子最崇高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