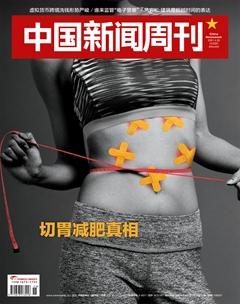抹不掉的東方底色
馬劍

瞭望臺欄桿上的愛情鎖。
5月底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依舊寒氣逼人,迷迷糊糊從機場大廳走出來,不得不急忙找出一件外套披上,此刻最重要的是早點到達市區喝上一杯熱咖啡暖暖身子。去往市區最早的一輛中巴已然停靠在了路邊,雖不懂站牌上的俄語,但跟隨著當地旅客的腳步,基本是不會有錯的。
之所以將符拉迪沃斯托克作為俄羅斯之旅的第一站,是因為這里是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最東端的起點,計劃從這里坐火車一路向西,開啟我的俄羅斯之行。
望著車窗外略顯荒蕪的平原與樹林,心情難免會變得有些復雜,這里既是異國他鄉,又好似故地重游,歷史雖早已定格,但民族的情感卻一時無法完全平復下來。
中巴的終點站便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車站,也是這座城市的中心。火車站始建于1912年,站臺上矗立著西伯利亞鐵路終點紀念碑,紀念碑上“9288”的字樣,是西伯利亞鐵路最初的里程,與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站臺上的西伯利亞鐵路起點紀念碑遙相呼應。
在站前廣場上的列寧像依舊矗立,十月革命勝利后,符拉迪沃斯托克仍屬于白軍的勢力范圍,直到1922年,這里才被列寧領導的蘇聯紅軍解放。此時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居民中一半以上仍是留在此地的華人,但在隨后的斯大林時期,生活在這里的華人和朝鮮人等東亞居民幾乎都被屠殺或遷徙殆盡,2009年當地工人修路時曾發現了大量華人的遺骸,如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區內已經很難再找到土生華人的后裔。
預訂的青年旅館距離火車站只有幾百米的距離,沿途街道兩側林立著高矮不一的樓房,大多帶有蘇聯時期的印記,它們夾雜在新建的高樓和已有幾百年歷史的俄式建筑之間,讓整座城市顯得既現代,又似乎無法擺脫曾經的歷史。

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街道。

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車站。

潛艇C-56號博物館內部。
阿文是我在青年旅館里認識的一名來自吉林的留學生,他特意為我制訂了兩日游的旅行計劃,并借給我一份旅游地圖。
阿文最推薦的是阿爾謝涅夫博物館,博物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90年,以俄羅斯探險家阿爾謝涅夫的名字命名,號稱是俄遠東地區最大的博物館,其實不過就是臨街的三層小洋樓。一層展廳里擺放的文物基本都是明清時期的遺物,聽阿文講,這些石碑中有兩塊是明朝時期的永寧寺石碑,看來俄國人對于這片土地原有的主人并不諱言。
藏品中數量最多的要數濱海邊疆區的動植物標本。這些動植物標本與中國東北的動植物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我甚至還看到了一只東北虎標本。
對于俄國人而言,他們更愿意展示自己引以為傲的軍事力量。潛艇C-56號博物館位于 “太平洋艦隊的戰斗榮譽紀念碑”廣場,這艘長77米、寬5米的潛艇,代表了當年蘇聯海軍的輝煌。“二戰”中,這艘潛水艇共擊沉敵艦10艘,重創4艘。功成身退后,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潛艇的前半段被裝修成陳列室,陳列著不少潛艇資料、“二戰”時期的軍服、徽章等,后半段才是潛艇原有的樣子。控制室有密密麻麻的儀表和管道,軍官休息室里面還掛著斯大林的肖像。船艙的尾部是船員休息艙,同時也是魚雷發射艙,十幾張船員的吊床,與魚雷并排在一起,很難想象在這樣環境下,船員們一待便是幾個月。在潛艇博物館后面有一排紀念碑,上面刻著那些死于戰爭士兵的名字。
紀念碑旁有一座不大的東正教堂,它是1907年為了紀念日俄戰爭時期犧牲的俄羅斯戰士而建的,當地虔誠的東正教教徒來到這座教堂做禮拜時,也不忘為一旁紀念碑上名字默默祈禱。大概是近年來到這里的中國游客太多的緣故,教堂大門上還有中文提示:“根據宗教規定,女士進入教堂需戴頭巾,請各位女游客入鄉隨俗。”
這是一座遍布教堂與雕像的城市,幾乎每走幾分鐘就能看到一座教堂或是一尊雕像。鄰近傍晚,一處隱藏在樹叢背后的教堂里正在舉行著一場小型的音樂會,彈鋼琴的是一位少年,聽眾中既有他的親友,也有像我這般的路人,大家西裝革履或坐或站,認真聆聽少年的琴聲。這些年俄羅斯的經濟大不如前,但人們的藝術素養水準依舊。
第二天,按照阿文的規劃前往鷲巢瞭望臺,這里是俯瞰整個海灣的最佳地點。去瞭望臺最好是先乘坐一段極富當地特色的索道纜車,但海港城市高低起伏的山路,猶如山城重慶,即便有手機導航也讓人辨不清方向。正躊躇時,迎面走來一位五六十歲的大媽,一手提著包裹,一手抱著一幅油畫。大媽聽不懂英語,我倆幾番對話好似雞同鴨講。
眼見大媽的神情逐漸急躁,我心想還是不要為難她了,沒想到大媽拍了怕我的肩膀,示意讓我跟著她,她掉頭向反方向走去,一路上兩人無話,大約走了二十分鐘,才走到我要去的纜車索道入口處。我連忙道謝,也不知道她是否能聽懂,大媽像是松了一口氣,又提著沉重的包裹和油畫原路返回。我猜她年輕時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纜車陳舊的車廂,機械式的爬升,讓人有時光倒流的錯覺。到達山頂后,又經過一段通道,就來到了瞭望臺。俯視海灣,整個金角灣大橋盡收眼底。當年俄羅斯政府花費數十億美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設這座大橋是為了迎接2012年的APEC會議,向世人展示了俄羅斯的遠東風采。
符拉迪沃斯托克距離俄羅斯本土太遠,這里的經濟發展緩慢,直到西伯利亞的鐵路貫通,才迎來一次快速發展機遇。如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正在試圖弱化自己的軍事色彩,而是更多展示出它的經濟魅力。
瞭望臺的身后聳立著圣西里爾和圣默多狄的雕像,兩兄弟一人拿著書本,另一個人高舉著十字架,正是他倆將基督教傳入到斯拉夫民族地區,并且為了將《圣經》翻譯成當地語言而發明了“西里爾字母”,并成為了現代俄語的重要起源。這個彪悍的民族在宗教中找到了平和的一面,但來自西伯利亞嚴酷的冷風,又讓這里的人們不得不變得強悍起來,看似矛盾的性格,似乎又是如此自然而然。
這座城市的年輕人,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愛情才是他們關心的。觀景臺的柵欄上,扣了無數象征愛情的鎖。阿文告訴我,他的俄羅斯同學,父輩們大多不是本地人,而是來自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家屬,又或是蘇聯時期從烏克蘭等地而來的移民。
即將離開時,我將地圖還給了阿文。“你知道嗎,這張當地出版的地圖上仍能看到中國的地名,類似一道河子、二道河子,這些地名在我們東北十分常見。” 阿文對我說道。
確實,符拉迪沃斯托克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個典型的歐洲城市,走在街頭你總可以感受到它的東方味道,路邊常會見到的中文、韓文廣告牌,城里到處都是中餐廳、日本餐廳,街道上更是隨時可能遇到來自東亞各國的留學生、打工者和游客,無不散發著東方的氣息,或許就是這里永遠無法抹掉的東方底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