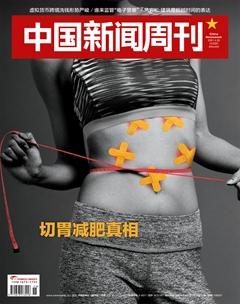觸不到的老師

波波夫
1998年,珍尼特·沃斯的《學(xué)習(xí)的革命》在中國出版,一時洛陽紙貴。那時,在老師和家長看來,電腦、網(wǎng)吧等同于孩子學(xué)習(xí)的敵人。不過,這位生于荷蘭、求學(xué)于美國的教育學(xué)博士在書中總結(jié)“創(chuàng)造世界上最佳教育體制所必需的13個步驟”時,旗幟鮮明地列出了兩個基礎(chǔ)性的步驟:“電子通訊的作用”和“每個人必須通曉電腦”。
珍尼特預(yù)言非虛,二十多年后信息技術(shù)掀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學(xué)習(xí)的革命”。今天,互聯(lián)網(wǎng)和計算機早已成為教育系統(tǒng)的重要基礎(chǔ),教室里處處閃爍著技術(shù)的“智慧”,老師們拋卻粉筆和黑板,取而代之展示的是ppt和激光筆,以及游走在屏幕和學(xué)生之間的注意力。學(xué)校之外,許多課程知識甚至可以通過各類免費公開課獲得,學(xué)校和老師不再是唯一主要的知識傳授者。
當(dāng)人們把越來越多時間投入到線上世界時,教育也亦步亦趨。去年新冠疫情最嚴(yán)重時,大部分學(xué)校都改為線上教學(xué)。而早在疫情之前,涵蓋小初高的K12階段的學(xué)科課外教學(xué)輔導(dǎo)便發(fā)軔于云端,10后的孩子們,人生的第一堂課大都是從方寸屏幕開始的,人生的第一所學(xué)校往往是網(wǎng)校,人生的第一個老師出現(xiàn)在屏幕中,云教育變得司空見慣。
人們有時也會陷入對技術(shù)的過度迷信,甚至有的學(xué)校還在教室中引入攝像頭,依靠圖像識別、機器學(xué)習(xí)來幫助老師發(fā)現(xiàn)哪些孩子上課打盹兒走神了,但是當(dāng)不知疲倦的硅基技術(shù)遭遇靈動的碳基生命時,往往忽略了人類一些固有的生理特點——比如我們的注意力無法持續(xù)數(shù)小時集中,從而最終走向它的反面。
一如并非所有尖端科技都適用于學(xué)校,青春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模糊和秘密,以消納成長的顛簸。完全在線教育讓人們懷念學(xué)校的魅力,教室不僅僅是灌輸知識的場所,更是未成年人完成社會化的溫床;學(xué)生們不僅需學(xué)習(xí)知識,他們還需要結(jié)識朋友、收獲友誼、建立“三觀”;老師固然無法像谷歌百度那樣“無所不通”快速響應(yīng),但在解惑之外,他還承擔(dān)著傳道授業(yè)的社會職能。但凡你輔導(dǎo)過孩子在線上課,你就不會同意斯坦福大學(xué)計算機教授塞巴斯蒂安·特倫的著名論斷:“一位老師,一個攝像頭,一個能上網(wǎng)的電腦,就可以教育整個世界。”他真的太樂觀了。
互聯(lián)網(wǎng)改變了很多,最明顯的是顯著提升了信息傳遞的效率、熨平了地理和時空的落差,在大城市的家長們習(xí)慣了在微信群里接收學(xué)校同步的各類通知,學(xué)生們企圖隱藏一份考砸了試卷的難度越來越大,學(xué)校和家庭之間關(guān)于學(xué)生信息的鴻溝正在縮窄,但互聯(lián)網(wǎng)也有許多未盡之事,一道寬闊的教育鴻溝——始終橫亙在城鄉(xiāng)之間、學(xué)校之間。
人們也在利用技術(shù)去破解教育不公,但是否把名校課堂在鄉(xiāng)村學(xué)校同步直播,就意味著貧困山區(qū)的學(xué)生可以考出和北上廣名校生同樣亮眼的分?jǐn)?shù)?各大視頻網(wǎng)站上海量的優(yōu)質(zhì)免費課程是否就意味著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的唾手可得?三歲學(xué)英文、五歲練編程、小學(xué)考雅思,這是贏在起跑線搶跑還是拔苗助長?
通往公平之路比想象的更為崎嶇不平。人類學(xué)家項飆用“內(nèi)卷”一次來形容當(dāng)下教育競爭的慘烈,同時但凡對內(nèi)卷一詞起源略有所知的人,也能從中會意出內(nèi)卷對“雞娃”模式終局的悲涼預(yù)言。技術(shù)是中性的,但愿能夠幫助孩子們走出內(nèi)卷,平撫家長的焦慮,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