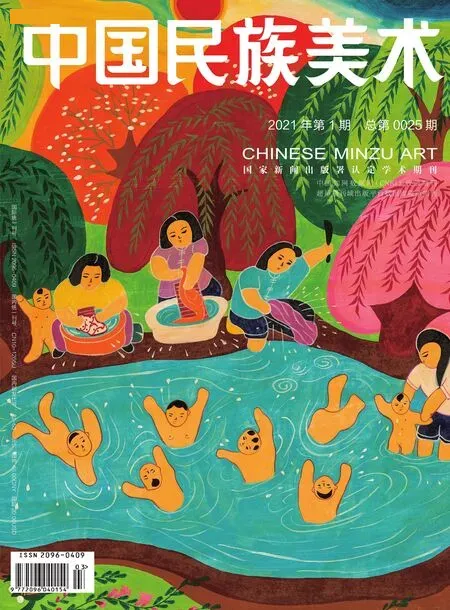到生活中起草稿
——探析黃胄赴新疆民族地區寫生的時代背景
文:崔名芳 中國國家博物館 / 圖:黃胄美術基金會

1979年8月,黃胄、鄭聞慧夫婦倆帶著女兒梁纓在新疆吐魯番寫生
引言
自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成為黨的文藝工作方針以來,民族題材美術創作引起廣大美術工作者的關注,加之政府加大了針對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扶持,民族地區的經濟、交通、生活條件日益得以改善,也使得畫家們能夠到達邊疆民族地區進行采風、寫生。藝術地表現民族地區人民的新生活、新面貌,以及展現獨特的民族風情成為一種潮流,也先后涌現出了一批致力于民族題材美術創作的畫家,黃胄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多次奔赴新疆,在行走中沿途寫生,做生活的速寫,深入民族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空間,積累了大量的寫生、速寫資料和經驗,使得他憑借以速寫入畫在20世紀中國人物畫的發展中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也奠定了他在20世紀中國民族題材美術創作中的歷史地位。

載歌行(趕集圖) 黃胄 中國畫 尺寸不詳 1959 年
一、黃胄奔赴新疆寫生的經歷
黃胄本來是在趙望云的指導下,以黃泛區寫生為代表的描寫人民悲劇生活的藝術家。由于時代的變化,50年代起又成為新生活的歌手,走向藝術創作鼎盛期,完成了個性的塑造,其中新疆生活圖畫又成為他的代表性藝術符號。因此,黃胄與新疆的關系便成為黃胄個案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一個側面。[1]
據《黃胄大事簡記》[2],黃胄五次赴新疆旅行寫生,而正文里記載著是六次,只是表述方式不同:
1947年,隨趙望云到甘肅、新疆等地旅行寫生;
1949年,經常到甘肅、陜西、青海、新疆部隊中采訪速寫;
1953年,隨中央慰問團解放軍代表團到新疆、青海地區,畫了大量速寫;
1956年秋,第三次去新疆北疆和南疆采訪速寫;
1963年,第四次去新疆訪問寫生;
1979年8月29日出醫院后,即赴新疆做第五次訪問。
也許編者沒有把1949年赴新疆部隊作為新疆之行,才有了五次新疆行之說。實際上,1986年他還曾到新疆短期旅行,計七下新疆,而到其他省區寫生大體在一至三次。[3]但無論如何,在黃胄藝術生涯中,有個深摯的“新疆情結”。他渴盼新疆如癡,1979年患脊椎綜合癥住院期間,他得到汪鋒的邀請,即向大夫報告:“你們用心給我治了兩年半,就是為了叫我畫畫。我離開生活這么久了,應該去補!”大夫會診后讓黃胄猜是否同意,他說:“當然通過!”這一次,一去就是七個月。

1979年在新疆寫生
在黃胄的上萬件速寫中,新疆速寫所占比例非常多,僅1956年于和田的六個月速寫即近千幅。在他的水墨畫作品中,新疆題材當在半數之上,如果把畫驢包括在內,比例當更大。如果以上都難以精確統計[4],眾多代表作取材于新疆的百姓生活卻是實實在在的論據:《豐樂圖》(1957)《趕集》(1959)《慶豐收》(1959)《維吾爾舞》(1961)《巡邏圖》(1962)《哈薩克少女》(1962)《上學》(1962)《塔里木之歌》(1962)《放牧》(1962)《載歌行》(1962)《庫爾班吐魯木》(1976)《百驢圖》(1981)《塔吉克舞》(1980)《育羔圖》(1981)《叼羊圖》(1983)《草原逐戲》(1986)……黃胄說他的藝術是在生活中鬧出來的,“遠離生活,失去對生活的激情,作品肯定失去光彩”。新疆無疑是黃胄最主要的生活根據地,是他夢魂牽繞的藝術故鄉;新疆人是他代表性的藝術符號,新疆的小毛驢是他藝術園里的寵物;新疆的節奏、新疆的色彩最與其性情相諧,是形成黃胄藝術風格最重要的客觀條件。正是在這諸多意義上,新疆在黃胄的藝術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說沒有新疆就沒有黃胄,或者說只能有一位別樣的黃胄。[5]
二、不同歷史時期的寫生緣由
(一)20世紀三四十年代赴新疆寫生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有一大批著名畫家走向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啟了他們藝術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這一現象在20世紀美術史上被概括為“走向西部”。黃胄正是在這個時期隨韓樂然徒步旅行八百里秦川,拜趙望云為師遠赴青海祁連山和新疆少數民族地區寫生。[6]當時多數西行藝術家的目的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以考察、研究和保護西部藝術為主并兼之臨摹學習歷代洞窟壁畫以滋養畫藝的藝術家,如張大千、常書鴻、王子云(以研究雕塑為主)等人,以及他們的學生何海霞、孫宗慰、董希文、張琳英、張民權、李浴、蘇瑩輝、周紹森、烏密風、龔祥禮、段文杰等。二是以考察石窟藝術和邊疆寫生兼重的藝術家,如趙望云、關山月、張振鐸、韓樂然、潘絜茲等。三是以沿途的風情寫生為重的藝術家,如司徒喬、沈逸千、吳作人、關良等。此外還有很多藝術家西行辦學或從事文化藝術方面的相關工作,如呂斯百、洪毅然、劉文清、張階平等。[7]
黃胄的藝術生涯正是起步于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藝術家西遷這一歷史背景中。他從1933年離開故鄉河北起就一直生活在西部,直到1955年東遷北京。他在西部歷經20世紀的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為成長為一個大畫家打下基礎。可以看出,黃胄在這一時期的寫生創作是積極主動地順應時代需求,他積累的寫生速寫為日后的新疆題材創作提供了重要素材。
(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疆之行
在深入生活寫生方面,五六十年代的歷史背景與三四十年代卻是差別很大的。之前是主動地積極地順應時代需求,而后是被動地完成任務。1950年《人民美術》創刊號《為表現新中國而努力(代發刊詞)》提到:“當前擺在美術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宣傳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政治綱領。這種宣傳不是抽象的條文的解釋;必須通過生動的形象。因此,美術工作者必須全身心地投入綱領之體現過程中間,去體驗去把握嶄新的形象、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如果自己思想感情還阻礙自己成為新人,那么必須改造自己。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參加新中國建設的革命美術工作者。……必須無條件地參加到工廠、農村、兵營,和群眾在一起……要從新的社會生活中……新作品的主題,要從新的社會生活中選取典型性的事件和人物做題材(英雄模范及其業績等等)……只要能夠啟發鼓舞、教育群眾的建設新中國之積極性,能夠使群眾更團結更堅定更樂觀更勇敢,能夠有益于建設新中國的事業,都可以是而且應該是我們取材的對象。”[8]

慶豐收 黃胄 中國畫 尺寸不詳 1976 年

新疆舞 黃胄 中國畫 尺寸不詳 1985 年
黃胄一生中所畫的速寫數量龐大,其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疆少數民族人物寫生占比很大。鄭聞慧女士的回憶錄中寫道:“黃胄1955年在西藏拉薩、日喀則畫了很多速寫,但在路上丟失了。”[9]黃胄在談到他的速寫稿時,他說:“速寫,一方面是畫家的基本功,另一方面它也是畫家的資料積累。從1949年參軍到1967年,我畫下來一萬多張速寫,現在只留下很可憐的一部分。個人的損失無所謂,我這雙手還在,今后我會加倍補償。但是,作為一個畫家來說,積累下來的資料給毀掉了,那還是很可痛心的。”[10]
1949年成為很多藝術家的轉折點,人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憧憬與向往,自然地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積極向上的新景象。歌頌新社會、新人物成為文藝界的主流。他們籠罩在革命主義與奉獻主義精神的宣講中,因而看問題的角度是積極向上、健康樂觀的,思考問題的方式也是極為簡單、淺顯的。這樣的藝術觀同樣貫穿于黃胄的藝術創作中,尤其在人物畫創作、大幅歷史性繪畫創作中更為突出。[11]

少女 黃胄 炭筆速寫 1979 年

草原逐戲 黃胄 中國畫 118.5cm x 370cm 1986 年
目前的畫冊中,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黃胄作品集》(全五卷)是黃胄作品中,由官方藝術機構收藏的最全面的畫冊,收錄速寫作品六十余張。這些以新疆民族生活為主題的速寫作品中,包含少數民族人物肖像、民族歌舞、兒童題材和生產勞動的題材。作品《織毯》(1963年)《師徒》(1963年)《老銅匠》(1963年)等是表現新疆民族勞作的題材。在勞動的題材中,出現了駱駝、毛驢、狗這些新疆地區常見的動物,它們與當地民族的生活生產有著密切的關系。速寫《傳藝》(1963年),畫家在作品下方標注“1963年2月于喀什葛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民族小刀車間”。畫面上一位車間師傅在打制刀具,徒弟在一旁仔細觀察學藝。另一幅作品《花帽刺繡合作社》,“一九六三年二月黃胄寫于喀什花帽刺繡合作社”。還有幾幅是新疆少數民族的人像,《帕夏》(1956年)《鐵匠艾撤》(1962年)《巴扎上的老人》(1962年)《維族少婦》(1963年)。關于新疆民族兒童主題,如《一年級小學生》(1963年)《祖國花朵》(1963年)。[12]
(三)20世紀80年代再次新疆之行
改革開放后,社會不再只需要依托少數民族題材高揚現實主義頌歌的作品,從寫實到表現,少數民族題材的美術創作呈現多元化發展。少數民族題材中的典型性和特有的審美規律退居其次,人們更在意的是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以及少數民族的民間美術與藝術傳統的關系。[13]
黃胄對新疆有著深深的熱愛,1979年,他的病情剛有所好轉,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新疆。患脊椎綜合癥住院期間,他得到汪鋒的邀請,即向大夫報告:“你們用心給我治了兩年半,就是為了叫我畫畫。我離開生活這么久了,應該去補!”大夫通過了他的申請。這一次,一去就是七個月。這個歷史階段的創作寫生,是第七次新疆之行,迎來了黃胄藝術生涯的第二個高峰。這一時期的藝術創作,不再是文藝創作服務于政治,去除掉了命令性質的寫生任務,黃胄作品發生了變化,描繪的對象更加生活化,不再是主題性繪畫創作,改變了簡單地記錄生活,更側重于藝術的表現,使筆下的人物傳神達意。這一改變體現在他80年代的許多經典之作中。

阿娜爾汗 黃胄 炭筆速寫 1979年

塔吉克獵人 黃胄 炭筆速寫 1979年

民間工藝師 黃胄 炭筆速寫 1979年
《叼羊圖》(1983年)《草原逐戲》(1986年)《好客的塔吉克人》(1979年)《牧場》(1979年)《氈房外》(1979年)《帕米爾之舞》(1988年)都是黃胄20世紀80年代的經典之作。黃胄在塔什庫爾干采訪期間,一個星期日,大隊里有一對青年要舉行婚禮,黃胄一行早早就到了新郎家,周圍十里八鄉的大人小孩都圍到新郎家帳篷外等著看熱鬧,新郎去新娘家迎親了,年長的到氈房內看望黃胄,年幼的已經在寬廣的平地上吹起鷹笛,男女青年模仿在天空翱翔的雄鷹翩翩起舞,那高昂的笛聲把聯歡推到高峰,黃胄快速地把這一幕幕激動人心的情景以速寫的形式記錄下來,給以后創作《鷹笛圖》《山鷹圖》《好客的塔吉克人》打下了主體創作的基礎。[14]
三、代言民族美,為時代立像

育羔圖 黃胄 中國畫 尺寸不詳 1981 年
有學者指出:討論黃胄先生的時候,可能經常會局限于美術史的范圍,僅僅談我們的畫家、我們的中國畫,但事實上黃胄藝術的出現,離不開20世紀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20世紀在一些西方的考古學家和邊疆學派的影響之下,中國各個學科的學者包括自然學科、社會學科、人文學科的學者,持續一個世紀的連續不斷的對于中國邊疆的考察和發現。在這個發現邊疆的運動過程中,有一些美術家、一些美術史家也在不同的階段紛紛地卷入到了這個發現邊疆運動中去。因此,中國20世紀的美術史有非常重要的一條主線,就是發現邊疆之美、表現邊疆之美。[15]
黃胄的藝術生涯歷經七次新疆之行,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歷史變革時期,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現代美術史上首次考察、關注和表現西部的熱潮,黃胄隨眾多畫家“西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政治任務與文藝相結合背景下的創作,黃胄創作大型的歷史性題材繪畫增多;到改革開放之后,黃胄描繪的對象更加生活化,以寫實為基礎,表達畫家主觀感情的寫意成為畫面的主導。
可以說,黃胄藝術觀的形成受20世紀初的社會及政治的影響,以題材和內容為重,這樣的藝術觀影響了他一生的藝術創作,通過對社會生活的觀察體驗,提高自己的技法。他是少數民族美的代言人,是時代造就的一位偉大畫家。
注釋
[1]劉曦林.黃胄與新疆[M]//黃胄研究.炎黃藝術館學術叢書.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9:185-194.
[2]鄭聞慧.黃胄作品集1986-1997(5)[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27-233.
[3]“1954年12月,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線通車,黃胄奉命隨慰問團到拉薩去體驗生活,并參加通車典禮。他在零下40度的氣溫下,不停地寫生,手指都凍壞了。黃胄在1982年和蘭州美術工作者座談時曾說:“我到西藏去過兩次,一次是給我補了一個警衛員的名額,一次是重新當兵,兩次都沒有好好生活和畫畫,我把一些機會給丟失了。”其實,他在拉薩、日喀則等地畫了大量速寫,不幸在卡車上被大風吹跑了,丟失了很多好的創作素材,但他還是根據自己的切身感受,創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并開始構思《洪荒風雪》,那是他在青海格爾木荒原上特別深刻的一次生活感受。”李松.黃胄[J].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9.
[4]本文以《黃胄全集》作為研究的主要依據,畫冊中新疆題材的速寫不多,但是從鄭聞慧女先生的回憶錄《回憶我的丈夫黃胄》中得知他的很多速寫作品在文革中被燒毀。
[5][12][14]崔名芳.黃胄新疆少數民族題材繪畫的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3.
[6]宋曉霞.黃胄與20世紀少數民族題材美術創作[J].美術,2019,(02):88。
[7]成佩.黃胄研究[D].中央美術學院,2012.
[8]為表現新中國而努力(代發刊詞).人民美術(創刊號),1950:15.
[9]鄭聞慧.回憶我的丈夫黃胄[M].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8:19.
[10]黃苗子.速寫生活技法—記黃胄的創作經驗[J].黃胄研究.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9:11.
[11][13]趙明.黃胄與傳統[D].中國藝術研究院,2012.
[15]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20世紀中國美術名家系列展—潘天壽藝術、李可染藝術、黃胄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王魯湘的發言,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