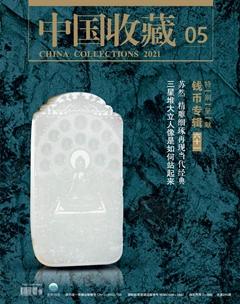在繁與簡中行走的玉雕人
趙玉國

楊光中國玉石雕刻大師
“叮咚!”
“來了。”
從房間里傳來的聲音有些沙啞,但回應的兩個字卻能聽出那是正宗的江淮腔。房門被打開后,煙草味撲面而來,一個健碩的身影隨即出現在記者眼前。
“你好。”他將夾著香煙的左手藏在身后,邊伸出右手,邊微笑地寒暄道:“ 抱歉,煙味是不是太重了?”
那只手看上去粗糙、厚重,但當與他雙手緊握時,觸覺的反饋卻是細膩、溫潤與爽滑的。
“美玉摸多了,手也被滋養得如玉一般。”不得不說,這個解釋恰當而巧妙。外表憨厚、樸實的他,于只言片語中閃出的是無限的靈光。
他就是楊光,在玉雕行業摸爬滾打30余年,以制作器皿見長。身為中國玉石雕刻大師、揚州玉器非物質文化傳承人的他,不僅擁有著過人的本領和非凡的經歷,而且對玉雕一藝有著深刻的感情和獨到的見解。

聰慧少年
1970年,楊光出生在江蘇揚州的鄉下。他說自己后來會從事玉雕創作,可能是從父親那里遺傳了一些基因。“父親喜歡寫字、畫畫,我受他影響,在還沒上幼兒園時就會照著墻上的標語口號畫字,還喜歡拿著鉛筆在紙上涂鴉。”
幼年時期萌發的興趣卻決定了楊光一生的命運。1986年,揚州市玉器學校首次面向農村招生。16歲的他憑借自學的美術基礎成功被學校錄取,開始接受為期三年的專業訓練。
而在繪畫上的天賦與靈性,使楊光得到了老師的特別關照。“當時教繪畫的倪紅英老師覺得我在繪畫方面會有前途,主動跟校領導說應該對我進行重點培養,并且她還利用休息時間加班帶我畫畫。”
在校第二年開始接觸玉器制作的楊光,也得到了玉雕老師的關注。切料、刻章、做小水盂,一步步由簡入繁,每個細節的要領都被他牢記于心。他也從這時候起,對玉器生發了自己的認知:“想讓一件器物有靈魂,必須加入自己的想法。”這或許是他后來在創作中不落俗套、新意迭出的根源。
瞬間之美
雖說小小年紀就顯露出一股子聰明伶俐的勁兒,但楊光卻并不覺得這是天生的資質好。“如果說天生,倒不如說我們農村的孩子動手能力更強、更刻苦,并且對于各種動植物的觀察力更敏銳。”
1989年,從玉器學校畢業的楊光被分配到揚州玉器廠爐瓶車間。“在廠里做了一段時間器皿后,領導覺得我有天賦,想拓展我的創作路徑,就把我推薦給了花鳥車間的劉筱華大師做徒弟。”
劉筱華大師1964年進入揚州玉器廠,師從“爐瓶醫生”朱邦元學藝,在爐瓶和花鳥方面均有豐富的創作經驗。其1984年設計的特大白玉“五行塔”是我國玉器工藝品中不可復得的珍品,現藏于中國工藝美術館。1986年,由他創作設計的白玉內鏈雙瓶為鏈條瓶雕琢技藝的發展做了一次新嘗試,此作后被著名當代玉器收藏家呂亞芳收藏。能得到這樣的名師指點,對于楊光來說如魚得水。“師父在花鳥上很有造詣,對爐瓶制作工藝不僅爐火純青,也有獨到見解。在他的指導下,我在這兩門技藝上都有很大進步。”
師父經常教楊光什么樣的花卉在什么時候最美,如菊花的美不在于待放與怒放之時,而微殘之際的姿態才最動人。他從師父那里學會的不僅是技藝,更多則是思考和觀察的方法。
加上從小在農村生活的經歷,讓楊光在創作時多了許多解決難題的辦法。“為了觀察各種昆蟲的動作,我捉來昆蟲先釘住一條腿,它抬起哪條腿我就粘哪條腿,看它走一步我就粘一步。后來,我做成了一套活體昆蟲標本。正因為這種細致的觀察,使我在玉器上塑造昆蟲時顯得更加鮮活、生動和逼真。”他說這就像拍照,擺拍始終沒有運動中途拍下的鏡頭美。而就是這樣的細心與刻苦,讓他等來了賺“第一桶金”的機會。
1990年,有港商進來與揚州玉器廠合作,楊光因一年來的出色表現,也被挑選過去。“那時候,我為了做一件翡翠白菜,每天去菜田里觀察、描摹。如果白菜只按照白菜的樣子去做其實是不好看的。我刻畫怒放的白菜,吸收了生菜的形象,這樣顯得更有力度、更加立體。”這件翡翠白菜做了6個月,他拿到了4萬元報酬,當時的工資則是每月2 0 0元。也因為這件翡翠白菜,他被港商負責人選中去深圳發展。

大器不繁
在深圳打拼數年后,楊光覺得做玉器還是要回到揚州,那里的氛圍和土壤更適于創作。1999年,回到揚州的他與師兄高毅進合作開辦了陽光玉器廠,后來又創辦了屬于自己的玉雕工作室。這時候,他在玉器創作技法和思想層面已臻成熟,開始大刀闊斧地去實現自己的創作理想。
花卉器皿,這是楊光一直潛心研究的器物類型。“過去在玉器廠花鳥車間也做器皿,但以花卉為主,老師傅要求花卉要飽滿,器皿往往被隱藏起來,因為要考慮器型不能與器皿車間有沖突。后來我覺得將器皿做大、花卉為陪襯,從整體上看更為靈動與活潑。”他認為,既然是器物,最好大大方方地將器型呈現出來,花卉、昆蟲等作為點綴更能從視覺上讓欣賞者分出主次,這猶如繪畫中對構圖的講究。這樣的器物既凸顯了莊重、肅穆的一面,也不失動感,繼而達到動靜結合的效果。他創作的金玉滿堂瓶、子孫匜、花開富貴瓶、四季平安瓶等都遵循了這種設計理念,這種風格已經成為他在玉雕界的標簽。
“玉有自己的語言,未進行雕琢的玉已經很美了,雕琢越多失敗的概率越大。”楊光始終主張“做玉器不一定要繁復”,他覺得如果材料很好,就盡量不要費工。在他看來,玉雕師是玉的醫生,它有瑕疵我們就來“治療”,如果完美無瑕就不要去“傷害”它。
“何為繁,何為簡,何為恰到好處?玉本身就是素的,我們為何要挖空心思去改變這種素?如果一位玉雕師能想明白這個道理,在雕琢它時可能就會更加從容。”這也許就是楊光多年來的從業“心經”。
小而可用
大器求簡,是楊光多年來悟得的創作思路。而在制作小器物時,他追求的則是“精”與“活”。
2017年,一件可握于手掌的活環沉香爐入藏大英博物館,被陳列在該館Alleyne玉器館。這也是該館首次收藏中國當代玉雕藝術家作品,而它的作者就是楊光。
為什么這件小器物能受到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大英博物館的青睞?該作選用俄羅斯碧玉,玉質細膩油潤、光瀅剔透、不含雜質。其整體造型圓潤飽滿,玩于掌心時手感舒暢順滑。而單憑這樣的材質與造型就能被大英博物館選中嗎?
楊光道出了其中的玄機:“我在爐蓋上加了一些工業設計理念,做了精巧的螺紋子母口和細密的螺圈紋工藝,再配上橡膠墊圈。在其擰緊后嚴絲合縫,儲放沉香粉或者香水精油等均不會溢出,這種設計突出了實用性與便攜性。”
可玩、可賞、可用,這是楊光做小器皿追求的三個要點。當玉器把玩件在市場上流行的時候,他就開始思考如何將器皿也做成可把玩并且能隨身攜帶的物件。“做把玩器皿不是簡單地將大器物做小,而是要考慮多方面因素。首先,握在手中時要與手型充分結合,不能產生不舒適感。其次,不可單純地為了追求圓潤、手感而失去造型之美。最后,既然要達到實用與便攜的目的,就必須解決顛簸后瓶內物泄漏的問題。”
正因為這樣的設計理念,讓一件“小物件”走進了世界最高藝術品殿堂,而這是楊光經過幾年摸索才研發成型的。現在,他的把玩器皿開發了香、茶、禪等多個系列,并不斷在迭代更新。他說:“ 如果現在還去開發鼻煙壺這類已經失去實用功能的物件,怎么能迎合現代人的使用需求呢?只有具備時代性的器物,才能在當下獲得更廣泛的推崇。”

我是匠人
提起自己出生在揚州,身為玉雕師的楊光滿是自豪感。但在海派玉雕、蘇州玉雕、京派玉雕蒸蒸日上的當下,他覺得揚州玉雕應該找準自己的方向。“雖說‘天下玉,揚州工,但這不能只停留在嘴上。換句話說,不能躺著吃先人們留下的老本兒。”
揚州玉雕自古以大型器皿、山子、鏈子活等為特色,但讓楊光傷心的是,一些本該成為重器的材料被切割成牌子、手鐲、掛件。在傷感的同時,他對此也持理解的態度:“做大器物制作過程慢,周轉也慢。而將大料切割后,選擇性廣了、流轉周期快了,人家能生存下去。”而讓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行業內的一些欺詐現象。“機雕就是機雕,俄料就是俄料,如實告訴買家就行了。如果你讓人家花重金買回去心里還不舒服,將來誰還敢買當代玉雕、買揚州玉雕?”
堅守與誠信,是楊光對待玉雕行業的態度。正是30多年來的堅守與誠信,讓他逐漸在這個行業里脫穎而出、站穩腳跟。但他在面對目前所取得的成績以及未來的發展時,還是堅定地認為應該踏實前行,尤其不能急功近利、追名逐利。他說:“ 現在很多玉雕師在追逐‘大師的名號,的確,作為從業者應該去追求這種榮譽。能有它更好,誰不想當大師?但沒有也別將精力都放在這上面,難道沒有就不干這一行了嗎?”
楊光覺得,即便成為“大師”,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從做玉器這件事來說,玉雕師永遠是匠人。“現在有了所謂的大師稱號,在以前,我們與瓦匠、木匠、石匠沒有任何區別,玉雕師千萬不能忘記自己是匠人。”
楊光曾做過一件作品,內膛為方形,沒有其他方法,只能用土辦法——磨。他說制作一件器皿需要十幾道工序,因此對創作者來說應慎之又慎。這件器物他整整磨了6個月,“做器皿很慢,是一個玉磨人、人磨玉的過程。磨啊磨,看著里面的線條逐漸清晰,心理舒服極了。而這種體會是用電腦、用機器無法感受到的”。
楊光說,在不停地打磨中,他可以看清一件器物成型的全過程。“器型追求簡,過程追求繁”,這是他不二的創作準則。
看來,在創作中常有奇思妙想的楊光,是在周而復始與玉的磨合中成就的。難怪,他那雙手如此溫潤如玉。(注:本文圖片由楊光大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