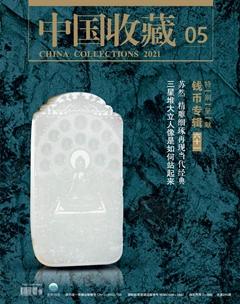清末最早的兩筆對外公債發行始末
戴學文

建成于1844年的倫敦證券交易所
清末中國因財政困難,開始息借洋款,先是為了作戰、防務、賠款等,繼而有筑路、建設、改革等名目。最初,以英商匯豐銀行為主的個別銀行承作此項業務。后因中方的借款需求猛增,19世紀70年代以降,許多借款就在中方不明就理及銀行的誘導下改以公債形式,并分割成各種金額的債券在海外市場發行,出售給不特定的投資人。而匯豐等銀行則搖身一變,成為承銷商。
轉為公債
清末官員雖急于獲得外國銀行的借款,但對借款轉為發行公債,乃至于背后的金融體制運作等問題普遍不重視。上奏時多僅以“另發小票”一語帶過,鮮少提及借貸成本、條件與法律關系等轉變;有不少人甚至因洋稅可一再預借巨款而竊喜。
相對于中方的顢頇無知,主宰當時國際債市的英國早已預做準備,提前布局。因其深知,一旦開始將清政府借款改以公債對外發行,同時也意味著公債市場將吸收來自中國舉債的量能,并承擔相關風險。為了保障金融秩序與安全,先決條件是:清廷符合條件,即至少必須承諾并有足夠能力履行償還義務。這項任務隨后就在英籍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的推動之下完成。

英國匯豐銀行在銀兩借款中支付給中方的是墨西哥鷹洋。
清末出現的早期息借洋款無不以關稅為擔保,進而形成海關為借款背書的慣例。不過,根據赫德的記述,中國官員常有先斬后奏、事后又未必可獲得授權與核準的情形;有時是因前任未經批準,遭到后任拒絕承認;也有的是以關稅擔保借款,卻未知會稅務司;甚至有的借款,出現了名義與用途不符的情形。這些亂象,直至1868年總稅務司與總理衙門及各地海關分別溝通、對于流程建立共識后才陸續解決。
此后,任何以關稅擔保的對外借款都必須獲得朝廷的同意才生效。另外,息借洋款因具有涉外性質,按外交慣例,應由總理衙門照會外國駐京使館,傳達中國政府對于借款合同的批準意旨。內部聯絡窗口則一律改由總理衙門負責,再知會總稅務司配合辦理。各口岸海關的權限也予以整合;各稅務司必須獲得總稅務司授權,才得在抵押的海關印票簽署用印等。這些規則的建立無疑已為匯豐等外國銀行完成了鋪路工作。
由于總稅務司赫德的布局,英國對于中國財政的影響力得以從海關擴展至中國的財政事務。因為關稅擔保及借款流程明確、借款風險獲得管控,所以匯豐銀行代理中國政府發行公債的態度轉向積極。1875年,匯豐銀行首度嘗試將“臺灣海防借款”轉發公債。
最早發行
臺灣海防借款,發生背景與1874年(同治十三年)爆發的“牡丹社事件”有關。當時,日軍借口琉球漁民被害而入侵臺灣南部,此一事件震動了中國朝野。為了整頓與強化臺灣的防御工事,閩浙總督沈葆楨緊急向匯豐銀行議借款項。
根據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沈葆楨等人《籌辦臺防向匯豐銀行借銀二百萬兩》折記載,匯豐同意出借200萬兩白銀,作為鞏固臺灣海防之用,年息8%,半年付息一次。前一年半僅付息;此后,本息一并攤還,以粵海、九江、江海、浙海、鎮江、江漢、山海、津海、東海等海關關稅代墊,再由福建將應解京餉撥還各海關。
這筆銀兩借款折合75萬英鎊。匯豐銀行接受中方之提議,以銀兩記賬、付息及還本。不過,也提出將借款轉到海外發行公債的要求。匯豐的這項要求也被中方采納。

作為西征解餉,杭州和記銀號于光緒二年委托上海萃泰銀爐改鑄的馬蹄形伍拾兩元寶。
后來,匯豐銀行選擇在1875年至1876年兩年間將部分借款分別轉往香港、倫敦兩地發行公債,出售債券。這種以“臺灣海防借款”為名的公債,就成為近代史上中國政府首次在國際市場發行的公債。
處于摸索過程的臺灣海防借款,由于以銀兩交付,債券卻以英鎊計價,匯豐銀行無異承擔了白銀貶值的風險。為了抵消風險,中國政府被要求支付8 % 年息,與同期倫敦市場公債年息水平4%至5%相比高出約一倍。
另一方面,臺灣海防借款雖是一種“銀兩”借款,不過,匯豐實際交付中方的并非中國各省慣用的銀錠,而是匯豐因經營遠東市場所累積的大量墨西哥鷹洋。
鷹洋早在1856年起就在上海租界華洋商人的共同支持下,取代了已停鑄多年的西班牙本洋作為流通之用。由于鷹洋同時也在臺灣流通,因此對于此一安排,沈葆楨并無異議。
只是,鷹洋與銀兩的換算仍須按倫敦匯市行情,先將鷹洋兌換成英國先令銀幣,再將先令兌換成白銀,手續頗為繁瑣。這筆200萬兩白銀借款折合75萬英鎊。匯豐選擇將其中的627615英鎊轉為公債對外發行,年息8厘,期限10年,每年抽簽還本。匯豐共發行100英鎊券6275張,畸零券66鎊2先令、48鎊18先令各1張,先后于1875年、1876年在香港與倫敦按面額如數完銷,兩地各賣出約半數。其余未發行公債之借款122385英鎊,則由匯豐自行出借。
公債發行后,本息均如期償還,并于1885年最后一次還本后結清。債券則于還本后繳回,應已全數銷毀,至今不僅無人見過其債券真面目,其相關歷史也少有人知。
后來,臺灣海防借款模式也被匯豐銀行套用到1877年左宗棠西征借款之上。
沿用前例
左宗棠西征期間,胡雪巖擔任上海轉運局委員,負責購運西洋軍火、轉運東南協餉,餉糧不足則向華洋商人洽借。這段時間,舉借外債就有六次。其中第四次是在1877年向匯豐借銀500萬兩,是唯一被轉為公債的借款,也是繼臺灣海防借款之后,中國第二筆在海外發行的公債。
借款由匯豐銀行出借關平銀500萬兩。中方則以上海、寧波、廣東、漢口四關關稅作抵,每月支付利息1%,合年息12%,本金分7年14次攤還,并授權匯豐代為發行公債。
由于同為銀兩借款,交易模式仍沿用1874年臺灣海防借款之例。亦即索取高額利息,以補貼可能的白銀跌價損失;另則,雖名為白銀借款,所交付者實為墨西哥鷹洋。
但前例的沿用卻在此次借款中造成中方極大的麻煩。與西征有關的山西、甘肅、新疆等西北地區慣用馬蹄元寶,與東南沿海各省及臺灣流行鷹洋的情形不同。由于歷次西征借款,大致都碰到必須因地制宜、改鑄餉銀的問題,所以胡氏旗下的錢莊銀號等曾提供相關支援。其中有一家名為“和記”的銀號,便是主管解交運庫(上海轉運局庫銀)至前線指揮所山西運城的任務,存世有“光緒二年 月·萃泰·和記”伍拾兩馬蹄銀一件,即為和記委托上海銀爐萃泰按照山西形制改鑄的庫銀。根據《杭州志》記載,即使在光緒九年胡氏破產之后,和記仍被指派專司相同任務。此次匯豐銀行借銀500萬兩,改鑄問題自不可免。為了非馬蹄元寶不用的西北地區,負責交涉的胡雪巖收到鷹洋借款后,在前線需款甚急、不容延宕的情況下,選擇由德商泰來洋行(Te l g e & C o m p a n y)“包認實銀”,負責提供500萬兩白銀。泰來洋行除了將折合500萬兩銀的鷹洋換成銀錠之外,由于匯豐提供的鷹洋多在中國流通過,按傳統金融界的習慣,轉手之間為了檢驗銀幣成色,常被砸上大大小小的戳印,幾至慘不忍睹的地步。商民口中的這些“爛番銀”、“爛板”,比起沒有戳印的“光洋”、“光板”,市價較低,兌換成白銀后,必然無法到達借款全數。折價后不足500萬兩銀的部分,泰來洋行也必須提供借款予以補足。為了這樁兼具匯兌與借貸性質的交易,胡雪巖將相關成本“利息化”,另又付出3%,年息增至15%。由于代價極高,也引來許多攻擊與非議。
匯豐銀行選擇了將這筆借款全數發行公債。借款關平銀500萬兩,合1604276英鎊又10便士,轉往倫敦與上海租界發行英鎊公債,100英鎊券16042張,畸零券76英鎊10便士1張。公債年息8%,按面額九八折出售。

1877年匯豐代理中國政府在上海與倫敦發行的西征借款公債100 英鎊券,已注銷。圖片來源:2013年斯賓克(Spink)倫敦拍賣
這一過程中,匯豐銀行再度承擔了銀兩與英鎊之間繁瑣的兌換手續,但更棘手的是匯兌損失。因各國紛紛改采金本位,拋售白銀,使得銀價大幅下跌,其程度已非以提高利息所能吸收。西征借款公債,年息8%,但匯豐銀行向中國索取的借款利息則是12%,多出的4%,匯豐預留作為彌補可能發生的白銀貶值損失之用,但事后看來,明顯不足。
1875年臺灣海防公債發行時,白銀與英鎊比價為2.66667兩換1英鎊;3年后的1877年,西征借款公債發行時,跌至3.11667兩換1英鎊。1885年,當西征借款清償完畢時,更跌至3.98514兩兌1英鎊。總計,臺灣海防公債所經歷的11年多期間,銀兩貶值了近五成,西征借款公債發行的7年期間,則下跌了約兩成八,匯豐銀行在兩次公債發行中都蒙受了損失。
有了前車之鑒,在英國主導下,原本對中國政府常見的銀兩借款往后已轉為堅持“非英鎊不借”的原則。這筆借款所轉發的公債,選擇在倫敦與上海租界兩地發行。前者,是當時世界金融中心,理由自不在話下;至于上海租界的雀屏中選,則應與當地的證券交易市場已成形并日趨活躍有關。
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航運、銀行等業務快速成長,租界的洋商因采取股份制,開始出現了公司股票的交易,成為近代上海證券交易的起源,公債的買賣也側身其中。19世紀60年代,以股票為主的證券交易快速成長。隨著1867年上海的第一家專業證券經紀商英商長利公司(J.P.Biest&Co)的成立,證券公司便如雨后春筍般接連開設。盡管經營者與參與者仍以上海租界的洋人為主,但匯豐銀行應是看中了這塊市場的潛力,因此西征借款公債就成為第一筆在上海發行的中國對外公債。
西征借款公債于1884年全數清償完畢,債券回收銷毀,至今僅見遺存注銷票一張,這也是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中國對外債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