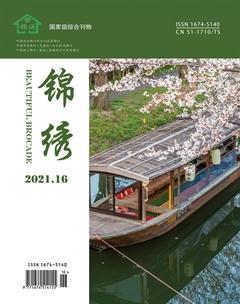試析時代變遷背景下電影《江湖兒女》中的故園憂思情結(jié)
王燕
摘要:作為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賈樟柯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領(lǐng)域的巨大變革與發(fā)展。在時代遷移與變化中,故園的鄉(xiāng)土鄉(xiāng)情成為他創(chuàng)作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江湖兒女》作為賈樟柯極具個人風(fēng)格的影片,秉承了一貫的關(guān)注現(xiàn)實,關(guān)注時代變遷下小人物的成長和境遇。本文從符號化的語言、空間敘事和聲音藝術(shù)等角度出發(fā),就影片《江湖兒女》的影像風(fēng)格和表達手法進行分析,旨在為同類題材的影片提供創(chuàng)作思路。
關(guān)鍵詞:《江湖兒女》;故園憂思情結(jié);符號化語言;空間敘事;聲音藝術(shù)。
《江湖兒女》是由賈樟柯執(zhí)導(dǎo)的犯罪愛情電影,影片聚焦于時代變遷背景下山西大同的一個小縣城。故事從2001年開始到2018年元旦結(jié)束,巧巧與斌哥跨越17年,歷經(jīng)相愛與背叛、分離又重逢。 “江湖”意味著動蕩、激烈、危機四伏的社會,也意味著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兒女”意味著有情有義的男男女女。1可以說《江湖兒女》是其對 “故園舊夢”的重新建構(gòu),也是對“故園遺失”的最后沉思,是賈樟柯情感的積淀也是其電影創(chuàng)作歷程的濃縮。
一、符號化語言的應(yīng)用
麥茨曾提出,電影是一個特殊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影片中內(nèi)容多樣的影像、文字、音樂以及聲響等多個部分可以看作電影語言的構(gòu)成元素,這些元素之間進行不同的組合拼貼,構(gòu)成了電影主題內(nèi)容的句式結(jié)構(gòu)與范式結(jié)構(gòu)。電影不僅是對現(xiàn)實為人們提供的感知整體的摹寫,而且還是具有約定性的符而且還是具有約定性的符號系統(tǒng),影片的意義是通過電影符號系統(tǒng)要素之間的內(nèi)部運作而產(chǎn)生的直接效果,所指和能指構(gòu)成了影片的內(nèi)涵和外延。2賈樟柯的影片從來不缺乏符號化的應(yīng)用,《江湖兒女》更是賦予了符號化電影語言更深層次的含義。影片伊始,斌哥替老賈和老孫斷案,老賈始終不承認自己欠老孫的錢,即使老孫用槍逼供,老賈都未曾承認,直至斌哥請出“關(guān)二爺”,老賈才松口。眾所周知,賈樟柯是山西人,而影片所選取的符號化形象代表“關(guān)公”也今屬山西運城人,這一人物形象在中國歷朝歷代都被人所褒獎,毛宗崗更是稱其為《演義》三絕中的“義絕。導(dǎo)演一方面借“關(guān)二爺”寫斌哥堅守道義,秉公處事這一江湖大哥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從側(cè)面反映出導(dǎo)演對故鄉(xiāng)的情感依托。影片中多次出現(xiàn)的“汾酒”也是為了加深了故園情思符號化的表達。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酒”聯(lián)系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市井宵小無一例外。斌哥請大家喝的 “五湖四海”其中就有山西汾酒,看似是喝生死之交一碗酒”的五湖四海,實則喝的是社會變革中對故土的深切眷戀;巧巧父親喝汾酒壯膽揭露礦廠廠長劉金明的惡劣行徑,憑借的就是曾為故土貢獻一生的底氣。總之,不論是“關(guān)二爺”還是“汾酒”影片傳達出來的恰恰是賈樟柯的山西根基和故鄉(xiāng)情懷。此外,礦泉水作為巧巧重塑自我過程中的重要道具,也是一個符號化的意象。巧巧出獄后前往奉節(jié)尋愛途中手里始終拿著一個礦泉水瓶,一方面礦泉水瓶為自己解渴,另一方面礦泉水瓶又如巧巧闖蕩江湖的劍,在飯席上巧巧用礦泉水瓶與桌上其他客人干杯,在拯救偷錢女人的時候,礦泉水瓶又成了巧巧的武器……一系列變革之后巧巧再次回到大同,彼時放下了情感的糾葛,成全了自己的故園道義。不斷解讀符號化語言背后的含義,也就讀懂了賈樟柯的故園憂思情結(jié)。
二、“江湖”變更中的空間敘事
《什么是電影敘事學(xué)》一書提到:在影片的敘事中,空間其實始終在場,始終被表現(xiàn)。3影片《江湖兒女》基于時空的敘事跨度,在時空變化中發(fā)現(xiàn)日常生活的哲理和歷史詩意,時空變更也描繪了一個錯綜復(fù)雜的社會現(xiàn)實。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擁擠臟亂的環(huán)境,疲懶木訥的人物群像一下把觀眾帶到那個現(xiàn)代化進程中被疏離的小縣城。小縣城既沒有農(nóng)村的落后貧瘠,也沒有都市的繁華熱鬧,這里剛好是兩者之間的過渡地帶,到處充斥著濃郁的時代氣息。斌哥和巧巧最初的江湖生活就在這里展開,嘈雜昏暗的麻將館煙霧繚繞、插科打諢,華燈閃爍的歌舞場激情狂歡、肆意吹噓,簡單樸素的居家環(huán)境寧靜致遠、有情有暖,這一幕幕真實的生活場景構(gòu)筑了在時代洪流下小人物最真實,最鮮明的生活狀態(tài)。此時的大同是賈樟柯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xiāng),是凝結(jié)著心血和情感的心靈歸處,是寄托著精神的理想家園。
“起先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內(nèi)心深處有著一種強烈的敘事愿望。當我離開縣城,汾陽的那些人和事兒一天比一天清晰”4。漂泊和輾轉(zhuǎn)是賈樟柯電影中不變的主題,空間轉(zhuǎn)換的過程是重塑自我,認識自我的過程。巧巧遠離故鄉(xiāng)踏上奉節(jié)開始漫漫尋愛之旅,起初為的是尋找自己的愛情,卻在重重磨難下尋回最真實的自我。盡管金錢被偷但不能允許男人打偷錢女人;遭受感情破裂也要體面等斌哥答復(fù);行騙騙人不忘提醒渣男給“她”打電話;機智化解危險不忘歸還摩的給人留口飯吃……雖歷經(jīng)多種苦難,但卻堅守了內(nèi)心最樸實的道義,正是因為巧巧的有情有義,導(dǎo)演才只讓她看見滿眼星辰,最終返回故鄉(xiāng)。同樣“異鄉(xiāng)”在賈樟柯的影像中往往也是侵蝕現(xiàn)代人情感的容器。反觀斌哥在對金錢和成功的渴望中迷失了江湖信仰、初心和故鄉(xiāng),最終導(dǎo)致愛情分道揚鑣,手足恩斷義絕。巧巧與斌哥這類遠離故園,漂泊異鄉(xiāng)的人的孤獨與迷惘也正是城市發(fā)展的陣痛與焦慮。
農(nóng)業(yè)生活的成長背景,返鄉(xiāng)之途的現(xiàn)實寫照,或隱或現(xiàn)的透露出賈樟柯的美學(xué)理念與哲思,使他的創(chuàng)作理念信條割不斷“土地的聯(lián)系”。在經(jīng)歷了故園遺失,他鄉(xiāng)漂泊之后,返鄉(xiāng)之途尋找精神樂園就顯得尤為可貴。在《江湖兒女》接近尾聲的時候,潦倒的斌哥返回曾經(jīng)的故土,飛速的高鐵,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陌生的街景讓他悵然若失,往昔馬仔的各奔東西,廚子上菜沒有規(guī)矩,老賈的欺辱,讓執(zhí)意返鄉(xiāng)的斌哥在真正意義上無法回歸。返鄉(xiāng)本是對故鄉(xiāng)的歸根,對精神家園的找尋與認同,而返鄉(xiāng)后卻發(fā)現(xiàn)無家可歸,這又是怎樣的凄楚與悲情。《江湖兒女》不是解構(gòu)的,而是重塑的,在變遷的時代和社會中,如何面對故園的逝去和日新月異的未來,這反映的正是導(dǎo)演的追問、尋找、哲思。縱觀導(dǎo)演的情節(jié)梳理和影像關(guān)照,不管是出于空間意義上衍生出的故園憂思,還是出于時間跨度上的懷舊情緒,近二十年的中國小城鎮(zhèn)變遷就這樣靜靜地流淌在了銀幕之上。
三、環(huán)境音、方言、流行音樂:聲音藝術(shù)的展現(xiàn)
除了符號化的語言和空間轉(zhuǎn)換的敘事方式外,賈樟柯還十分注重利用聲音元素來營造生活的現(xiàn)實氛圍和反應(yīng)人物內(nèi)心的情感波動。《江湖兒女》中環(huán)境音、方言、廣播電視音和流行音樂都為他建構(gòu)廣闊的現(xiàn)實和豐富的詩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江湖兒女》對環(huán)境音的應(yīng)用可謂是貫穿了整部影片的始終,汽車聲、風(fēng)聲、機械聲、電視聲、廣播聲,交談聲……為了突出這些聲音,導(dǎo)演不惜讓它們淹沒主人公的對話。戴維蓋里奧克說:“我們今天試圖逃離的城市噪音,對于現(xiàn)代早期的城市居民來講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源,它形成一個符號系統(tǒng),傳遞信息幫助人們確定他們的時空位置使他們變成一個聽覺共同體”。5賈樟柯顯然對此有自己獨到的理解,他的影片不但不反對“噪音”,反而通過它們來構(gòu)造立體的聽覺系統(tǒng)和整體的現(xiàn)實生活。影片開頭的汽車發(fā)動機轟鳴聲和車內(nèi)的嘈雜聲瞬間為觀眾展現(xiàn)了一個真實小縣城的生活百態(tài);麻將館的麻將碰撞聲、人物的交談聲,與斌哥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從側(cè)面烘托出了出了江湖大哥的威嚴;巧巧與斌哥兩次站在火山口,耳旁生機盎然的風(fēng)聲和凄涼蕭瑟的風(fēng)聲,揭露了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的現(xiàn)實,更為往日大哥形象的消逝平添一份落寞;斌哥巧巧在異鄉(xiāng)重逢后,背景雨聲甚至超過了倆人的談話聲,陰暗潮濕的環(huán)境,渲染了巧巧與斌哥分道揚鑣的悲涼氛圍;后面斌哥返鄉(xiāng)時候的高鐵過站聲,導(dǎo)航語音聲又闡釋了時代變遷中美好情愫不復(fù)存在的惋惜。盡管這種有違藝術(shù)的“噪音”既無美感可言,也無人為賦予其符號化的象征意義,甚至它們顯得刺耳、多余。然而,正是這種作為物性聲音的“噪音”,卻顯示了一種未經(jīng)簡化與抽象的本真音色,凸顯了現(xiàn)實生活本然的嘈雜、混亂與庸常。這種聲音狀態(tài)更加貼近生活,更加雜陳,也更為豐滿凝重,使得賈樟柯的電影揭示的現(xiàn)實充滿更多可以觸摸的細節(jié)。
賈樟柯電影中的方言的應(yīng)用已經(jīng)成了他的風(fēng)格標識,具有建構(gòu)真實藝術(shù)空間、彰顯紀實美學(xué)風(fēng)格、還原生活原始形態(tài)、塑造底層人物形象、標識主體社會身份、隱喻文化的延續(xù)與斷裂等多種內(nèi)涵。《江湖兒女》中的巧巧和斌哥所說的是山西方言;林家燕講的是粵語;船上的小偷,摩的司機、辦案警察、林家棟公司前臺講的重慶話;克拉瑪依男子講普通話……這些方言融匯到一起就是社會變革遷徙中最真實的中國原貌。片中巧巧初到奉節(jié)與小偷講話時用的山西方言,發(fā)現(xiàn)與人無法溝通時轉(zhuǎn)換成普通話,從這一細節(jié)不難看出巧巧飄落在外心系故園又不得不順應(yīng)時代發(fā)展而做出心理轉(zhuǎn)變。在奉節(jié)見到斌哥之前,巧巧跟遇到的行騙對象、摩的司機、警察的時候都講普通話,這樣的設(shè)置無疑是加深了故土難歸與異鄉(xiāng)難融的矛盾沖突。在他鄉(xiāng)重逢后的巧巧與斌哥所講的都是山西方言,盡管鄉(xiāng)音依舊 ,但眼前人已非彼時人,二人在復(fù)雜的社會背景下已然成為兩個極端。故事的最后,巧巧決定回到故園,重新認同和定義自己的江湖。 在這一系列方言與普通話的不斷轉(zhuǎn)換中,影片加深了故園情誼的確立和身份的認同。
從《小武》到《江湖兒女》,賈樟柯幾乎每部電影必用流行歌曲,從來沒有一個導(dǎo)演如此執(zhí)著地把大量流行歌曲植入電影。賈樟柯電影中的流行音樂不僅表情達意,而且轉(zhuǎn)虛為實,把個體無言的體驗轉(zhuǎn)化為具體可感的物性音符,把情感記憶轉(zhuǎn)化為可觸的現(xiàn)實空間。流行歌曲的植入,極大地擴展了賈樟柯電影的文本意蘊和現(xiàn)實指向。“ 一首歌曲流傳越廣,它的社會聯(lián)系越是復(fù)雜繁多,它溢出了音樂主文本,指向各種現(xiàn)實相關(guān)的語境。”二勇不幸遇害,斌哥和巧巧前去祭奠的時候,所奏之樂不是哀樂,而是《上海灘》,浪奔浪流,萬里濤濤江水永不休,淘盡了世間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短短四句濃縮了二勇一生的沉浮,最后歸于塵土,也道明了斌斌所在所處的江湖即小縣城,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猶如滔滔江水一般奔流到海不復(fù)回。 斌哥被大壯小壯偷襲后與小弟觀看影片《喋血雙雄》的時候響起了葉倩文的《淺醉一生》,斌斌和眾多命運相似的小弟們一樣,夢想找到志同道合,生死相依的兄弟,找到自己在時代變遷中的一席之地。命運往往事與愿違,斌斌在入獄后不僅失去了自己的兄弟,也遺失了自己的江湖。《瀟灑走一回》結(jié)束后,斌斌、巧巧與林家棟、林家燕兩兄妹碰面,再后面的故事走向中,斌斌也是在巧巧家燕兩個女人之間聚散,恩恩怨怨,名利愛情都不如瀟灑走一回。《江湖兒女》對于流行歌曲的運用,不僅僅是接受現(xiàn)實物質(zhì)的載體,更是變成了一種對抗現(xiàn)代化創(chuàng)傷的精神信仰。
如果說嘈雜的音響是生活的聽覺基底,流行音樂就是電影音樂的“ 現(xiàn)成品 ”,而方言則是語言的肉身能指,賈樟柯電影中的這些聽覺元素始終充滿著可以觸摸的物性特征。這些聲音拒絕形式的簡化,拒絕旋律的美化,也拒絕相對單一的電影敘事編碼,這卻使得它們向廣闊的社會生活敞開,向更為豐富細膩的聽覺整體性敞開,從而使賈樟柯的電影充滿樸素飽滿的詩意。
結(jié)束語:
賈樟柯的影像大都聚焦于社會變遷下的城鎮(zhèn)發(fā)展,始終用冷靜的鏡頭描繪著社會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態(tài)。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城鎮(zhèn)帶給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一種文化上的信心。這是我從縣城里吸收到的最大的營養(yǎng)。這使我不管走到哪兒,都能有一種勇氣。”6《江湖兒女》不僅是賈樟柯對往昔創(chuàng)作的回顧,對故園舊夢的重拾,更是對自己過往的總結(jié)與超越。在中國電影發(fā)展的今天,如何觀察世界,如何在自身創(chuàng)作的固有模式中尋找創(chuàng)新,《江湖兒女》提供了很好的參考意見。
參考文獻
[1]郭增強,楊柏嶺.“兒女的江湖”:賈樟柯電影的空間敘事[J].電影文學(xué),2019(02):80-82.
[2]楊狀振.賈樟柯電影:如菊影像與似酒情懷[J].藝術(shù)廣角,2007(03):.20-23+27.
[3]田野.《江湖兒女》與賈樟柯的電影江湖[J].文化藝術(shù)研究,2019,12(04):122-128.
[4]劉昌奇.嘈雜音響、流行歌曲與地域方言——從藝術(shù)物性論看賈樟柯電影的聲音詩學(xué)[J].文化藝術(shù)研究,2019,12(01):114-121.
[5]賈樟柯.江湖從頭說[J].視野,2018(19):50-51.
[6]安德烈·戈德羅[加],弗朗索瓦·若斯特[法].什么是電影敘述學(xué)[M].商務(wù)印書館.2005(10).北京
[7]賈樟柯.賈樟柯電影手記1996-2008.[M].臺海出版社.2017(2).北京
[8]吳曉東.《城鎮(zhèn)帶給我文化上的信心》,載《中國青年報》.2006年第5期
[9] Garrioch, David. Sounds of the City: The Soundscape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Town[ J ].Urban History, 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