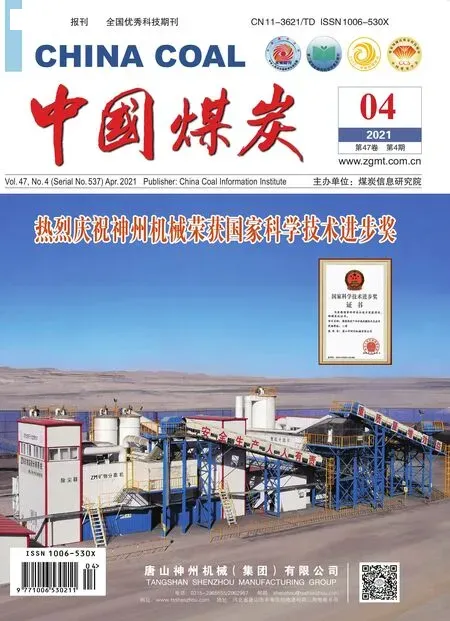德國煤炭工業發展趨勢
黃 嵐
(應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北京市朝陽區,100029)
德國是世界第四大經濟強國、歐盟最大經濟體,也是第八大煤炭生產國及第九大煤炭消費國。德國煤炭資源豐富,根據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8年德國硬煤(煙煤和無煙煤)可采儲量為3 Mt,褐煤可采儲量為3.61 Gt,總可采儲量為3.610 3 Gt,占世界煤炭總可采儲量的3.4%。煤炭在德國一次能源結構中曾占絕對統治地位,但從1990年開始,煤炭在能源行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2019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所占的份額為17.7%,居第3位。煤炭是德國重要的電力來源之一,但由于近年來德國一直推行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轉型”戰略,煤炭工業政策整體調整,2018年德國國內硬煤生產停止,燃煤電廠將逐步被淘汰。
1 煤炭資源
德國的煤炭資源生成于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古生代煤層主要為煙煤,也有部分無煙煤,分布在西部北威州的廣大地區;南方薩爾州有小的含煤區。中生代煤層從次煙煤到無煙煤,但儲量很少。新生代次煙煤和褐煤在西部的萊茵河地區和東部地區分布很廣。
德國的煤炭分類十分簡單,分硬煤和褐煤兩大類。硬煤以煙煤為主,無煙煤所占比例很少,煤質好,低灰低硫,適合作動力煤和煉焦煤,但德國硬煤開采條件比較差,煤層薄,開采深度大。與硬煤礦井不同,德國褐煤煤礦開采條件十分有利,煤層厚、埋藏淺,適合露天開采。
德國有7個主要煤田,其中硬煤煤田為魯爾煤田、薩爾煤田、亞琛煤田和伊本比倫煤田,褐煤煤田有西部的萊茵煤田和東部的勞齊茨煤田、德國中部煤田。
2 煤炭在能源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能源消費量和生產量總體呈雙下降趨勢
1990年以來,德國的一次能源消費在波動中緩慢下降,如圖1所示。特別是近10年來,由于經濟增長疲軟、冬季氣溫上升導致供暖能源需求減少、能源利用效率的總體提高以及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影響,德國的能源消費總量、石油和煤炭消費量下降,可再生能源消費同期增長。2019年德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為436.0 Mtce,其中,石油占35.3%,天然氣占 25.0%,煤炭占17.7%,可再生能源占14.8%,核能占6.4%。與1990年相比,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下降了14.3%,其中煤炭消費量下降了約59%,而可再生能源消費量上升了約8.7倍[1]。
2019年德國的一次能源產量為122.2 Mtce,比1990年的212.4 Mtce下降了42.5%。德國國內的能源生產主要是煤炭及可再生能源,石油及天然氣需大量依賴進口。1990-2019年,可再生能源產量大幅增加,從1990年的6.8 Mtce增加到2019年的65.0 Mtce,增長了約8.6倍,煤炭產量則下降了77.3%。

圖1 1990-2019年德國能源消費及生產情況[2]
2.2 煤炭在能源系統的重要性下降
20世紀50年代,煤炭在德國的一次能源結構中占比高達近90%,占絕對統治地位。從1990年開始,德國煤炭消費量多年來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煤炭在能源系統的重要性逐步降低,失去了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主導地位,截至2019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所占的份額僅居第3位。
從1990年開始,德國能源消費結構變化如圖2所示,石油、天然氣是德國國內最重要的能源消費來源,煤炭、核能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下降明顯,可再生能源的消費占比逐年提高[2]。

圖2 1990-2019年德國能源消費結構發展趨勢
煤炭是德國重要的電力來源之一,由于受到了天然氣及石油進口增加、可再生能源增長、碳價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德國的燃煤發電量持續下降,從1990年的311.7 TWh降至2019年的171.2 TWh;燃煤發電在總發電量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從1990年的56.7%降至2019年的28.0%,如圖3所示。2019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所占的比重已超過燃煤發電。

圖3 1990-2019年德國發電結構變化趨勢
3 煤炭工業政策
3.1 逐步取消硬煤開采補貼及關閉硬煤煤礦
德國的煤炭工業基本走完了從初期的簡單開采到現代化發展,從企業轉型到煤礦關閉的整個生命周期。德國政府一直對煤炭工業采取傾斜政策,包括價格補貼、稅收優惠、投資補助、政府收購、礦工補助、限制進口、研究與發展補助等。由于高額的補貼導致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同時受到廉價進口煤炭和其他能源的不斷沖擊,德國的煤炭工業政策也在逐步調整。
1997年,德國聯邦政府和煤炭公司及礦業能源協會就硬煤補貼達成協議,根據這項新的財政補貼協議,聯邦和州政府對本國硬煤銷售補貼額從1996年的67億歐元減少到2005年的27億歐元。2007年,歐盟的競爭法規要求德國在2018年終止硬煤補貼。2007年2月,聯邦政府、北威州和薩爾州政府以及德國硬煤公司和采礦、化學與能源工業聯盟(IG BCE)達成了一致意見,于2007年12月底出臺了《煤炭工業融資法》,決定到2018年底逐步取消對硬煤的補貼。2008年1月,德國執政兩黨高層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在2018年前關閉德國所有煤礦[3]。
3.2 淘汰褐煤電廠及退出燃煤發電
近10年來,德國一直推行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轉型”戰略,其政策框架是氣候保護、退出核能、保障供能安全和確保競爭力。在氣候保護方面,德國設定的溫室減排目標是以1990年為基準,計劃到2030年減少55%,到2050年減少80%~95%,見表1。為了達到能源轉型的目標,德國鼓勵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計劃到205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終端能源消費總量的60%,在發電量中的占比至少達到80%。

表1 德國能源轉型的定量目標和現狀
根據德國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煤炭消費占德國全部能源領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5%(1990年為58%),其中,硬煤占21.3%,褐煤占23.7%。數10年來,雖然在歐盟和德國國內層面都采取了一些減排政策,但德國在煤炭領域的減排效果不佳。德國要實現其減排目標,整個能源部門,特別是燃煤發電領域必須做出高于平均水平的貢獻。
2015年,德國政府提出在2016-2019年關閉裝機容量達2.7 GW的褐煤發電機組計劃,相當于當時總裝機容量的13%。2018年6月,德國政府創立了“增長、結構變化和就業委員會”(也稱“煤炭委員會”),煤炭委員會在2019年向政府提交了建議報告,建議在2038年(最早可能在2035年)前逐步淘汰以煤炭為基礎的發電項目,包括: 2019-2022年逐步淘汰12.5 GW燃煤發電裝機量,將燃煤儲備電廠轉變為燃氣儲備電廠;2023-2030年盡可能平穩地減少燃煤發電量,到2030年燃煤發電裝機容量將降至不超過17 GW。基于煤炭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報告,德國內閣于2020年通過了《退煤法案》,確定了到2038年逐步淘汰燃煤發電的政策。
3.3 扶持采煤區轉型
2020年,針對煤炭委員會提出的到2038年逐步淘汰燃煤發電項目的建議,德國政府通過了一項關于扶持德國原煤炭產區經濟轉型的法案——《礦區結構調整》。根據該法案,德國政府將在2038年之前逐步向勃蘭登堡、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特和北威州4個煤炭主采區投入總計400億歐元資金,用于幫助這些地區在煤炭工業停止后實現經濟轉型。其中,大部分資金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包括網絡、道路和鐵路等,還有一部分資金將用于在這些地區設立科研機構和政府機關等。根據德國相關法律,這4個地區要想得到聯邦政府的資助,也必須同時出資,最低出資額要達到10%。此外,這4個聯邦州都提出了一系列應對經濟轉型的措施和建議,涵蓋諸多領域和行業。
4 煤炭消費與進口
4.1 硬煤和褐煤消費量大幅下降
德國是世界上第九大煤炭消費國,也是歐盟最大的煤炭市場,每年的需求約為60 Mtce。在德國能源轉型政策的影響下,德國的煤炭消費量出現明顯下降,從1990年的187.9 Mtce降至2019年的78.5 Mtce,下降了約58.2%。
1990-2019年,由于總體需求下降及國內褐煤減產,褐煤消費量下降明顯。1990年,德國的褐煤消費量為109.2 Mtce,如圖4所示,約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21.5%,在一次能源消費中僅次于石油,2019年的消費量降至39.8 Mtce,與1990年相比降幅達63.5%,在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中僅居第4位,占9.0%。受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擴張、國內硬煤停產及硬煤電廠關閉等因素的影響,加上碳價的上漲及天然氣價格的下跌,德國的硬煤消費需求疲軟,德國的硬煤消費量從78.7 Mtce降至38.7 Mtce,下降了50.8%,在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中的占比從15.5%降至8.6%,如圖4所示。

圖4 1990-2019年德國煤炭消費趨勢
德國主要煤炭消費行業為電力和鋼鐵。2019年,德國煤炭消費量的69%用于發電供熱,29%用于鋼鐵生產。褐煤是德國重要的電力來源之一,消費結構相對穩定,2019年褐煤消費量的91.2%用于發電。但是,近20年來硬煤的消費結構有所變化,對比2007年及2019年的數據可以看出,發電占比從2007年的65%降至2019年的47%,鋼鐵行業的消費上升明顯,從2007年的23%上升至到2019年的51%[4],如圖5所示。

圖5 2007年與2019年德國硬煤消費結構對比
4.2 煤炭進口量逐步下降
從1990年開始,隨著德國國內硬煤產量的減少,德國的煤炭進口呈逐年增長的趨勢,2014年達到近幾年的峰值49.79 Mt,如圖6所示。2014年以后,由于德國的煤炭消費量整體下降,煤炭進口量也出現下降的情況。2019年,德國的煤炭進口量為42.28 Mt,相比2014年下降了15.1%,其中硬煤進口量為40.35 Mt,焦炭進口量為1.89 Mt。
德國煤炭進口主要來自俄羅斯、美國、澳大利亞、哥倫比亞、南非、加拿大、歐盟國家等。俄羅斯是德國主要的硬煤進口國,近年來德國對俄羅斯的硬煤進口量連續增長,2017年達到歷史最高的19.71 Mt。2019年,德國從俄羅斯進口硬煤19.22 Mt,與2018年基本持平,占德國硬煤進口總量的47.6%。德國對美國的硬煤進口量穩定在10 Mt左右,2019年的進口量為9.35 Mt,占硬煤進口總量的23.2%。德國焦煤進口主要來自波蘭,2019年的進口量占焦煤進口總量62.8%。

圖6 1990-2019年德國煤炭進口趨勢
德國煤炭進口價格在2008年達到112歐元/tce的歷史最高水平,相比2000年的42 歐元/tce增長了近3倍,隨后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價格有所回落,2019年已降至72 歐元/tce,同比下降35.3%,如圖7所示。由于德國的原油和天然氣也極度依賴進口,因此與進口原油和天然氣的價格相比,進口煤炭的價格一直具有較高的競爭力。

圖7 德國進口能源價格變化趨勢
5 煤炭生產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統計,德國是世界第九大煤炭生產國,也是最大的褐煤生產國。從1990年開始,德國的煤炭產量總體呈下降趨勢。2019年,德國的煤炭產量約為131.3 Mt,同比下降20.7%,均為露天開采的褐煤;相比1990年的產量427 Mt,下降了約68.6%。隨著能源轉型的推進及退出燃煤發電政策的實施,未來德國的煤炭產量將繼續下降。
5.1 褐煤產量下降,從業人員銳減
德國近30年來的褐煤生產呈現下降趨勢,其中,1990-2000年左右出現了比較劇烈的下降,進入2000年以后波動較小,基本穩定在160 M~180 Mt之間。德國政府提出的2016-2019年關閉部分褐煤電廠的計劃影響了褐煤的生產,導致褐煤產量從2016年再次出現下降。2019年的產量為131.3 Mt,同比下降了21%。
德國褐煤以露天開采為主,生產集中在3個礦區,即位于科隆以西的萊茵礦區、德累斯頓和科特布斯之間的勞齊茨礦區、萊比錫以南的中部礦區。此外,在黑爾姆斯泰特附近也有小規模褐煤露天礦,但在2016年以后已停產。
位于西部的萊茵礦區是最大的褐煤開采區,萊茵集團(RWE)在該礦區經營了3個露天礦,2019年產量約為64.8 Mt,占德國褐煤總產量的49.4%,約90%產量直接供應集團的9個電廠。西部地區的褐煤產量一直保持較為穩定的水平,但就業職工的人數有明顯的下降,1990-2019年降幅接近43%,如圖8所示。
東部勞齊茨礦區的勞齊茨能源礦業公司(LEAG)共經營4個露天煤礦,2019年產量約52 Mt。德國中部礦區的德國中部褐煤公司(MIBRAG)經營2個露天礦;羅蒙旦公司(Romonta)經營了1個露天煤礦,生產的褐煤主要用于生產褐煤蠟。中部礦區2019年產量約為14.5 Mt。1990-2019年,德國東部地區的褐煤產量和就業職工人數出現顯著下降,產量降幅約為73.3%,就業職工人數降幅達到93%。
2019年,德國褐煤露天礦的平均剝采比為5.6。其中,西部的萊茵礦區覆蓋層厚度10~450 m,煤層厚度30~50 m,最大開采深度為300 m,剝采比為5.5;東部2個礦區的煤層覆蓋層厚度一般為100 m,煤層厚度8~30 m,最大開采深度為120 m,勞齊茨礦區的剝采比為6.3,中部礦區的剝采比只有3.7[5]。

圖8 1990-2018年德國煤炭產量及職工人數變化趨勢
5.2 硬煤生產結束
德國的硬煤產量在1957年達到歷史最高值,達到150 Mt/a,從1958年開始,德國的硬煤產量開始穩步下降。1990-2018年,德國的硬煤產量持續下降,從 1990年的69.76 Mt降至2018年的2.58 Mt。
德國硬煤以井工開采為主,生產集中在魯爾礦區、伊本比倫礦區、薩爾礦區和亞琛礦區。亞琛礦區及薩爾礦區已分別于1998年、2013年停止開采。2018年仍在運營的2個煤礦是位于魯爾礦區的Prosper-Haniel煤礦和伊本比倫礦區的Ibbenbüren煤礦。隨著德國政府對硬煤煤礦補貼的終止,這2個煤礦的常規開采于2018年9月結束,德國本土的硬煤生產也宣告結束,各礦區的職工將陸續轉崗再就業[6]。
德國生產的硬煤適合作動力煤和煉焦煤,具有重要經濟價值,而且礦區靠近工業中心,交通方便,基礎設施條件好。但是德國硬煤開采成本高,需要依賴政府的補貼才能維持正常生產。一方面,煤層薄,多數煤層厚度為0.5~1.5 m,工作面產量受到很大限制,難以實現高產高效;另一方面,開采深度大,2018年魯爾礦區平均開采深度已達1 290 m,通風降溫等開采裝備設施投入大。近30年來,德國的硬煤礦井經過合理化調整,加上煤礦的陸續關閉,生產工作面大大減少,生產主要集中在條件較好的少數工作面。2018年,德國的井下開采工作面共3個,工作面的開采速度為564 cm/d,日產量達到4 049 t的規模,井下全員效率達到100.41 t/工。
6 環境保護與安全生產
6.1 環保及關閉復墾經驗
德國煤礦區分布較廣,因此十分重視礦區的生態保護和土地復墾。政府相繼出臺了《聯邦礦業法》(2013)、《聯邦礦業條例》(1995)、《聯邦德國環境影響評價法》(1990、2001年修訂)、《廢棄淹水礦井的水資源管理》(2008) 等一系列有關環境的法規。同時,環境投資逐年增加,污染治理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左右。《聯邦礦業法》規定,企業在礦山開采前、開采中和終止時,都要制訂環境保護和治理規劃,報礦山主管部門批準。其中,開采企業對礦區復墾提出具體措施,礦山終止要有清除危險、拆除礦山建筑物、消除污染的具體規劃方案,方案中應明確生物物種和水體恢復到礦山開采以前狀態。《廢棄淹水礦井的水資源管理》也規定了廢棄礦井地下水監測、排水管理、排水處理等方面應遵循的原則和技術途徑。這些都由企業實施,礦山主管部門負責監督和驗收,從而保證了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環境的保護與修復。
德國的煤礦機械化程度高,所有褐煤露天礦井均是大型現代化煤礦,剝、采、運輸、回填全部采用機械化,產出的煤炭用強力皮帶直接運輸至煤礦周邊的火力發電廠,整個礦區對環境的破壞很小。煤礦邊生產邊回填,邊回填邊恢復植被,生產區周圍噴水霧降塵,防止煤塵擴散,經回填后留下的礦坑由環保公司進行全面系統的整治,用經處理的水充填礦坑,并將礦區改造為環境優美的水上休閑運動娛樂場所。根據德國褐煤協會的數據,自開采開始以來,德國褐煤開采的土地使用面積總計1 788.19 km2,其中69.8%已復墾[5]。
在硬煤開采工作結束后,魯爾公司承擔了魯爾礦區關閉礦井地表設施拆除、采礦區域監控管理等工作。2007年成立的RAG基金會負責為魯爾公司在采煤區進行礦井水抽排及凈化、塌陷區恢復等永久性工作提供資金,相關的投入約2.2億歐元/a,同時在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促進與硬煤開采業相關的項目。為了保障這些活動的長期融資,RAG基金會通過可靠的資本投資計劃來積累資產,截至2019年底,其資產已達到168億歐元。基金會的成立大大減輕了公共部門的財務壓力,保障了煤礦退出關閉后續工作的開展[7]。
6.2 安全生產水平
德國煤礦安全生產水平一直處于世界先進水平。2019年采煤業報告工傷事故人數200人,無人死亡[8],詳見表2。褐煤行業每百萬工作小時平均有2.0起應報告的意外事故,遠低于各行業的平均水平。
完備立法和嚴格執法是德國煤礦安全的首要保證。現行的礦業安全相關的法律主要有《聯邦礦業法》和《勞動保護法》,還有原料及化工保險機構(BG RCI)制定的一些安全衛生規章和技術標準等。《聯邦礦業法》對保障礦山安全生產,保護礦工人身安全和健康方面作了詳細規定,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規定了礦主必須確保員工的安全和健康,并根據礦山開采的實際情況制定安全技術規則和安全衛生計劃。《勞動保護法》對雇主的安全責任進行了明確的規定,雇主有保證員工安全與健康的責任和義務。由于德國是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也會依具體情況制定出適合本地特點的煤礦安全生產法律及規程。

表2 2004-2019年德國煤炭行業工傷事故人數及死亡人數
為保證煤礦安全生產法規切實執行,德國建立了嚴格的4個層次的執法監督機構,即州政府設立經濟能源與交通部,州下設專職礦山與能源管理處,各區設安全監察部,另設煤礦行業協會。這些機構從不同角度對煤礦安全生產實施監督和監察,共同協調處理煤礦安全生產中的問題。這樣,煤礦生產中可能存在的各種事故隱患,都能被及時發現和消除。
重視煤礦安全技術的研制與開發工作,采用先進的安全控制技術,是德國煤礦安全的重要保證。德國的礦山設備制造技術是世界一流的,礦井裝備自動化程度較高。近年來,德國采礦業引入“工業4.0”概念,通過“采礦 4.0”技術實施,實現自動化無人工作面采煤,最大限度地減少井下輔助運輸和崗點作業人數,降低勞動強度,減少事故發生概率,提升礦井自動化、智能化生產水平,達到煤礦生產安全高效目的。
7 發展前景
根據德國能源轉型的要求,德國未來將致力于降低所有終端用能部門的能耗,并通過可再生能源發電來滿足剩余的能源需求,可以預計未來德國的煤炭消費需求也會進一步縮減。雖然目前德國的井工開采已經基本結束,但德國的智能化開采技術仍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德國的礦山機械企業及相關的科研機構一直積極開拓海外業務,煤炭及電力企業也積極尋求轉型機遇。德國和中國同是經濟大國,在資源稟賦方面都具有富煤缺油少氣的特點,油氣對外依存度較高,因此在能源轉型方面面臨著許多相似的問題與挑戰。但是德國的煤炭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堅持立法的原則、在能源轉型中重視區域協調發展及土地復墾、煤礦關閉退出后的環境保護工作等經驗,仍值得中國借鑒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