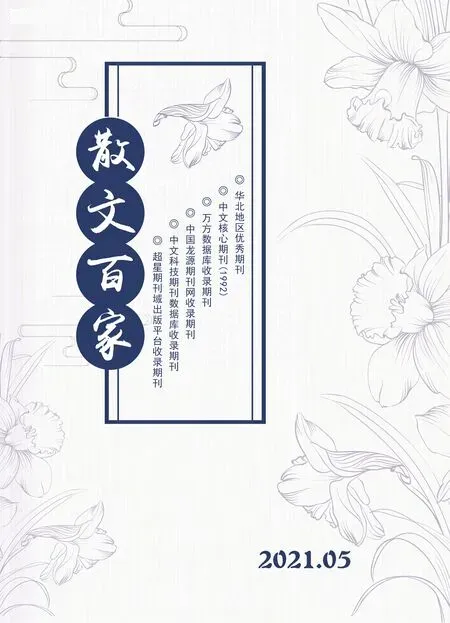竹添光鴻《論語會箋》札記(二則)
劉書含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竹添光鴻先生的《論語會箋》綱羅中日古今學者學說,點校矜慎,考證翔實。臺灣學者金培懿稱其爲“近代日本《論語》注釋轉爲日本《論語》研究,由舊學轉折新學之過渡”“可視爲日本傳統注疏學的總結”。《論語會箋》一書的影印發行,對于《論語》學的研究者與學習者來說無疑是一大幸事。筆者在讀書學習的過程中產生些許想法,揀擇一二撰成小文,以見教于方家。
一
《論語會箋》學而時習條有:“古者稱諸侯曰‘君’曰‘后’,故天子曰‘大君’曰‘元后’。”
按,“君”本用于表示王臣、職官之稱,可指稱諸侯、邦族首領、“國君”,后亦可用于稱呼天子。傳世典籍中“大君”確可訓爲天子,而出土文獻中未見“大君”之文例。金文中可訓爲“大君”的有“冢君”和“天君”,“冢君”實指稱諸侯、邦族首領,而“天君”指稱天子。典籍之“大君”,或即“天君”,以其形近而訛。
1.君。

周初承用此義:
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小盂鼎,《集成》02839)
由于周朝“要臣常由畿內外諸侯充任。”故而“君”除了表示王臣之一類,亦可用于表示天子或同級統治者對分封的區域統治者的稱呼,即“邦族首領、諸侯”:
衛以邦君厲告于邢伯、伯邑父、定白伯、?伯、伯俗父。(五祀衛鼎,《集成》02832)
五祀衛鼎記錄了畿內諸侯厲爲執行共王命令,與裘衛進行土地交易的過程,引文爲裘衛將邦君厲的交易條件轉告給邢伯等監督土地交易的執政大臣。裘衛爲作器人,銘文中“邦君”是其對“厲”的稱呼,下文皆省作“厲”。
列國諸侯即爲小國之君主,故而“君”也可以表示臣民對上層統治者的稱呼,即“國君”。如“膺受君公之易光。”(叔夷鐘,《集成》00275)
“君”的詞義范圍又由表示天子分封的區域統治者的“國君”,進一步擴大爲表示[臣子百姓]+[最高統治者]+[稱呼]的“天子、帝王”:
皇天眷命,奄奄四海,爲天下君。(《書?大禹謨》)
君,至尊也。(《儀禮?喪服》)
2.大君。
典籍中,“大君”即爲“天子”。《易?師》:“大君有命。”孔疏“大君,謂天子也。”而在出土文獻中,情況則不單一。筆者考察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匯數據庫發現,卜辭無“大君”及相關文例。金文、簡帛亦不見“大君”,與之相關的文例有“冢君”“天君”。
《說文》:“冢,高墳也。”郝懿行疏:“蓋冢本封土爲名,而凡大亦皆稱冢…然則大君謂之冢君,大宰謂之冢宰。”即“冢君”可訓爲“大君”。
王令毛公?邦冢君、徒馭、?人伐東國?戎,咸。(班簋,《集成》08431)
銘文中,王令毛公率軍攻伐犬戎,則“冢君”自非天子,而乃邦族首領、諸侯之謂。典籍亦可輔證。《書?泰誓上》:“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孔傳:“冢,大……稱大君,尊之。”所謂“冢”,是表示夸贊的修飾詞。

金文中,“天”有“上帝”之義,如“受天有大命。”(大盂鼎,《集成》02837)“天君”,即上帝之“君”、上帝之王臣,即帝王天子。
金文中常見“對揚王休”這一習語,“對揚天君休”與其對舉,其義顯豁,可知“天君”即爲“王”。后世訓爲天子的“大君”或源于“天君”,以其形似而訛。
此外,尹姞鼎中有“君蔑尹姞?”,此“君”乃上下文“天君”之省稱,即指“帝王”。然除此以外,西周未見“君”指稱“帝王”之文例,故“君”指稱帝王的用法并非來源于尹姞鼎。“君”的帝王義,除了如上文所言受“國君義”詞義范圍擴大的影響,亦有可能是因爲“天”“君”常常連用表示天子,久而久之該詞組意義固定,并凝固于“君”上,故而產生此義。
二
《論語會箋》學而時習條:“子,本人君之稱也,非大夫之稱也。”
按,“子”無單用稱呼人君、大夫之例。人君稱“天子”,或在祖先前自稱“小子”。貴族亦自稱爲“小子”。

古以君權為神所授,故稱帝王為“天子”:“對揚天子丕顯皇休。(利鼎,《集成》02804)”“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大雅?江漢》)”
可見,“子”與“天子”斷然有別,不可混爲一談。
李零指出“西周時期,貴族子弟多被稱爲
‘小子’,就連王,在神祖面前也自稱‘小子’。”其說可從。“小”金文作(《集成》2803),其義與大相對,訓爲微小。“小子”于金文中有兩種釋義,一種用法是作爲“未成年的人”,用于貴族子弟:
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仆學射。(靜簋,《集成》04273)
銘文爲王任命靜主司學宮的學射之事,即在大學中教貴族子弟習射藝。典籍亦有常見此用法,如《大雅?思齊》:“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鄭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
另一種用法是作爲自稱謙辭,或爲王臣貴族自謙爲“職位卑微低下的小官”:
有司暨師氏、小子佮射。(令鼎,《集成》02830)
天子在祭祀祖先時,爲表虔敬亦自稱“小子”,或稱“余小子”“臺小子”。《論語?堯曰》劉寶楠正義云:“稱小子者,王者父母天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銘文及典籍常見:

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書?湯誓》)
貴族與天子同自稱“小子”。蓋因先秦時期,等級、禮儀制度雖然分明,但于語言表達上并無針對等級進行嚴格界定。
如前文論述的“君”既可用于指稱王臣諸侯,也可以用于指稱天子;“朕”可以用于君主自稱,大盂鼎中康王之言可證:“盂!若敬乃正,勿灋朕令”。“朕”亦可用于貴族官員,如《離騷》:“朕皇考曰伯庸”;
周王之命爲“誥”,《書?酒誥》:“文王誥教小子。”諸侯亦可“誥”于王,《書?太甲下》:“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