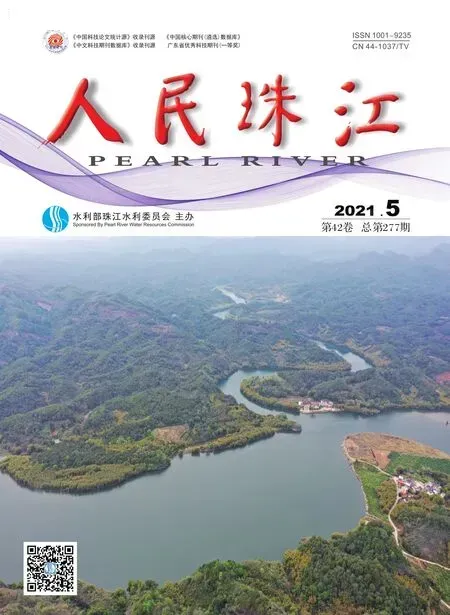沿黃取用水對黃河干流主要斷面徑流影響分析
祁永輝,澈麗木格,余煌浩,錢 宇,李彬權(quán)*
(1.中國電建集團(tuán)青海省電力設(shè)計(jì)院有限公司,青海 西寧 810008;2.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通遼市河湖管理中心,內(nèi)蒙古 通遼 028000;3.河海大學(xué)水文水資源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98)
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黃河流域工農(nóng)業(yè)發(fā)展迅速,生產(chǎn)和生活用水增加。再加上黃河流域地處干旱、半干旱地區(qū),本身水少沙多,沿黃各省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人民群眾生活用水對黃河取水依賴很大[1]。但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雙重影響下,黃河水資源面臨嚴(yán)峻挑戰(zhàn),20世紀(jì)70年代開始,黃河下游河段甚至經(jīng)常斷流,影響了生產(chǎn)發(fā)展和生活需要。沿黃地區(qū)取耗水直接影響黃河流域水文情勢,如徑流量及其年內(nèi)分配等[2],因此,研究沿黃取用水條件下的黃河干流主要斷面徑流變化對認(rèn)識黃河水資源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張建云等[3]分析發(fā)現(xiàn),黃河上游唐乃亥站實(shí)測年徑流量為非顯著性減少趨勢,花園口站實(shí)測徑流量呈現(xiàn)顯著性減少趨勢。Wang等[4]研究表明在1919—2018年,黃河流域年降水量總體變化不大,但日極端降水量則隨著氣溫每增加1℃而增加7%。較多研究表明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取用水等人類活動是黃河徑流急劇減少的主要原因[5-8]。王煜等[9]指出,由于沿黃各省區(qū)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程度和速度不一致改變了黃河流域的用水格局,現(xiàn)行的“87分水方案”與流域供需形勢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離,對省區(qū)用水的指導(dǎo)作用降低,不利于有效控制全河的取水總量。賈紹鳳等[10]在考慮預(yù)留生態(tài)水量、下游南水北調(diào)及海水利用及上中游部分產(chǎn)業(yè)發(fā)展需水條件下,提出了向黃河上中游分配更多水量指標(biāo)的水資源戰(zhàn)略配置方案。
本文選擇黃河干流上中下游重要控制斷面,應(yīng)用代表性水文站的實(shí)測流量資料和1998—2019年《黃河水資源公報(bào)》資料[11],分析年季尺度徑流變化以及不同流域分區(qū)取用水的影響。
1 數(shù)據(jù)與方法
1.1 基礎(chǔ)數(shù)據(jù)
a)干流蘭州站(1919—2018年)、花園口站(1919—2018年)、利津站(1950—2018年)月徑流資料。數(shù)據(jù)來源于《黃河流域水文年鑒》和黃河水利委員會信息中心,數(shù)據(jù)質(zhì)量良好,主要用于分析三站年季尺度長期徑流變化趨勢。
b)干流主要控制水文站實(shí)測年徑流資料(1998—2019年)。收集得到黃河干流上中下游主要控制水文站(唐乃亥、貴德、蘭州、下河沿、石嘴山、頭道拐、龍門、三門峽、花園口、高村、利津)1998—2019年的年徑流量,數(shù)據(jù)來源于《黃河水資源公報(bào)》。
c)沿黃省區(qū)(分區(qū))取、耗水資料(1998—2019年)。收集得到沿黃各省區(qū)(及不同分區(qū))1998—2019年間年尺度取水量、耗水量、地表取水量和地表耗水量資料,數(shù)據(jù)來源于《黃河水資源公報(bào)》。
1.2 分析方法
1.2.1Mann-Kendall趨勢檢驗(yàn)方法
非參數(shù)Mann-Kendall(MK)趨勢檢驗(yàn)方法[12-13]是基于統(tǒng)計(jì)學(xué)上的假設(shè)檢驗(yàn)進(jìn)行的,對一資料樣本X={x1,…,xn},n>10而言,MK檢驗(yàn)提出原假設(shè)H0和備擇假設(shè)H1。H0:樣本系列在時間上隨機(jī)排列的,無顯著性趨勢;H1:樣本系列在時間上存在顯著性的上升或下降趨勢。
MK檢驗(yàn)的統(tǒng)計(jì)量S可用式(1)估計(jì):
(1)

(2)
式中xj、xk——樣本中第j、k個數(shù)據(jù)(j>k)。
當(dāng)樣本總量滿足n>10時,統(tǒng)計(jì)量S服從均值為0的正態(tài)分布,其方差為:
(3)
根據(jù)式(3)可進(jìn)一步計(jì)算統(tǒng)計(jì)量Z:

(4)
式中,統(tǒng)計(jì)量Z服從標(biāo)準(zhǔn)正態(tài)分布。當(dāng)Z大于零時,說明樣本系列呈上升趨勢;當(dāng)Z小于零時,說明樣本呈下降趨勢。根據(jù)顯著性水平α從標(biāo)準(zhǔn)正態(tài)分布表中查出臨界值(雙尾檢驗(yàn))Zα/2。當(dāng)統(tǒng)計(jì)量Z的絕對值大于Zα/2時,則拒絕原假設(shè)H0而接受備擇假設(shè)H1,反之則接受原假設(shè)。
若序列中存在上升或下降的趨勢,假定其為線性的,則樣本數(shù)據(jù)的坡度可根據(jù)Sen法[14]進(jìn)行估計(jì)。在序列中,取不同的2個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組合,計(jì)算坡度值βj:
(5)
這樣,對樣本大小為n的序列而言,式(5)可以計(jì)算得到N=n(n-1)/2個坡度值。取N個坡度值的中值β為樣本的坡度。坡度β的正或負(fù)也分別反映了序列的上升或下降的趨勢。
1.2.2水文變異綜合診斷方法
謝平等[15]提出的水文變異綜合診斷方法,可用于檢測水文序列的突變點(diǎn)。該方法假定時間序列X={x1,…,xn}中的可能突變點(diǎn)位置為τ(1<τ (6) 因此,滿足式(7)的目標(biāo)函數(shù)最小的τ0就是序列中的突變點(diǎn)位置。 Vn(τ0)=min{Vn(τ)}, 2≤τ≤n-1 (7) 2.1.1年際變化分析 圖2為干流蘭州、花園口、利津三水文站年徑流量及5年滑動平均序列,可以看出自1994年開始中游花園口站實(shí)測徑流量低于上游蘭州站(根據(jù)5年滑動平均系列對比),表明蘭州—花園口河段取耗水量越來越大,在1994年后基本保持中游花園口站實(shí)測徑流量小于上游蘭州站的現(xiàn)象。對比下游利津站與中游花園口站年徑流量系列(1950—2018年)可知,1970年代中期前,兩系列徑流量相差不大、變化相對穩(wěn)定,這與兩站控制的集水面積相關(guān),花園口站以下分區(qū)面積僅占流域總面積的2.9%,產(chǎn)水量占比較小。 圖2 黃河干流三站年徑流量變化情況 根據(jù)1919—2018年系列統(tǒng)計(jì),上游蘭州站多年平均實(shí)測年徑流量為309.16億m3,變化坡度值為-0.204億m3/a,MK趨勢檢驗(yàn)發(fā)現(xiàn)無顯著性變化趨勢,其原因主要是數(shù)據(jù)系列較長,整體變化不顯著,但不同時期仍有明顯趨勢性變化。例如,盡管1919—1949年和1950—2018年兩系列多年平均實(shí)測年徑流量相差無幾(分別為308.97億、309.25億m3),但是在變化趨勢上分別為顯著性增加趨勢(99%置信度)和顯著性減少趨勢(95%置信度),坡度分別為3.64億、-0.84億m3/a。在年代際變化尺度上,1960年代平均年徑流量最大(357.93億m3,為多年平均值的1.16倍),20世紀(jì)90年代、21世紀(jì)00年代的平均年徑流量相對較小(259.82億、267.59億m3,為多年平均值的85%左右)。 根據(jù)1919—2018年系列統(tǒng)計(jì),中游花園口站多年平均實(shí)測年徑流量為401.75億m3,坡度值為-2.86億m3/a,MK趨勢檢驗(yàn)表現(xiàn)為顯著性減小趨勢(99%置信度)。對比1919—1949年和1950—2018年兩系列可發(fā)現(xiàn),二者分別為99%置信水平的顯著增加和顯著減少趨勢,坡度分別為5.74億、-4.23億m3/a,這與上游蘭州站對比情況類似,但兩系列的均值相差較大(分別為479.45億、366.84億m3)。在年代際變化尺度上,年徑流量變化趨勢與上游蘭州站相似,在1960年代均值最小(505.92億m3,為多年平均值的1.26倍),1990年代、2000年代的平均年徑流量相對較小(256.92億、231.57億m3,為多年平均值的60%左右)。 下游利津站年徑流量系列時間期限為1950—2018年,多年平均年徑流量為293.51億m3,MK趨勢分析表明,與上中游兩站變化類似,表現(xiàn)為顯著性減少趨勢(99%置信度),坡度值為-6.19億m3/a。三站變化對比可知,在同一時期(1950—2018年)內(nèi),自上游向下游,年徑流量減少幅度呈增大趨勢,表明中下游取用水量日益增大。 利用水文變異綜合診斷方法分析上述三站年徑流量系列的突變情況,結(jié)果表明:上游蘭州站有2個突變點(diǎn),分別為1932、1985年(其中1985年為最顯著突變年份),中游花園口站、下游利津站的年徑流量系列突變年份均為1985年。總體看,干流三站均表現(xiàn)為年徑流量減少趨勢和較為一致的突變點(diǎn)位置,表明受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雙重影響,黃河流域干流上中下游三站水文情勢變化基本一致。 以突變年份為分界點(diǎn)將整個時期劃分為多個階段,統(tǒng)計(jì)不同時期的徑流量均值變化情況見表1。上游蘭州站第二時期(1933—1985年)的多年平均年徑流量比前一時期增加30.64%,第三時期(1986—2018年)的多年平均年徑流量比第二時期減小17.60%,整個研究時期表現(xiàn)為先增加再減小的趨勢(但根據(jù)圖1中MK檢驗(yàn),該趨勢并不顯著)。中游花園口站突變點(diǎn)前后的多年平均年徑流量減少43.35%,而下游利津站突變點(diǎn)前后的多年平均年徑流量的變幅則更大,減小幅度達(dá)62.62%。 圖1 黃河水系及部分干流主要控制站示意 表1 黃河干流三站年徑流量序列突變前后均值變化情況 2.1.2汛期與非汛期變化分析 黃河干流蘭州、花園口、利津三站年內(nèi)汛期與非汛期徑流量分配情況統(tǒng)計(jì)見表2。蘭州站汛期(6—9月)徑流量為161.58億m3,占全年徑流量的51.4%,最大可達(dá)68.9%(1933年),最小只有36.3%(1971年);7—8月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28.1%,最大可達(dá)47.5%(1933年),最小只有16.6%(2000年)。非汛期徑流量為147.58億m3,占全年徑流量的48.6%。徑流量平均每年7月最大、8月次大,2月最小、3月次小,最大是最小的4.6倍。歷年最大月徑流量是1981年9月的109.90億m3,占當(dāng)年徑流總量的26.4%,是多年平均徑流量的35.5%。汛期和7—8月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比重在年代際變化上總體呈減小趨勢,汛期由1930年代的59.8%非單調(diào)減至2010年代的44.7%,減少了15.1%,表明徑流量年內(nèi)分配趨向均勻。 表2 黃河干流三站徑流量年內(nèi)分配統(tǒng)計(jì) 花園口站汛期徑流量為202.85億m3,占全年徑流量的48.9%,最大可達(dá)69.4%(1933年),最小只有24.3%(2001年);7—8月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28.0%,最大可達(dá)52.2%(1933年),最小只有8.5%(2003年)。非汛期徑流量為198.90億m3,占全年徑流量的51.1%。據(jù)統(tǒng)計(jì),徑流量平均每年8月最大、9月次大,2月最小、1月次小,最大是最小的4.8倍。歷年最大月徑流量是1949年9月的153.06億m3,占當(dāng)年年徑流量的22.3%,是多年平均年徑流量的38.1%。汛期和7—8月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比重在年代際變化上總體呈減小趨勢,這與上游蘭州站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表明徑流量年內(nèi)分配趨向均勻。其中,蘭州—花園口區(qū)間的水庫調(diào)節(jié)作用是重要原因。 利津站汛期徑流量為150.41億m3,占全年徑流量的51.3%,最大可達(dá)55.7%(1999年),最小為45.0%(1979年);7—8月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30.9%,最大可達(dá)35.3%(1999年),最小只有24.7%(1979年),極值出現(xiàn)時間與汛期的一致,表明7—8月徑流量是汛期徑流量的最主要貢獻(xiàn)部分。非汛期徑流量為143.15億m3,占全年徑流量的48.7%。據(jù)統(tǒng)計(jì),徑流量平均每年8月最大、9月次大,2月最小、1月次小,最大是最小的5.8倍。歷年最大月徑流量是1964年9月的183億m3,占當(dāng)年徑流總量的18.8%,是多年平均徑流量的62.3%。與上中游兩站不同,利津站汛期和7—8月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比重基本保持穩(wěn)定,變幅不大,這是由于黃河流域徑流主要來源于花園口站以上的上中游流域,在自然坦化作用下,徑流量年內(nèi)分配相對均勻,此外,上中游水庫調(diào)節(jié)作用也是重要貢獻(xiàn)之一。 為更好對比近年來流域上下游徑流變化情況,圖3—5分別展示了干流上游(唐乃亥、貴德、蘭州、下河沿、石嘴山)、中游(頭道拐、龍門、三門峽、花園口)和下游(高村、利津)共11個站點(diǎn)1998—2019年間實(shí)測年徑流量系列。盡管從前文干流蘭州、花園口、利津三站長系列資料分析得到年徑流量呈遞減趨勢,但是1998—2019年總體變化趨勢是增加的,且這種增大趨勢在圖中11個站點(diǎn)均能體現(xiàn)。由圖6可知,黃河流域面平均降水量在1998—2019年呈增多趨勢,因此,降水增多應(yīng)是干流各站點(diǎn)實(shí)測年徑流量增大的重要原因。 圖3 黃河上游五站實(shí)測年徑流量系列(1998—2019年) 圖4 黃河中游四站實(shí)測年徑流量系列(1998—2019年) 圖5 黃河下游兩站實(shí)測年徑流量系列(1998—2019年) 圖6 黃河流域面平均降水量系列及其線性趨勢(1998—2019年) 圖7給出了干流11站1998—2019年間年徑流量系列箱形圖。按上下游年徑流量對比來看,蘭州—頭道拐、花園口—利津2個區(qū)間的下游徑流量小于其上游河段,表明這2個區(qū)段流經(jīng)的地區(qū)(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河南和山東等省區(qū))取用水量對干流徑流影響較大。 圖7 黃河干流11站1998—2019年間年徑流量系列箱形圖 將黃河全河劃分為蘭州以上、蘭州至頭道拐、頭道拐至龍門、龍門至三門峽、三門峽至花園口、花園口以下、內(nèi)流區(qū)等共7個分區(qū),分析1998—2019年間各分區(qū)的取耗水情況。圖8為黃河各分區(qū)1998—2019年取水總量、耗水總量、地表取水量、地表耗水量多年均值系列及各取/耗水量的變化范圍。對比可知,取水量最大的是蘭州至頭道拐區(qū)間,年均取水總量為183.92億m3,花園口以下次大(為127.14億m3,主要發(fā)生在花園口至利津區(qū)間),取水量最小的是內(nèi)流區(qū)的4.09億m3,次小的為頭道拐至龍門區(qū)間的16.95億m3。從耗水量來看,年均耗水量最大的是蘭州至頭道拐的124.12億m3(占其取水總量的68%),其次為花園口以下的120.42億m3,耗水量最小是內(nèi)流區(qū)的3.30億m3(占其取水總量的80%),次小的為頭道拐至龍門區(qū)間的14.11億m3;這與沿黃各分區(qū)取水總量的大小規(guī)律基本一致。 圖8 流域不同分區(qū)1998—2019年間取耗水情況 地表取水是沿黃各省(區(qū))取水的主要方式,因而不同流域分區(qū)的地表取水量、地表耗水量的對比情況與取耗水總量沿程變化基本一致。地表取水量最大的是蘭州至頭道拐區(qū)間的155.32億m3,占該分區(qū)取水總量的85%,地表取水量最小的是內(nèi)流區(qū)的1.29億m3,占該分區(qū)取水總量的31%,這兩個分區(qū)也分別是取水總量最大、最小的兩個分區(qū)。在地表耗水量方面,與地表取水量反映的各分區(qū)極值一致,最大的地表耗水量發(fā)生在蘭州至頭道拐區(qū)間(104.32億m3),最小值發(fā)生在內(nèi)流區(qū)(1.07億m3)。 取耗水量相對集中在蘭州至頭道拐區(qū)間的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等地區(qū),以及花園口以下的河南、山東兩省。總體來看,地表取水量在取水總量中比重較大,除內(nèi)流區(qū)僅占約31%外,頭道拐至龍門、龍門至三門峽、三門峽至花園口等區(qū)間地表取水量在取水總量中占比在50%左右,蘭州以上、蘭州至頭道拐、花園口以下等區(qū)間的地表取水量在取水總量中占比約85%。此外,就耗水量在其取水量中占比而言,無論是取(耗)水總量還是地表取(耗)水量,蘭州至頭道拐區(qū)間取水量的利用率(即耗水量除以取水量的比值)最低,約為68%,其他流域分區(qū)的比值均大于75%,主要的可能原因是蘭州至頭道拐區(qū)間取水中的農(nóng)業(yè)用水占較大比重,灌溉用水利用率低。 分析取耗水對干流蘭州、頭道拐、龍門、三門峽、花園口等分區(qū)斷面干流徑流量的影響,表3列出了各站1998—2019年間多年平均實(shí)測徑流量、天然徑流量、地表耗水量和地表水還原水量。總體看,各斷面的地表還原水量在天然徑流量比重的多年平均值都是正值,且自上游貴德站開始向下游增加趨勢,中下游斷面的比重都在43%以上,在利津站取值達(dá)到最大(64.6%),可推斷取水主要發(fā)生在蘭州以下的中下游地區(qū)。 表3 干流7站多年平均實(shí)測徑流量、天然徑流量、地表耗水量和地表水還原水量 地表耗水量與地表還原水量的比值可以反映沿黃河道取用水對河道徑流量影響的貢獻(xiàn)。統(tǒng)計(jì)結(jié)果表明,貴德以上分區(qū)耗水對河道徑流量影響較小,在減小的水量中僅有14.3%是由用耗水造成的,其余85.7%是貴德站以上龍羊峽水庫蓄水導(dǎo)致的。在蘭州以上分區(qū),耗水對徑流減少的貢獻(xiàn)比例上升至75.6%,成為徑流減少的主要原因。再往下游的頭道拐、龍門、三門峽、花園口和利津等站點(diǎn)以上分區(qū)的耗水貢獻(xiàn)比例大幅增加至約95%左右。因此,從整個流域?qū)用婵矗攸S取耗水活動對黃河干流年徑流量的影響較大,是徑流減少的最主要貢獻(xiàn)成分。 統(tǒng)計(jì)分析各單獨(dú)流域分區(qū)的河道天然徑流量、地表水還原水量和地表耗水量情況(表4),結(jié)果表明:除蘭州—頭道拐、花園口—利津2個分區(qū)外,取耗水、水庫蓄水等人類活動對貴德以上徑流量影響最小,對河道天然徑流量變化的影響比例僅為5.7%(其中地表耗水量僅占天然徑流量0.8%),而貴德—蘭州分區(qū)的影響比例增大至17.3%(其中地表耗水量的比重為16.3%);在流域中下游分區(qū),人類活動的影響進(jìn)一步增大,特別是在龍門—三門峽分區(qū),地表還原水量占河道天然徑流量的比例達(dá)到55.4%(其中地表耗水量占比為54.8%)。此外,需要注意蘭州—頭道拐分區(qū)的天然徑流量計(jì)算結(jié)果是-15.26億m3,這主要原因是該分區(qū)取水、蒸發(fā)、河道滲漏等影響較大,造成頭道拐站的河道天然徑流量小于其上游的蘭州站;花園口—利津分區(qū)以河道匯流為主,區(qū)間匯水面積較小,因此該區(qū)間2005—2019年多年平均天然徑流量為10.75億m3是合理的,但該區(qū)段人類活動(取水、水庫蓄水等)對河道徑流的影響最大,本地水遠(yuǎn)遠(yuǎn)不夠使用,大量取耗水的是上游來水。 表4 各分區(qū)多年平均天然徑流量、地表還原水量和地表耗水量 a)根據(jù)1919—2018年系列統(tǒng)計(jì),上游蘭州站多年平均實(shí)測年徑流量為309.16億m3,變化率為-0.204億m3/a,無顯著性變化趨勢;中游花園口站多年平均實(shí)測徑流量為401.75億m3,變化率為-2.86億m3/a,表現(xiàn)為顯著性減小趨勢;下游利津站多年平均年徑流量為293.51億m3(1950—2018年),表現(xiàn)為顯著性減少趨勢,變化率為-6.19億m3/a。三站變化對比可知,在同一時期(1950—2018年)內(nèi),自上游向下游,年徑流量減少幅度呈增大趨勢,表明中下游取用水量日益增大。 b)1998—2019年黃河年徑流量變化趨勢則呈增加趨勢,且這種增大趨勢在干流上下游11個站點(diǎn)均有所反映。分析原因發(fā)現(xiàn),流域面平均降水量在1998—2019年呈增多趨勢,因而可能導(dǎo)致干流各站點(diǎn)實(shí)測年徑流量的增大。此外,2012—2017年干流各站點(diǎn)年徑流量明顯減少,結(jié)合降水量變化過程來看,人類活動應(yīng)是主要原因。 c)1998—2019年,流域多年平均取水、耗水總量分別為503.38億、395.09億m3,取水、耗水總量的變化均呈增大趨勢,表明黃河流域各行業(yè)取用水量不斷增加。取耗水、水庫蓄水等人類活動對貴德以上徑流量影響最小,貢獻(xiàn)比例僅為5.7%,而貴德—蘭州分區(qū)的影響比例增大至17.3%;在流域中下游分區(qū),取耗水、水庫蓄水等干擾的影響進(jìn)一步增大,特別是在龍門—三門峽分區(qū),地表還原水量占河道天然徑流量的比例達(dá)到55.4%。
2 結(jié)果與討論
2.1 蘭州、花園口、利津三站徑流變化分析




2.2 上下游11站1998—2019年間徑流變化分析





2.3 流域分區(qū)取耗水分析

2.4 取耗水對干流徑流量影響分析


3 結(ji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