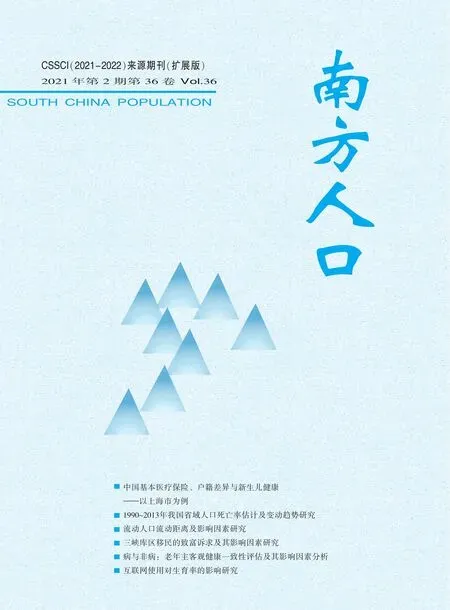病與非病: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評估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吳敏 熊鷹
(1. 湖北經濟學院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430205;2.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1 研究背景
老年健康而美。健康不僅是高質量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提高預期壽命、促進積極老齡化的發展方向。《“十三五”健康老齡規劃》指出,建立健全老年健康支持體系,積極推進老年健康促進和健康教育工作,提高老年健康管理水平。隨著物質經濟發展,新時期老年健康需求以及健康認知不斷變化,對健康的理解和定義也賦予時代新特征。一方面,物質條件豐富快速釋放老年健康需求,尋醫問診、保健養生、甚至過度醫療等行為愈發普遍;另一方面,不少老年人忽視健康要求,倡導不健康生活方式,以致造成嚴重的健康隱患。個體如何認知疾病和健康將決定其采取某種有益于健康或放棄某種危害健康的行為[1],而有效認知健康、以及健康認知差別將成為影響健康管理的關鍵。“病與非病”作為心理認知的重要原則,強調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統一性、心理活動的內存協調性及其對行為的重要影響[2]。老年人主觀健康感知和客觀軀體健康若失去同一,即疑“病”、或盲目健康自信而忽視健康管理,必然造成嚴重風險隱患。
現有研究多將主觀健康作為健康的有效標準[3]-[4],并由此展開健康公平、健康福利[5]-[6]、健康與醫療[7]-[8]等研究。然而,在特殊情境或目的中,所處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個體可能夸大或縮小健康感知,從而呈現“知情意”不一致[9]。對老年人而言,年齡增長帶來的記憶、理解等認知功能弱化,加劇了健康感知的非準確性[10];特別是初老過程中,身體機能逐漸衰弱以及高發的疾病風險,強烈沖擊健康感受。那么,老年人獨特的健康體驗是否會混肴“病與非病”的界限,從而導致主觀健康感知在測量真實健康上的非準確性?據此,本研究從健康認知風險出發,對老年人主客觀健康的一致性程度進行評估。老年健康隨年齡增長而緩慢衰退,較少在某個時間段受外在因素突發變動,故本文重點聚焦于主客觀健康隨年齡增長而呈現的動態變化,并圍繞不同群體全面闡述老年主客觀健康的特征差異,以期為指導老年健康生活方式、就醫等健康管理行為提供有效依據。
2 文獻綜述
健康是復雜且多維的概念。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健康不僅是一個人身體沒有出現疾病或虛弱現象,也是一個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會上的完好狀態,傳統時代無病即健康在現代社會發生較大變化。諸多健康概念包括了自評健康[11]、主觀健康、客觀健康[12]、心理健康、軀體健康[13]等方面,而針對一般化軀體健康、生理健康的討論中,不少研究將自評健康作為軀體健康的直接代理變量并展開相關研究[14]-[17]。自評健康最早由Suchman 等人[18]提出,強調個體對健康狀況作出的主觀評價和期待,此后,諸多學者對該概念進行了充實和完善,并衍生出自測健康、主觀健康等類似表述[19]。然而,當自我感知健康和醫學觀察健康不一致時,自評健康作為健康測量的代替將發生偏差,從而導致個體高估或低估健康的狀態,并可能導致嚴重隱患[20]。
自評健康作為個體主觀認知和健康期望的體現,在反映客觀健康上存在難以解決的缺陷。一是群體異質性偏差。除了客觀存在的軀體疾病,經濟條件、文化背景、父母健康、健康風險偏好[21]以及城鄉[22]等均會導致個體對健康理解的差異;客觀的身體狀態和疾病不再是主觀健康認知的唯一條件[23]-[24]。二是情境因素影響健康評價的穩定性。例如,當個體先后處于在婚和不在婚兩種狀態時,報告的健康水平相差甚遠,婚姻的支持作用極大促進了個體的積極健康認知[25];對比失落、沮喪、遭遇挫折等情境,處于積極、心情愉悅狀態的個體毫不例外匯報更高的健康水平[26]。三是特殊目的性。在尋求工作、構建他人對自己的積極認知時,個體傾向于報告更好的健康狀態;反之,當尋求政府扶貧補助、殘障幫扶中,往往呈現低的健康狀態以獲取高的津貼或救助[27]。另外,在疾病尚未對身體、生活構成明確威脅時,也多出現系統性拔高自我健康的錯誤[28]。
雖然主觀健康在度量客觀健康時可能存在偏差,但該指標仍被廣泛使用[4]。與反映客觀健康的醫學觀察或體檢數據不同,自評健康數據資料通過自評健康量表、自評健康問答等即可有效獲取。部分研究證實了自評健康與客觀健康之間的相關性。身體質量指數(BMI)正常、血壓穩定等健康狀態好的人匯報出高的主觀健康[20]。睡眠作為健康的外在表現之一,與自評健康高度正相關,自評健康高者的睡眠質量也更高[29]。而患有癌癥、心血管疾病等患者的自評健康差,特別是重癥患者的自評健康與軀體健康呈現高度一致[30]-[32]。一項大規模的研究也表明,住院病人自評健康狀況普遍較差,自評健康報告良好的比例甚微[3]。
自評健康較好體現了個體自我感知的健康狀態與既有的關于自身健康的知識,但難以反映個體無法感知的機體健康問題,特別是涉及到不同異質性群體健康公平、健康福利等健康比較的研究和應用中,自評健康的適用性值得商榷。已有關于主觀健康和客觀健康一致性的討論和研究中,多從相關性出發對兩者進行相似性比較,而基本的關聯并未有效表達出主客觀健康之間的差距以及差距的程度。據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探討了老年主觀健康、客觀健康之間的一致性程度,并圍繞個體稟賦差異因素,探討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城鄉等對主客觀健康差異的影響,以充分挖掘老年健康認知的形成機制。
3 數據與方法
3.1 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2015 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和血檢數據。Charls 數據以45 歲及以上中老年人為調查對象,調查內容涵括老年人基本人口學特征、家庭、健康狀況和功能、醫療保健和保險、職業和養老金、收支和資產、住房等信息。Charls 數據于2011 年的基線調查中首次設置了血檢和體檢數據模塊,以收集老年血壓、身體質量、血檢等數據,2013 年、2015 年的追蹤調查中繼續保留了血檢和體檢等調查項。根據研究目的,本文選取了參與血檢和體檢的調查對象,最后納入分析的有效樣本數為9004。
3.2 變量測量
(1)客觀健康。客觀健康是基于體魄、疾病、行動力等反映出的一種綜合狀態,是個體外在軀體的良好呈現,類似的表述有軀體健康、生理健康等。本文傾向于基于醫學可靠的觀察和判斷,對個體反映的疾病或亞健康進行探討,并通過可測量的數值來衡量。已有研究關于客觀健康的度量繁雜多樣,如慢性病[33]、某種具體的疾病[30]、身體質量指數[20]等。然而,準確衡量個體的客觀健康或生理健康并非易事,單一健康指標不足以反映身體健康狀態,即使通過常規性體檢也難以實現。幸運的是,CHARLS 血檢數據基本上涵括了常規的身體素質指數、神經系統、行動能力、免疫系統、慢性病等健康信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我們繼續豐富客觀健康的測量標準,從身體質量指數(BMI)、血壓、肺活量、平衡能力、行動能力、血常規、慢性病等對老年客觀健康進行綜合評價(見表1)。為了防止癌癥等特殊重癥疾病對個體健康狀態的損害及其可能造成的極度負向認知,將少數癌癥患者樣本排除在外。另外,所有納入分析的對象皆具有基本獨立思考和回答問題的能力。
為了對不同觀測對象的客觀健康進行有效測量并予以比較,本文將以上述健康指標與科學的正常醫學區間進行比照,若指標處于正常范圍將其設定為1,處于正常值以外則為0;進一步將所有指標均處于正常狀態(變量值為1)的老年人的客觀健康分值設定為100,并作為基準測量點。為了有效測量其他老年人到基準點之間的距離,我們利用歐氏距離進行樣本(類)與樣本(類)之間值的度量。歐氏距離是對樣本進行相似性或差異性分類的常規方法,源自歐氏空間中兩點間的距離公式。二維平面上兩點a(x1,y1)與b(x2,y2)間的歐氏距離為:;三維空間的歐氏距離公示則為:;兩個 n 維向量 a(x11,x12,…,x1n)與 b(x21,x22,…,x2n)間的歐氏距離為:;也可以表示成向量運算的形式:。在本文的處理過程中,將健康指標數據(X)理解成一個M×N 的矩陣,其中M 為樣本數,N 為所有反映客觀健康的指標數量(11),那么X 矩陣M 行的每一行作為一個N 維向量,然后計算M 個向量兩兩間的距離。根據基準點的原始百分值以及向量間的距離,依次確定其他健康狀態樣本的分值。歐氏距離計算結果表明,與基準點最遠距離的個體的健康得分為30.52,平均健康分值為75.21,整體的健康狀態不容樂觀。

表1 客觀健康的指標選取及定義
(2)主觀健康。主觀健康即自評健康,自測健康,是個體基于軀體健康狀況作出的主觀評價。本文沿用國際上常用的自測健康評定量表(SRHMS),包括身體癥狀與器官功能、日常生活功能、身體活動功能、心理情緒、認知功能、角色活動與社會適應、社會支持、健康總體自測等內容。主觀健康指標雖然與自測健康評定量表(SRHMS)基本條目保持一致,但條目問答選項分值的設置略有區別(見表2)。各個回答項方向一致化處理后,將所有答項統一設置為“1、2、3、4”并進行分值加總,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態越好。
(3)主客觀健康差異。為了對主觀健康、客觀健康之間的一致性程度進行度量,利用離差標準化(Min-Max Normalization)對健康分值進行歸一化處理,并使分值處于0-100 之間。歸一化處理后,主觀健康平均分值為69.17,客觀健康平均分值為59.40,前者平均高出后者9.8 分,且通過顯著性檢驗。進一步對主客觀健康之間的相對差距和一致性程度進行比較后,生成主客觀健康差異變量,即主觀健康與客觀健康的差。若主觀健康得分高于客觀健康,將其賦值為1;若主觀健康得分低于客觀健康,則為0。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主客觀健康差異是一種相對狀態的度量,如果某被訪者的主觀健康在全人群中處于低值,而客觀健康處于高值,那么該個體屬于典型的主客觀健康不一致,且低估軀體健康。
(4)其他控制變量。基于已有研究,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了年齡、性別、城鄉、收入、居住條件、子女數、受教育程度、是否在業等,以尋求影響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的因素。被訪者的平均年齡為59 歲,女性略多于男性,農村老人占比超過七成,平均子女數2.7 個。鑒于不少老人處于退休狀態,故將職業狀態處理為是否在業(二分類變量),如果從事經濟活動,將其賦值為1,如果沒有從事任何經濟活動,將其賦值為0。老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初中及以下占比一半以上。超過7 成的被訪者處于在業中,這與農村老年人占比偏多直接相關。平均家庭收入為15663元,整體水平偏低。居住條件處理為二分類變量,1 為住宅配備熱水器、空調等現代化設施,0 為住宅無相應現代化設施。其中,居住條件偏好的樣本占比超過6成。

表2 主觀健康的指標選取及定義
3.3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本文首先利用歐式距離測量樣本與樣本、類與類之間的距離以獲取客觀健康得分;在此基礎上,采用離差標準化將主觀健康和客觀健康分值進行歸一化處理,并利用雙變量描述分析,探討不同人口學特征、社會經濟特征以及家庭特征的老年人主客觀健康分布。基于主客觀健康之間相對大小生成的二分類變量,采用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老年主客觀健康一性質的影響因素,以期挖掘健康認知風險的作用機制。
4 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的變動趨勢及特征差異
4.1 主觀健康高于客觀健康,兩者之間隨年齡增長而交替錯落
隨著年齡增長,老年人主觀健康不斷下降,客觀健康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主客觀健康之間交替錯落(見圖1)。主觀健康隨年齡增長保持穩定的負向趨勢,一定程度上符合個體對生命發展周期的認知規律。年齡作為決定老年健康的關鍵因素,個體健康期望隨年齡增長而不斷降低,并以老年式理性認知健康。與預期相反,客觀健康并未隨年齡增長而呈現相應下降趨勢,在臨近退休時快速上升,并持續到古稀之年,隨后開始快速衰退。退休作為重要的生命事件,對健康、生活態度等具有正向促進作用[34],特別是退休前后的臨近狀態,個體身心壓力釋放而帶來的健康正效應明顯。而后步入高齡期,嚴重衰退的機體功能以及不斷出現的疾病,導致高齡老人的軀體健康快速下降。結合主客觀健康之間差異來看,兩者隨年齡變化并非呈現同步特征:步入花甲之前,老年人主觀健康高于客觀健康;臨近60 歲并至75 歲老年人主觀健康低于客觀健康,而高齡老人的主觀健康則高于客觀健康。

圖1 主客觀健康的年齡變動趨勢
4.2 男性主客觀健康不一致程度高于女性,且主觀健康顯著高于客觀健康
男性主客觀健康不一致程度高于女性(見圖2):男性主客觀健康的平均值分別為71.73、61.04、女性分別為64.54、58.72; 男 性主客觀健康均高于女性,且主客觀健康差值(10.69)高出女性(5.82)近一倍。老年男性健康要求低,一定程度上源于吸煙、喝酒等諸多不健康生活方式,從而造成了基于同等客觀健康狀況而報告更高主觀健康的結果。這一健康認知將可能增加男性繼續不健康生活方式、忽視健康管理的風險隱患。男性主客觀健康隨年齡增長波動大,低齡以及高齡男性的主觀健康遠高于客觀健康;女性主客觀健康隨年齡增長波動較為平緩,但低齡女性的健康積極認知逆轉為高齡期的消極認知。

圖2 主客觀健康隨年齡變動的性別差異
4.3 受教育程度高者的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程度高,但略微低估個體健康
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客觀健康狀態越好(見圖3)。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對應的客觀健康值分別為56.45、58.01、63.98、63.74。教育并非是促進老年人健康的決定因素,而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多社會經濟地位高,享有的物質生活條件與醫療資源更優,從事的職業以腦力勞動為主,從而帶來高的健康資本優勢。受教育水平越高,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程度越高,且隨年齡增長而趨于平穩。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者擁有的知識、資源等有效促進了自我認知的準確性;另一方面,他們健康管理資源優勢明顯,在經常性體檢的基礎上加強了對軀體健康的理解,從而有效促進客觀健康和主觀健康的一致性。

圖3 受教育程度、年齡與主客觀健康
4.4 主客觀健康隨年齡變動的城鄉差異小,但城鎮老年人主觀健康略高于客觀健康
城鎮老年人主觀健康略高于客觀健康,兩者之間隨年齡增長逐漸縮小(見表4)。城鎮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出現的臨界點處于退休時,并貫穿于其后的老年期。退休帶來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變化,對健康也產生新的影響。城鎮老年人退休后從工作崗位撤離,生活重心逐漸轉向對健康快樂的追求以及對自我的關注,健康認知也越來越真實。農村老年人主客觀健康隨年齡變動的趨勢稍顯復雜,在步入60 歲以前,他們作為家庭核心勞動力,需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態從事體力勞動,甚至作為高齡農民工,通過匯報比事實健康更好的狀態以獲取工作機會。農村社會雖然較少存在退休這一概念,但60 歲之后步入老年的群體大多從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轉為次要勞動力,這期間對健康的關注逐漸增多,自我感知不健康的偏差開始出現。

圖4 主客觀健康隨年齡變動的城鄉差異
5 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前文相關分析的基礎上,表3 進一步展現了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模型1 單獨納入人口學特征變量,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礎上納入社會經濟特征變量,模型3 在模型2 的基礎上進一步納入家庭特征因素,以全面考察在控制其他因素基礎上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的影響因素。年齡對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的影響在三個模型中均通過統計檢驗,且年齡以及年齡的平方均正向決定了主觀健康與客觀健康之間的差異。隨年齡增長,主客觀健康之間的差距呈現先縮小后擴大的變動趨勢。結合相關分析可知,老年人主觀健康低于客觀健康的年齡段集中于60 至75 歲之間,而其他年齡段則處于主觀健康高于客觀健康的狀態。可見,初老之人易陷入“患病”、“秋愁”之思而低估自我健康。步入初老期,機體功能逐漸減退、行動力、適應能力等也相應發生變化,老人特別是剛從工作崗位抽離的退休老人開始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關注自我健康,但主觀情緒上的過分憂擾極易導致健康認知偏差,從而陷入“病而非病”的消極狀態。傳統言“七十三,八十四”,老年往往異常重視此時的健康狀態,認為度過之后將延年益壽、平安康樂。步入高齡期,老年心態的豁達以及對健康理解的包容,對生活的態度也更積極,從而呈現基于事實健康更高的主觀健康。
性別顯著影響老年人主客觀健康差異,且男性主觀健康與客觀健康之間的差異大于女性。也即,相對比女性老人,男性主客觀健康認知的非一致性偏差更大。男性客觀健康雖略高于女性,但主觀健康感知卻遠超女性。主客觀健康相一致的程度決定了健康行為的選擇空間。當主觀健康高于客觀健康,可能出現忽視健康管理,減少就醫、體檢等行為;反之,當主觀健康低于客觀健康,可能出現過度醫療、甚至通過保健藥品尋求健康保證等行為。因此,男性老年人脫離事實健康的認知偏差,一定程度上會導致非科學的健康管理活動,如繼續忽視健康,延續非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相比較受教育程度為初中的老年人,小學及以下者的主客觀健康之間的差距大,而大專及以上者的主客觀健康差異小。與居住環境較差者相比,老年人的居住環境越好,對應的主客觀健康之間的差異也越小,呈現的健康一致性程度也越高。收入一定程度促進了老年人主客觀健康的一致性程度,與家庭收入較高者相比,低收入者的主客觀健康的差異大。子女數與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呈現正向關系,子女數越多,老年人主客觀健康分值越相近。健康認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是基于客觀軀體健康所呈現出的綜合評判和標準。個體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同,對健康的評價和期望有別,對健康風險的厭惡程度亦不同,從而導致個體匯報的健康標準也相應存在差異。居住環境好、受教育程度高、家庭收入高以及家庭照料資源豐富的老年人在物質條件資源優勢下往往對健康分外關注,比其他群體對健康標準的要求更高,基于同等事實健康而匯報更低的健康水平。在業老人主客觀健康的差距顯著高于不在業者,他們與社會經濟條件弱勢者具有諸多類似之處,甚至為同一類群體,對于健康的標準和要求偏低,甚至仍處于勞動階段,尚需要通過積極的健康認知獲取更多的勞動和工作報酬。婚姻、城鄉對老年人主客觀健康的一致性并不具有顯著影響。

表3 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影響因素的logistic 回歸模型
6 結論與討論
基于對老年人主客觀健康的測量,本文探討了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主觀健康和客觀健康之間存在一致性偏差,且隨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居住條件等呈現不同特征。60 至75 歲的老年人疑“病”而“非病”,而低齡、高齡老年人則信“無病”而“病”。女性主客觀健康一致程度高;男性多吸煙、酗酒等非健康生活方式導致其健康標準低于女性,基于客觀軀體健康而感知的主觀健康也更高,從而擴大了主客觀健康之間的距離。受教育程度高者、居住條件良好者以及家庭收入較高者的主客觀健康一致性程度高;相較之下,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個體主觀健康反而更高,并導致自評健康遠超客觀健康的非一致狀態。雖然老年人主客觀健康隨年齡、性別、城鄉、受教育程度呈現不同特征,但總體而言老年人主觀健康高于客觀健康,即個體基于客觀軀體健康的認知更積極。如果考慮到某些不被個體察覺的非健康因素或疾病,軀體的客觀健康值將進一步下降,屆時老年人主客觀健康之間的不一致程度更明顯。
年齡作為影響健康的決定性因素,對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具有重要影響,主客觀健康之間的年齡差異應證了老年人生路途過程的心理狀態變化。在尚未變老時對健康的肆無忌憚,初老時分體會“變老”帶來的恐懼,以及跨越某個特定年齡的豁達與樂觀。健康認知是個體對疾病、行動能力等軀體健康的主觀評價的有效程度,但主觀健康信念和客觀事實之間存在偏差或不一致,將導致非健康管理行為。因此,對健康頗為敏感的花甲、耳順老人可能因對健康的過分關注而混淆“病與非病”的界限,甚至出現盲目保健消費、過度醫療等異常行為。普及健康觀念和健康生活方式,促進不同年齡段群體健康認知的有效性;既需杜絕懷疑自我“有病”而亂投醫發生的過度醫療,亦不能盲目夸大自己的健康行為而忽視對健康的管理。
社會經濟地位顯著影響老年主客觀健康一致性,也帶來健康標準期望的差異。健康評價是復雜事件,客觀健康通過醫學檢測、行為活動能力予以判斷,而主觀健康除了基于客觀健康的感知外,也因個體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環境而相異,即在同等客觀健康狀態下,經濟地位不同的個體可能匯報出不同的主觀健康。社會經濟地位低者、物質條件劣勢者降低對健康標準的期待,反而報告出高的自評健康,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主客觀健康之間的同一性,導致基于客觀健康的主觀健康認知的風險偏差。因此,主觀健康高于客觀健康的非一致性偏差并非源于“積極健康認知”,也非預示“健康自信”,更可能是處于資源弱勢的個體對于健康低標準的非公允認知。
已有研究論證了自評健康與事實健康的正相關關系,將主觀健康作為客觀健康的有效度量并廣泛被使用。然而,主客觀健康之間的非一致性結果強調了主觀健康(自評健康、自測健康)作為客觀健康替代所存在的風險問題。社會經濟地位低者傾向于匯報比客觀健康更優的主觀健康,社會經濟地位高者的主客觀健康認知一致性程度更高;但前者往往是醫療救助以及健康需求更高的群體。諸多關于健康福利、健康公平等的研究大多基于自評健康展開,實際卻高估了事實健康,由此可能導致健康評估的“馬太效應”并加劇健康福利不平等。未來有關健康公平和健康福利等的研究中,主觀健康指標一定程度上需謹慎使用。然而,客觀健康數據獲取難度偏大,這也加重了科學研究的成本和困難程度。隨著社區健康檔案管理的推行,以及常規性體檢的逐漸普及,未來獲取健康數據資料的便捷程度將相應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