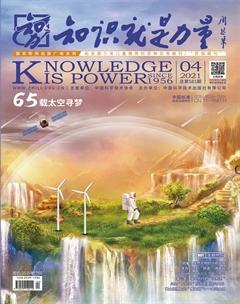開啟星際大航海時代一評《發現人類》《LC的探險》
劉健

當最早期的一批智人離開非洲大陸,站在小亞細亞的荒原上,仰望夜空蒼穹上的點點繁星和一輪明月時,他們中或許有人想過,終有一天,后世子孫的腳步將會踏入星空之中。或許,就是在這一刻,好奇與敬畏同時植入了人類的文化基因之中,左右了此后成千百萬年間——最終走向星辰大海的旅程。
在絕大多數古人的眼中,“天”是與“地”對應的存在,日月星辰不過是眾神鑲嵌在天空中的裝飾品。直到近代科學產生,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否定了大地是宇宙中心的舊學說,伽利略通過望遠鏡觀測證明了日心說,而開普勒則提出了行星運動定律……在一代又一代科學家的不懈努力下,人類終于走出了偏狹和迷信的包圍,真正認識了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的真相——地球僅僅是太陽系內的一個行星,而整個太陽系也僅僅是宇宙中無數星系中平凡的一個。
隨著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的到來,人類僅僅花費了二三百年的時間便將足跡踏遍了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無論是赤道、兩極,還是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抑或是地球表面的最深處馬里亞納海溝。于是,人類再次將目光投向了遙遠的太空,飛出地球,探索宇宙成為人類新的夢想。

1865年9月,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開始在報刊上連載他的新宇宙冒險故事《從地球到月球》。小說講述一家主要由大炮發明家組成的大炮俱樂部。俱樂部的主席巴比康是個狂熱的大炮研究者,他提出把一顆空心炮彈改造成宇宙飛船,利用超級大炮將宇宙飛船發射到月球上去。法國冒險家米歇爾·阿爾當在獲悉這一消息后,設法找到了巴比康,希望自己能成為這趟冒險之旅的主要成員。最終巴比康、米歇爾·阿爾當和尼卻爾船長克服了重重困難,成功地將這艘炮彈飛船發射到了外太空。但中途遇到火流星的引力干擾,炮彈飛船并沒有在月球上著陸,而是在距離月球4500千米的地方繞月運行。而在續作《環繞月球》中,炮彈飛船三人組將生死置之度外,利用環繞月球的機會仔細觀測月球的表面,并做了詳細的筆記。
在《從地球到月球》面世的38年后,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先生,無意間看到了這部小說的日文譯本,深受震撼,便親自將這部小說轉譯成中文,并在出版前言中寫下了擲地有聲的“導中國人前行,必自科學小說始!”
美國科幻作家詹姆斯·布立什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創作出版了《宇宙城》系列太空科幻故事。小說中,人類利用比鋼鐵更為堅硬的超級材料“冰4”,在木星內部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橋”。利用“橋”,人類將木星內部的強風變成數百萬兆瓦的動力。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橋”竟然具有自生長的能力。而人類制造“橋”的目的,就是為將來的宇宙遠航提供動力來源。與此同時,人類還在研究抗衰老的“不死藥”,以延長人類壽命,讓人體適應超長時間的宇宙航行。而在這些技術的基礎上,人類最終掌握了“原子核相率”宇航法,從此人類不必再建造宇宙飛船,只要通過加載“原子核相率”就能把一座城市傳送到太空之中,并完成星際旅行。于是,飛航在宇宙中的城市越來越多,整個銀河系也建立起了鍺本位的經濟體系。不過,福禍相依,興衰迭起,本來就是文明的常態。由于經濟危機的爆發,最終飛行在宇宙中的太空城們,紛紛破產。最后的人類幸存者找到了一個適于人居的行星,并將其命名為“新地球”。
中國創作者筆下的太空傳奇也毫不遜色。“中國科幻小說之父”鄭文光在20世紀50年代便寫下了《火星建設者》,描繪了中國人如何在貧瘠荒涼的火星表面,利用科學技術改造火星,通過艱苦奮斗建設新家園的英雄詩史。

本期刊載的兩篇文章都是優秀的宇航題材科幻作品。其中,當代中國著名科幻作家江波的《發現人類》,講述了未來的外星訪客在地球上發掘已經消逝的人類文明的故事。而在故事的結尾處,文中的外星訪客和正在閱讀小說的讀者們一起發現了人類文明滅亡的真相——是人類對科技無節制的濫用,最終毀滅了人類自身。而《LC的探險》則描繪了兩位為了人類的宇航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偉大宇航英雄。雖然他們只存在于小說故事中,但所展現的英雄氣概同樣令人敬佩。
宇宙航行之父齊奧爾科夫斯基晚年曾經給《航空評論》雜志寫信,信中留下了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可能永遠被束縛在搖籃里。”如今,一個新的星際大航海時代正在開啟。中國的天問一號已經進入火星軌道,在這場邁向星辰大海的旅程中,中國人已不再缺席。我們也將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為人類的太空文明譜寫更絢麗的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