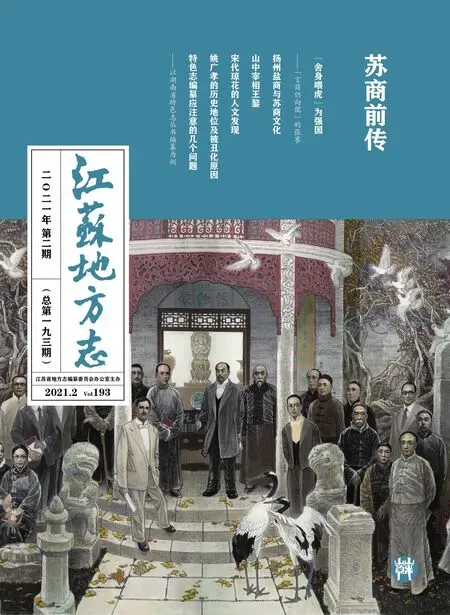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橋梁專(zhuān)家陳昌言
◎周世青
(江蘇南京210036)
謹(jǐn)以此文紀(jì)念我國(guó)老一輩著名橋梁專(zhuān)家陳昌言先生逝世30周年
——題記
陳昌言先生是上世紀(jì)我國(guó)著名的橋梁工程專(zhuān)家、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指揮部最后、任職時(shí)間最長(zhǎng)也是工作難度最大的一任總工程師。陳昌言的小兒子陳宗杰是我的同學(xué)、摯友,因?yàn)檫@層關(guān)系,加上一些工作的原因,我對(duì)陳昌言先生有所了解,也特別崇敬。
在陳昌言先生的晚年,我曾先后兩次見(jiàn)過(guò)他。那是1988年的秋季,組織上安排我去北師大參加全國(guó)骨干教師進(jìn)修班的脫產(chǎn)學(xué)習(xí)。臨行前,我看了進(jìn)修班的教學(xué)計(jì)劃,該校一批名教授,如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陶大鏞、哲學(xué)家彭萬(wàn)春、心理學(xué)家林崇德、黨史大家張靜如等都將為我們授課。然而,在授課老師的名單里沒(méi)有我久仰大名并且想去求教的著名教育學(xué)家、新中國(guó)教育哲學(xué)學(xué)科奠基人黃濟(jì)教授。宗杰告訴我黃濟(jì)是他父親的侄女婿。于是,在一個(gè)炎熱的晚上,我登門(mén)請(qǐng)陳昌言先生給我寫(xiě)引薦信。這是我第一次見(jiàn)到老人家,他已近耄耋,高大、微胖,和藹、可親。大約40分鐘后,當(dāng)我看到引薦信時(shí),驚訝不已,這哪是長(zhǎng)輩給晚輩的便箋,更像是平輩交談的家書(shū),字里行間流淌著濃濃親情,也滲透著對(duì)我這個(gè)小輩的厚愛(ài)。老人家的認(rèn)真、負(fù)責(zé)和謙遜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第二次見(jiàn)到陳昌言先生是在兩年半后,此時(shí)老人家已是病重彌留之際。宗杰約我和他的孿生兄弟一道,把老人家從四樓家里抬下樓理發(fā)并送往醫(yī)院。那時(shí)的居民樓樓道很窄,各家都堆放了不少雜物,我們抬得很吃力。老人家過(guò)意不去,對(duì)我說(shuō):“世青啊,對(duì)不住啊,我真是狼狽不堪啊!”陳昌言先生此次離家就再也沒(méi)有回來(lái),三天后也就是1991年3月6日便駕鶴西去了。

陳昌言(左)在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工地上
我因?yàn)槌霾睿瑳](méi)能參加陳昌言先生的告別會(huì)。事后,宗杰特地送來(lái)告別會(huì)上宣讀的“陳昌言生平”:
陳昌言,江蘇溧水人,1909年5月出生,1933年于南京中央大學(xué)工學(xué)院土木系畢業(yè)后,先后輾轉(zhuǎn)中南、西南、華東等地,從事鐵路工程建設(shè)。全國(guó)解放以后,他以更高的熱情為祖國(guó)的橋梁事業(yè)辛勤工作。在武漢長(zhǎng)江大橋的建設(shè)中,他負(fù)責(zé)漢水鐵路橋以及大橋北岸的施工技術(shù);在重慶白沙沱鐵路大橋的建設(shè)中,他解決了在大孤石中鉆孔并下沉管柱的難題;在舉世矚目的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中,他先是擔(dān)任北岸施工的四橋處總工程師,后又擔(dān)任大橋局副總工程師和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指揮部總工程師。1985年,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橋新技術(shù)獲國(guó)家技術(shù)進(jìn)步特等獎(jiǎng),陳昌言作為7位主要獲獎(jiǎng)?wù)叩拇恚氨本┤嗣翊髸?huì)堂領(lǐng)獎(jiǎng)。
陳昌言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遺愿,將其骨灰葬在長(zhǎng)江南岸象山的小樹(shù)林里。這里緊靠南京長(zhǎng)江大橋的鐵路引橋,每天都能看到心愛(ài)的大橋、每天都能聽(tīng)到火車(chē)過(guò)橋的轟鳴聲,這是老人永遠(yuǎn)的守望。
2013年,南京鐵道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與上海鐵路局共同成立全國(guó)首家鐵路文化研究中心。我作為校方代表,擔(dān)任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成立以后的一項(xiàng)重要工作就是策劃和設(shè)計(jì)江蘇鐵路教育館之江蘇鐵路百年歷程展。南京長(zhǎng)江大橋是新中國(guó)鐵路建設(shè)的重大成就,陳昌言是這一舉世矚目工程的突出貢獻(xiàn)者,也是我仰慕已久的老前輩。于是,我開(kāi)始收集老人家資料,期待著更深入地走進(jìn)陳昌言的“橋梁人生”。我首先在百度上搜索,出乎意料的是在浩瀚的互聯(lián)網(wǎng)上幾乎找不到陳昌言的信息。我很不甘心,終于在施仲衡的回憶錄里看到了老人家的名字。
被譽(yù)為“中國(guó)地鐵之父”的施仲衡生于1931年,是上世紀(jì)50年代我國(guó)第一個(gè)赴蘇學(xué)習(xí)地鐵專(zhuān)業(yè)的留學(xué)生,中國(guó)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學(xué)博士生導(dǎo)師,城市軌道交通專(zhuān)家,中國(guó)地下軌道交通事業(yè)的奠基人。在施仲衡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話(huà):
1949年南京解放,我們家有了很大的轉(zhuǎn)機(jī)。哥哥到燕子磯小學(xué)當(dāng)校長(zhǎng),父親在市立三中教歷史、語(yǔ)文等課,我在市立三中學(xué)習(xí)。1950年高中畢業(yè)考試,我的成績(jī)名列前茅。考大學(xué)報(bào)志愿時(shí),家里有三個(gè)意見(jiàn):父母親建議考南京大學(xué)文史類(lèi),既可繼承父親衣缽,又可留在南京;哥哥建議我考東北的大學(xué)到老解放區(qū)去;舅舅陳昌言在鐵路工作,是橋梁專(zhuān)家(后曾任南京長(zhǎng)江大橋總工程師),他勸我上中國(guó)交通大學(xué)唐山工學(xué)院(簡(jiǎn)稱(chēng)唐山交大)。3個(gè)學(xué)校我都報(bào)了名并都被錄取了。最后我選擇了唐山交大土木系。1952年進(jìn)行教育改革和院系調(diào)整,我校土木系分成橋梁隧道系和鐵道建筑系。我當(dāng)時(shí)受舅舅的影響,因?yàn)樗歉銟蛄旱模揖瓦M(jìn)入橋梁隧道系就讀。
我這才知曉,陳昌言是大名鼎鼎的施仲衡院士的舅舅。年輕的施仲衡為什么對(duì)舅舅如此“言聽(tīng)計(jì)從”,是因?yàn)檫@個(gè)舅舅一直是他的學(xué)習(xí)楷模。少時(shí)的施仲衡常聽(tīng)父母給他講述舅舅的故事:陳昌言祖籍是溧水漁歌鄉(xiāng)大陳村,從小生活在南京城南的一個(gè)小職員家庭。家境貧寒、生活艱辛造就了他迎難而上、自強(qiáng)不息的性格。他決心刻苦學(xué)習(xí)、改變?nèi)松\(yùn)。無(wú)論是在剪子巷小學(xué)還是在鐘英中學(xué),他的成績(jī)總是名列前茅。1929年陳昌言如愿考入中央大學(xué)土木系,因?yàn)樵谛W∷藁ㄙM(fèi)大,他就住在中華門(mén)外的家里,每天花一個(gè)小時(shí)時(shí)間步行到位于成賢街的學(xué)校,中飯常常是兩塊燒餅、一杯開(kāi)水。大學(xué)階段要獲得助學(xué)金必須是前三名的成績(jī),他一次都沒(méi)落下。從小生活在長(zhǎng)江邊的施仲衡為何選擇與鐵路結(jié)緣?在一次與媒體記者對(duì)話(huà)時(shí),已是耄耋之年的施仲衡笑著說(shuō),這是受到舅舅陳昌言的鼓勵(lì)。“中學(xué)畢業(yè)時(shí)舅舅對(duì)我說(shuō),你去學(xué)鐵路吧。現(xiàn)在新中國(guó)剛剛成立,百?gòu)U待興,未來(lái)火車(chē)一定會(huì)跑遍華夏大地,學(xué)鐵路大有作為。”

1973年陳昌言(前左4)和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工作組成員合影
陳昌言是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指揮部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總工程師。作為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指揮部任職時(shí)間最長(zhǎng)的總工程師,陳昌言在主持大橋施工的過(guò)程中做了什么,有哪些經(jīng)典之作和感人的故事?通過(guò)走訪(fǎng)相關(guān)人員、查閱有關(guān)資料,其脈絡(luò)、亮點(diǎn)在我的腦海里漸漸清晰起來(lái)。
1959年底,我國(guó)鐵路橋梁界的技術(shù)精英和建設(shè)大軍帶著武漢長(zhǎng)江大橋建成的喜悅順江而下,匯聚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工地。陳昌言擔(dān)任大橋局四橋處總工程師,負(fù)責(zé)長(zhǎng)江北岸1—4號(hào)橋墩及其以北工程的建設(shè)。長(zhǎng)江南京段的水文情況復(fù)雜,施工遇到的困難不斷地出現(xiàn)在大橋建設(shè)者面前。繼1號(hào)墩、2號(hào)墩開(kāi)工之后,3號(hào)墩于1961年2月開(kāi)工。這個(gè)橋墩的下部結(jié)構(gòu)是鋼沉井加管柱基礎(chǔ),地處河床地質(zhì)的斷裂帶上,在灌注水下混凝土?xí)r,水泥漿都流失了。面對(duì)這個(gè)大難題,陳昌言寢食難安,他查閱了大量的國(guó)內(nèi)外資料,把水利部專(zhuān)家請(qǐng)到現(xiàn)場(chǎng)共同研究,終于拿出“多孔聯(lián)通填充灌漿”的施工方案,就是從斷裂河床的大外圈逐漸向中心圈鉆孔,清除殘留物,然后向基巖夾層填充大量的水泥砂漿,使斷裂帶由上而下形成混凝土實(shí)體,然后再鉆孔做管柱基礎(chǔ)。施工期間,曾有一艘大噸位的輪船撞到3號(hào)墩上,結(jié)果船頭破損嚴(yán)重,而橋墩的基礎(chǔ)安然無(wú)恙。陳昌言從1964年開(kāi)始全面負(fù)責(zé)南京長(zhǎng)江大橋的技術(shù)工作,1965年1月正式擔(dān)任大橋局副總工程師和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指揮部總工程師。紛繁復(fù)雜的工作令陳昌言不敢有一絲一毫的馬虎和懈怠。然而,更復(fù)雜的局面、更重的擔(dān)子還在等著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kāi)始后,在南京的大橋局人員大都奉命回武漢接受“再教育”。時(shí)任大橋局局長(zhǎng)、大橋建設(shè)指揮部指揮長(zhǎng)宋次中讓陳昌言負(fù)責(zé)縮編的大橋局駐南京工作組。臨行前,他緊緊攥著陳昌言的手說(shuō):“我把南京大橋交給你了,如果質(zhì)量有任何問(wèn)題,那就唯你是問(wèn),這是組織的命令。”陳昌言在極其困難的歷史時(shí)期擔(dān)任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工程的唯一負(fù)責(zé)人。當(dāng)時(shí),“文革”使很多工作都已停擺,而大橋施工有很多問(wèn)題需要處理。雖然陳昌言每天都是樂(lè)樂(lè)呵呵地出現(xiàn)在工地上,可他的心里卻承受著很大的壓力。“造反派”把指揮部的公章?lián)屪吡耍姐y行開(kāi)工資、劃撥工程款,全憑陳昌言的小方章,他小心翼翼時(shí)刻把小方章掛在身上。
大橋鋼桁梁的聯(lián)結(jié)采用的是鉚釘技術(shù),就是用燒紅的鉚釘,對(duì)準(zhǔn)鉚孔用風(fēng)槍擠壓鉚死。鋼桁梁的板層多達(dá)9層,板束最厚達(dá)18厘米,鉚結(jié)的難度可想而知。工人在現(xiàn)場(chǎng)的火爐旁燒制鉚釘時(shí)溫度很高,勞動(dòng)強(qiáng)度極大,陳昌言一直和工人在一起。1966到1967年是南京長(zhǎng)江大橋正橋鋼梁架設(shè)的關(guān)鍵時(shí)期。在近兩年的時(shí)間里,陳昌言幾乎每天都在鋼梁上爬上爬下,時(shí)刻提醒工人:鉚釘要燒紅燒透,進(jìn)孔要正,開(kāi)裂彎曲的一定要重鉚。同時(shí),督促質(zhì)檢人員認(rèn)真檢查、把關(guān)。陳昌言對(duì)鋼梁鉚結(jié)要求高、把關(guān)嚴(yán),得到部里領(lǐng)導(dǎo)和專(zhuān)家的交口稱(chēng)贊,給了他一個(gè) “鉚釘專(zhuān)家”的雅號(hào)。如今,橋梁上的150多萬(wàn)個(gè)鉚釘經(jīng)過(guò)半個(gè)世紀(jì)的風(fēng)雨考驗(yàn),仍然整齊良好,返修率極低。
1968年9月,南京長(zhǎng)江大橋鐵路橋架通。27日晚,首次開(kāi)行重載試驗(yàn)列車(chē),前后兩個(gè)火車(chē)機(jī)頭拉著7節(jié)裝滿(mǎn)貨物的車(chē)廂,火車(chē)司機(jī)心里有些緊張,似乎對(duì)大橋的質(zhì)量有些擔(dān)心。陳昌言看出司機(jī)的膽怯,他迅速登上車(chē)頭,拍著司機(jī)的肩膀說(shuō):“沒(méi)問(wèn)題,有我在車(chē)頭陪著,你放心大膽地開(kāi)過(guò)去!”司機(jī)這才拉下閘把,汽笛劃破夜空,列車(chē)由慢而快,在剛剛建好的長(zhǎng)江大橋上鏗鏘前行并駛了個(gè)來(lái)回。走下機(jī)車(chē),陳昌言響亮地說(shuō):“我有絕對(duì)把握,大橋肯定沒(méi)問(wèn)題,絕不會(huì)垮!”鐵路橋通車(chē)后,“造反派”卻把“反動(dòng)技術(shù)權(quán)威”帽子扣到陳昌言的頭上。不久,陳昌言被送到湖北沙洋干校邊勞動(dòng)改造邊接受審查。直到五年以后的1973年,陳昌言才回到南京,奉命進(jìn)行大橋建設(shè)的總結(jié)工作。
2015年6月,南京鐵道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承辦歐亞鐵路高校國(guó)際論壇,江蘇鐵路教育館計(jì)劃同時(shí)開(kāi)館。5月中旬的一天,也是籌備展覽最緊張的時(shí)刻,宗杰和他的孿生哥哥宗俊送來(lái)了他們捐贈(zèng)的陳昌言先生的施工手稿和老人家使用過(guò)的計(jì)算尺、飯盒等辦公、生活用品。那天晚上我請(qǐng)陳家兄弟小酌,大家邊吃邊聊,長(zhǎng)期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宗俊如數(shù)家珍般款款道來(lái):
爸爸在主持大橋建設(shè)施工的日子里,一天也離不開(kāi)計(jì)算尺。那時(shí)沒(méi)有電腦和電子計(jì)算器,所有施工圖紙上面的每一個(gè)數(shù)字,都要通過(guò)計(jì)算尺來(lái)拉來(lái)算,有時(shí)候?yàn)榱艘粋€(gè)數(shù)字的準(zhǔn)確性甚至要忙上一天,他常常提醒身邊的工程技術(shù)人員,必須計(jì)算準(zhǔn)確,斤斤計(jì)較,不能有一絲一毫的誤差。南京橋的鐵路引橋設(shè)計(jì)的31.7米跨度的鋼筋混凝土預(yù)應(yīng)力“T”形梁,是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橋梁的空白,沒(méi)有任何實(shí)例或可借鑒的資料。爸爸深入技術(shù)人員中集思廣益,組織大家仔細(xì)計(jì)算分析,晚間回到家里反復(fù)計(jì)算核對(duì)。爸爸還用了一年多時(shí)間,在南京梁廠(chǎng)做了整片梁的靜載破壞性試驗(yàn),用實(shí)際數(shù)據(jù)來(lái)驗(yàn)證梁體的極限強(qiáng)度、剛度和穩(wěn)定度,為大批生產(chǎn)高質(zhì)量的31.7米跨度鋼筋混凝土預(yù)應(yīng)力“T”梁提供了可靠的技術(shù)保證。
彭敏是鐵道部大橋工程局第一任局長(zhǎng),南京長(zhǎng)江大橋建設(shè)指揮部第一任指揮長(zhǎng),新中國(guó)鐵路和橋梁建設(shè)卓越的組織者、領(lǐng)導(dǎo)者。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彭敏的路橋情緣》一書(shū)中間有這樣一段敘述:
彭敏在漢水鐵橋上選擇的工程技術(shù)負(fù)責(zé)人是陳昌言,來(lái)自上海鐵路局基建處的總工程師。他精通英語(yǔ)、德語(yǔ),為了和蘇聯(lián)技術(shù)人員交流,自修俄語(yǔ),以后還自學(xué)了日語(yǔ)。他技術(shù)扎實(shí),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豐富,有人見(jiàn)過(guò)他厚厚的筆記本,密密麻麻的小字,記滿(mǎn)了他累累的經(jīng)驗(yàn)。在杭州臨近解放時(shí),他硬是不跟著國(guó)民黨去臺(tái)灣,設(shè)法躲避留下來(lái),直到解放大軍到來(lái)。陳昌言心悅誠(chéng)服地?fù)碜o(hù)共產(chǎn)黨,是因?yàn)樗H眼看到共產(chǎn)黨軍隊(duì)紀(jì)律嚴(yán)明,官兵平等,進(jìn)城不擾民,露宿街頭,深受感動(dòng)。浙贛鐵路總軍事代表劉白濤對(duì)他們宣布所有沒(méi)有跟國(guó)民黨走的工程技術(shù)人員一律保留原職務(wù),按原薪支付工資。陳昌言確認(rèn)共產(chǎn)黨“乃仁義之師也!
這本書(shū)還披露了彭敏在漢水鐵橋建設(shè)中,因支持陳昌言等中方技術(shù)人員的意見(jiàn)而被紀(jì)律處分的經(jīng)過(guò)。1953年底開(kāi)工的漢水鐵橋是建設(shè)武漢長(zhǎng)江大橋的前哨戰(zhàn),國(guó)家十分重視,邀請(qǐng)?zhí)K聯(lián)專(zhuān)家擔(dān)任顧問(wèn)。漢水河床是密實(shí)細(xì)沙沖擊層,由塑性砂質(zhì)黏土和礫石構(gòu)成。在這樣的河床中打樁十分費(fèi)力。因?yàn)榇驑兜氖拢刑K技術(shù)人員發(fā)生了分歧,在4號(hào)橋墩,樁打不下去了。根據(jù)蘇聯(lián)的打樁公式,樁的承載力不夠,樁沒(méi)有下到設(shè)計(jì)的深度,蘇聯(lián)顧問(wèn)提出需逐根復(fù)打。陳昌言則認(rèn)為根據(jù)靜重試驗(yàn),樁的承載力已經(jīng)超過(guò)數(shù)倍,不同意復(fù)打,并且指出蘇聯(lián)公式不合理之處。彭敏贊成陳昌言的意見(jiàn),做出不再?gòu)?fù)打的決定。工程進(jìn)展的結(jié)果證明陳昌言的判斷是正確的。可是,沒(méi)想到這事被蘇聯(lián)顧問(wèn)告到了鐵道部,鑒于當(dāng)時(shí)的政治形勢(shì),彭敏受到警告處分。

1985年陳昌言獲國(guó)家科技進(jìn)步特等獎(jiǎng)
膽敢對(duì)蘇聯(lián)“老大哥”說(shuō)不,這就是陳昌言。其實(shí),陳昌言是非常重視學(xué)習(xí)國(guó)外的先進(jìn)技術(shù)的,否則他就不會(huì)那么刻苦的學(xué)習(xí)多門(mén)外語(yǔ)。宗杰告訴我:從武漢搬來(lái)南京后,中山東路外文書(shū)店是父親最常去的地方,父親的晚年還翻譯了不少?lài)?guó)外橋梁建設(shè)的文章和資料,在中外新技術(shù)推廣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陳昌言卻從不崇洋媚外,他一貫堅(jiān)持的是實(shí)事求是的科學(xué)態(tài)度。
2020年,我在一位大橋物件收藏家的手里看到一份南京長(zhǎng)江大橋驗(yàn)收交接報(bào)告書(shū)(初稿)的鋼筆手抄件,報(bào)告書(shū)共11張稿紙,字跡工整、秀麗、老道,似曾相識(shí)。我給宗杰看,他一看便大聲喊道:“是我爸爸的親筆!”我聯(lián)想起館里展出的施工手稿,怪不得字體那么面熟。經(jīng)宗杰回憶,這份報(bào)告書(shū)的初稿,是他父親從沙洋干校回來(lái)后,帶領(lǐng)一個(gè)工作小組反復(fù)討論,多方征求意見(jiàn)所形成的。鋼筆手抄件是陳昌言仔細(xì)修改、親筆謄寫(xiě)的。報(bào)告書(shū)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是,南京長(zhǎng)江大橋的建造,是“國(guó)家的決定”,是“廣大建橋工人和革命干部,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有志氣,有魄力,自己設(shè)計(jì),自己施工,排除重重困難,終于建成這座轟動(dòng)世界的橋梁”。“報(bào)告書(shū)”總結(jié)了大橋設(shè)計(jì),施工的方方面面。陳昌言作為大橋的中、后期技術(shù)主管,在“報(bào)告書(shū)”中既充分肯定了工程的偉大成就,又不掩飾、不回避當(dāng)年工作的失誤與不足,為后人樹(shù)立起無(wú)私無(wú)畏,追求真理的精神豐碑。
陳昌言個(gè)人生活嚴(yán)肅,恪守傳統(tǒng),煙酒不沾,只愛(ài)讀書(shū)。妻子多年患病,陳昌言工作之余悉心照料,又兼顧對(duì)孩子的培養(yǎng)教育。他的四個(gè)兒子、一個(gè)女兒先后在“文革”前和恢復(fù)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學(xué),并且全部加入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分別在冶金、電力、橋梁、醫(yī)療、教育等領(lǐng)域奉獻(xiàn)國(guó)家。陳昌言沒(méi)喝過(guò)洋墨水,但他卻以中國(guó)人特有的勤勉和睿智,創(chuàng)造出了很多被他自己稱(chēng)作的“笨辦法”,解決了實(shí)踐中的難題。
“橋是凝固的歷史,它記錄了民族的精神。”南京長(zhǎng)江大橋是長(zhǎng)江上第一座由中國(guó)人自己建造的長(zhǎng)江大橋,是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我國(guó)最耀眼的建設(shè)成就。半個(gè)世紀(jì)過(guò)去了,南京長(zhǎng)江大橋雄風(fēng)不減、英姿猶在。在干線(xiàn)交錯(cuò)、高鐵縱橫的華東鐵路網(wǎng)上,它依然是重要的跨江通道;在古城南京的多條長(zhǎng)江橋隧中,它依然是最為忙碌、最不可或缺的;在古今眾多的城市文化名片中,它依然是最為質(zhì)樸厚重、璀璨亮麗的。
每當(dāng)空閑,我總喜歡帶著家人來(lái)到大橋不遠(yuǎn)處的江邊。看鐵路橋上動(dòng)車(chē)飛馳、公路橋上車(chē)水馬龍。注目于那九座橋墩,它們巨人般地屹立中流、身負(fù)萬(wàn)乘,用堅(jiān)挺的肩膀扛起萬(wàn)噸鋼梁,我不禁感慨,“不辱使命,忠于職守”是對(duì)橋墩精神的詮釋?zhuān)菍?duì)陳昌言為祖國(guó)鐵路橋梁事業(yè)奉獻(xiàn)一生的高度概括。如今,在流經(jīng)江蘇的近400公里的長(zhǎng)江上,已有13座長(zhǎng)江大橋建成通車(chē),而在整個(gè)中國(guó)的版圖上,大江大河上已經(jīng)架起了無(wú)數(shù)座現(xiàn)代化的橋梁,連通了中華騰飛和民族復(fù)興的通衢大道,這正是像陳昌言先生這樣的一代又一代橋梁專(zhuān)家、大國(guó)工匠代代接續(xù)、脈脈相承,砥礪奮斗、無(wú)私奉獻(xiàn)的結(jié)果。他們以楷模之光匯聚時(shí)代精神,不愧為祖國(guó)和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