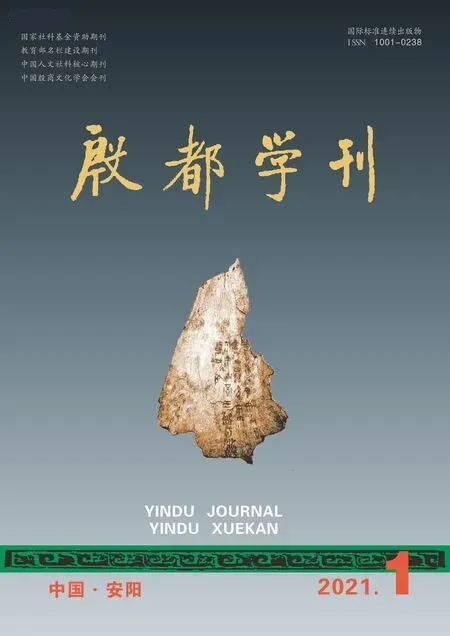《清華簡(七)·晉文公入于晉》中的軍旗考論
洪德榮
(鄭州大學 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河南 鄭州 450001)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先秦兵學和軍事學的相關研究中,關于制度的問題,過往主要以傳世文獻作為重建先秦制度的基礎及根據。而除了傳世文獻,商周金文對于古代軍制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與軍事有關的銘文早已成為獨立的研究論題,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其中與旗類有關的器物作為賞賜物已見于西周金文,(1)如商艷濤:《西周軍事銘文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對軍事銘文做過整理與討論,如常、旗、旜、旟、旐或與“物”字相關的字形都見于西周金文,也可印證孫詒讓提出的“五正旗四通制”之說。參鄔可晶:《西周金文所見有關“九旗”的資料》,《中國經學》(第十六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5-144頁。因此出土文獻材料對于探究古代旗幟制度,也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在出土的簡帛文獻中,有一類關于先秦旗幟的材料值得注意,材料公布以來也有不少學者進行過討論,但從先秦兵學的角度而言,仍有再討論的空間。
二、簡文校讀
近人對于古代旗幟制度的討論頗有成果,如林巳奈夫細致地探討關于旗的形態,高木智見亦對旗幟的圖案及內涵進行討論,楊英杰也對旗幟的意義做過討論。(2)(日)林巳奈夫:《中國先秦時代的旗》,《史林》1966年第49卷第2號;(日)高木智見:《關于春秋時代的軍禮》,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1-169頁;楊英杰:《先秦旗幟考釋》,《文物》1986年第2期,第52-56頁。在新出楚簡中關于旗幟的記載,可以為有關研討帶來不同的詮釋角度。
《清華簡(七)·晉文公入于晉》簡5到簡6是關于旗幟的敘述,(3)竹簡材料的情況可參馬楠:《<晉文公入于晉>述略》,《文物》2017年第3期,第90-92頁。先將簡文抄錄如下:

原整理者認為“旗物”為諸旗統稱,《周禮·大司馬》:“辨旗物之用。”《周禮·鄉師》:“四時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庶以旗物。”《周禮·巾車》:“掌公交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周禮·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周禮·司常·九旗》:“日月為常,交龍為旗,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孫詒讓據金榜《禮箋》說,以為“通帛為旜,雜帛為物”“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系諸旗通制,“日月為常”色纁,象中黃,“交龍為旗”色青,“熊虎為旗”色白,“鳥隼為旟”色赤,“龜蛇為旐”色黑,各象五方之色。“通帛為旜,雜帛為物”,通帛謂縿斿一色,純色,故尊于雜帛。(4)原整理者之說及簡文的通讀隸定皆出自李學勤,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中西書局,2017年。下同,不再出注。如有其他諸家之說再引用討論。

是以《說文》言旗上有熊形,蓋因旗的作用就在于標示、象征,因此可作為士卒聚集的地點,也是構成軍事行動中的軍隊信息體系。但筆者認為以旗的作用及本義而言,不同典籍所記載的內容與簡文所言不一定能完全對比的上,甚至同樣用于軍事的旗幟在不同時代的不同記載之中,都有不一樣的圖像象征與表義功能,以材料本身的文字記載去做解讀,在其記載的內部體系及背景中去考慮,這是考察簡文中的軍旗制度很重要的視角。

在考古發現中,河南淮陽馬鞍冢的戰國晚期車馬坑出土過一種貝旗,旗為紅色,旗一面每組用八枚海貝,旗另一面每組用四枚海貝,用線綴成四瓣的花紋,排列整齊。旗紋飾是由海貝綴成,整理者稱其為貝旗。(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區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陽馬鞍塚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0期,第12頁。而軍旗本身的表意作用除了顏色,圖像更是一大關鍵。如《禮記·曲禮上》: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后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其主要敘述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軍隊進軍所遭遇的情況,及對應的旗號圖像,二為左右前后方位的應對,用意在于分辨各軍,以利指揮。而《管子·兵法》也有類似意義的敘述: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韟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但兩種材料對于同一情況下采取的旗號是不同的,如遇到行水,《禮記·曲禮上》為青旌;《管子·兵法》為龍章。
另如《墨子·旗幟》的記載: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 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童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旌旗,劍盾為羽旗,車為龍旗,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同樣也以顏色與圖像表示事物的現象及狀態,可見旗幟的表意具有材料中自己的表達體系,這也是解讀先秦軍旗問題需要注意的可比性與相似性之間的辨別問題。

原整理者引鄭玄注“交龍為旗”,以為“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謂二龍一升一降。
謹案:就簡文分析,“升龍”即“師以進”;“降龍”即“師以退”,以“升”對比“進”,是語意的引申轉移,“升”指物體的移動由下而上,并有登義,“進”則指平行的向前移動。相對于“退”而言,“降”與“退”同樣也是語意引申轉移。因此就簡文言,圖像的內容亦不難想見。至于鄭玄注“交龍為旗”的“交龍”《釋名·釋兵》言:“交龍為旗,旗,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通帛為旃,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也。三孤所建,象無事也。” “交龍”指兩龍相依交會,龍首一在上,一在下,也是一種表意的方式,與簡文所記載的“升龍”“降龍”自然為不同的旗幟。

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石小力又補釋認為“豫”,整理者如字讀,訓為預備。今按,豫可讀為舍,訓為止息。楚簡“豫”字多讀為“舍”,如《上博四·曹沫之陣》18-19:“臣之聞之:不和于邦,不可以出豫(舍)。不和于豫(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戰。”軍隊住宿一夜為舍。《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引申可指軍隊休息,《漢書·韓信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顏師古注:“舍,息也。”《管子·兵法》:“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偃兵”即“師以舍”。(8)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7年4月23日。
程浩亦補釋認為整理報告于“豫”字無說,而按照楚簡的用字習慣,或應將其讀為“舍”。清華簡《系年》屢見“豫”字,如“楚王豫圍”(簡42)、“秦人豫戍”(簡45)、“楚人豫圍”(簡117)等,這些“豫”很明顯都應讀“舍”,意為釋放、舍棄。然而《晉文公入于晉》中這個“豫”字的涵義,似乎還不能完全與《系年》等同。從上下文來看,簡文用以描述不同旗幟作用,往往是一組反義詞。如簡6“為升龍之旗師以進,為降龍之旗師以退”,升龍與降龍分別對應的是師的“進”與“退”。以此類推,這里角龍與交龍所對應的“戰”與“舍”應該也是相對的概念。實際上,上博簡《曹沫之陣》中就有這樣的用例,其云:
既戰復舍,號令于軍中曰:“繕甲利兵,明日將戰。”(《曹沫之陳》簡50)
從中可以看出“舍”是與“戰”相反的動作,有止戰之意。《孫子·軍爭》“交和而舍”,賈林注“止也”,即是此意。陳劍先生認為《曹沫之陳》中的“豫”皆當讀為“舍”,意為“軍隊駐扎”(動詞)或“軍隊駐扎之所”(名詞)。所謂“軍隊駐扎”,亦可引申為休戰、止戰。簡文“為角龍之旗師以戰,為交龍之旗師以舍”,意思就是用角龍旗時出師交戰,用交龍旗時止戰回營。(9)程浩:《清華簡第七輯整理報告拾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7年4月23日。

關于本段簡文原整理者無詳說,王挺斌指出簡文“舊”的用法與上博簡《孔子見季桓子》22號簡“迷(悉)言之,則恐舊吾子”、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13號簡“女(汝)慎重君葬而舊之于三月”一致,都讀為“久”,訓為久留、等待之義。這種“久”的訓釋古書較為少見,一開始并沒有得到學者關注;陳劍先生在解釋《孔子見季桓子》22號簡“迷(悉)言之,則恐舊吾子”之“舊”的時候就曾疑惑猶豫,后來讀書會舉出《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為證,這才確定“舊吾子”當即讀為“久吾子”。簡文這種帶有軍事色彩的“舊(久)”,可以和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五名五恭》“軒驕之兵,則共(恭)敬而久之”之“久”合觀。(10)程浩:《清華簡第七輯整理報告拾遺》。
而簡文中所載的以日月為旗號,原整理者亦無說法。日月之形常出現于旗幟之上,典籍有記載,如《周禮·春官·宗伯》“日月為常。”鄭玄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釋名·釋兵》:“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日月”在典籍及文化意義中象征天地及天道秩序,《禮記·郊特牲》:“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荀子·天論》:“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也有學者認為日月與兵學文化中的“避兵”有關,如《兵避太歲戈》中的神靈腳踏日月。而李零也認為古代的避兵符以太一、北斗和日月為主。(11)李零:《“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235頁。耿雪敏認為軍旗上以日月為章,與《兵避太歲戈》上的日月圖案一樣,具有避兵的含義。(12)耿雪敏:《先秦的軍旗與兵陰陽家》,《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2年第12期,第47-51頁。任慧峰也認為軍旗不僅在戰爭中具有實戰作用,并且由于其可以體現古人信仰,而在古人心目中具有了溝通神靈、保佑平安、提高勝率甚至殺傷敵人等特殊功能。(13)任慧峰:《先秦軍禮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10頁。
筆者認為“日月”在典籍中記載十分豐富,可知與文化思想有密切關系,但簡文中的日月與避兵之間并無關連,而是應更直觀的去思考旗幟上日月的意義,簡文既然說“日月”象征“(師)以舊(久)”那么“日月”象征的應該是時間的經過,典籍中也會以“日月”表示時間之意,如《論語·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論語·陽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由此可見,簡文中的旗幟圖像應是以日月表示時間的經過,而象征部隊停留過久,不利于戰事。

原考釋者言熊、豹對應《周禮·司常》“熊虎為旗”,與《周禮·大司馬》《司常》所載職級相合。
謹案:在前文已經討論,旗幟圖像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記載中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就本段簡文而言,以“熊”表示大夫出,以“豹”表示士出,就具備了用動物間不同的大小特質表示不同的身份階級。首先,“熊”“豹”都是典籍常見的猛獸動物,如《大戴禮記·五帝德》:“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行其志。”而以動物表示諸侯大夫的等級之別,如《周禮·天官·冢宰》:“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又如《論衡·亂龍》:“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
以上都是以動物表示身份等級的差異,因此簡文此處的旗幟,應也具有同樣的意義。如《白虎通德論·鄉射》:“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


王寧認為“蕘”二字當讀“獌”或“獟獌”,亦即《爾雅·釋獸》之“貙獌”,《說文》:“獌,狼屬”。或云“貙虎”。“侵糧者”疑當讀“侵掠者”或“侵略者”,指外出作戰、侵掠敵國的士卒。(20)王寧:《清華(七)〈晉文公入于晉〉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網論壇,2017年4月28日。


三、結語
通過出土文獻中軍旗材料的記載,以及對傳世文獻的對比,可以發現旗幟的圖像與形制本身帶有因地因時表達意義的特質,雖然部分的旗幟材料仍具有其共通性,但自成系統仍是先秦旗幟展現的特色。而對于先秦軍旗的研究有助于先秦軍事學及旗幟制度的深入探討,《清華簡(七)·晉文公入于晉》中的軍旗,是很寶貴的文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