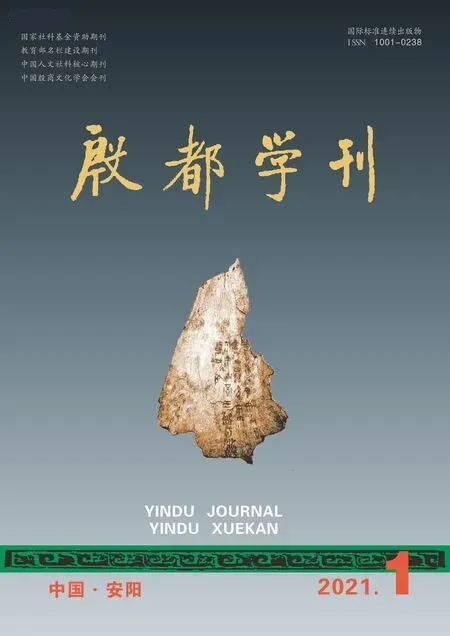西周金文“馭方”釋義辨正
王 碩
(北京師范大學(xué) 歷史學(xué)院,北京 100875)
“馭方”一詞幾次見于西周金文,專家學(xué)者對其有著不同的理解。“馭方”一詞的解釋往往關(guān)涉到西周某些歷史重大問題的理解,如雷晉豪先生認(rèn)為其中隱含有西周中、晚期王朝中央與南土在軍事制度與權(quán)力關(guān)系變遷的重要訊息;(1)雷晉豪:《征服與抵抗:周代南土的政治動態(tài)與文化轉(zhuǎn)型》,博士學(xué)位論文,臺灣大學(xué)文學(xué)院,2014年,第178頁。“馭方”與獫狁之間存在的密切關(guān)系也有可能會牽動對于西周覆滅的歷史解釋。(2)韓巍:《探尋西周王朝的衰亡軌跡——<西周的滅亡>讀后記》,香港城市大學(xué)中國文化中心編:《九州學(xué)林2010·春夏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4-295頁。新近發(fā)布的西周晚期銅器伯碩父鼎銘文為解決關(guān)于“馭方”的諸多爭議提供了重要線索。因此,筆者不揣鄙陋,試在專家學(xué)者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西周金文中“馭方”的含義及相關(guān)問題加以梳理辨析,不當(dāng)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相關(guān)研究之檢討
“馭方”一詞見于西周金文,包括鄂侯馭方鼎(《銘圖》02464)、禹鼎(《銘圖》02499)、不其簋蓋(《銘圖》05388)(3)除必要說明外,本文所引青銅器和銘文資料皆出自吳鎮(zhèn)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直接在銅器名稱之后用括號標(biāo)注(《銘圖》+原書編號)。等西周重器,諸家在研究相關(guān)銅器銘文時多有說明,然仍存在較大分歧。為方便討論,現(xiàn)將諸家研究頗多的包含“馭方”一詞的西周金文列舉如下:
鄂侯馭方鼎:王南征,伐角、僪,唯還自征,在坯,鄂侯馭方納壺于王,乃祼之。
禹鼎:鄂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內(nèi)。
同銘又說:禹以武公徒馭至于鄂,敦伐鄂,休,獲厥君馭方。
不其簋蓋:伯氏曰:“不其,馭方、獫狁廣伐西俞。”
前兩篇銘文跟鄂侯相關(guān),時代為西周厲王;(4)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古學(xué)報》1959年第3期。不其簋蓋記周與獫狁間的戰(zhàn)事,其時代學(xué)者多定為宣王。(5)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435-436頁。關(guān)于其中“馭方”的解讀,雷晉豪先生將代表性觀點(diǎn)加以分類整理,歸納為人名說、方位說、官職說。(6)雷晉豪:《征服與抵抗:周代南土的政治動態(tài)與文化轉(zhuǎn)型》,第178-179頁。郭沫若先生認(rèn)為鄂侯馭方與不其馭方為同一人,不其與馭方是一字一名,(7)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科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230頁。此說已經(jīng)不符合新的斷代認(rèn)識,一字一名的理解也難以成立。馬承源先生認(rèn)為“馭方”是鄂侯和獫狁首領(lǐng)之名,(8)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10頁。將“馭方”理解為鄂侯之名符合文例,但恐并不適用于獫狁之例,《國語·周語上》“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9)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diǎn)校:《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8-9頁。“樹”為犬戎首領(lǐng)之名,是私名加在部族名之后。

李峰先生認(rèn)為“馭方”是一種“尊貴的頭銜”,所有金文中只有兩個人有這一頭銜。(12)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jī)》(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1頁。雷晉豪先生在此基礎(chǔ)上加以闡發(fā),認(rèn)為不其馭方和鄂侯馭方即不其御方和鄂侯御方,分別為防御西方和南方邊區(qū)之人,“馭方”應(yīng)當(dāng)是因應(yīng)西周中、晚期邊境情勢而特設(shè)的職責(zé)。(13)雷晉豪:《征服與抵抗:周代南土的政治動態(tài)與文化轉(zhuǎn)型》,第179-181頁。“馭”與“御”相通甚或混用自不成問題,透過銘文詞語,深入挖掘背后的歷史信息,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鄂侯馭方鼎與不其簋蓋中的“馭方”是否可以等同起來,對相關(guān)歷史的解讀是否合適尚有討論的空間。
二、“馭方”釋義

新近公布的西周晚期銅器伯碩父鼎銘文對于重新審視此前的研究思路有重要幫助。伯碩父鼎為慶陽合水縣博物館藏該縣何家畔鄉(xiāng)南鹼一座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其銘曰:“我用爰司赤戎、馭方,伯碩父、申姜其受萬福無疆。”(16)梁云:《隴山東側(cè)商周方國考略》,文化遺產(chǎn)研究與保護(hù)技術(shù)教育部重點(diǎn)實驗室等編:《西部考古》第8輯,科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112-115頁。伯碩父負(fù)責(zé)管理“赤戎馭方”事務(wù),將此處“馭方”解為“朔方”表示地點(diǎn)或方位并不合適。趙慶淼先生在研究中表示更傾向于將“馭方”理解為通名,以“赤戎馭方”作一句讀,理解為守衛(wèi)邊疆的赤戎之族,(17)趙慶淼:《商周時期的族群遷徙與地名變遷》,博士學(xué)位論文,南開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2016年,第170-171頁。但將“赤戎馭方”與“馭方獫狁”對比合觀,赤戎、馭方、獫狁皆為部族之名的理解應(yīng)更為合理。
鄂侯馭方鼎和禹鼎中的“馭方”為鄂侯之私名,與不其簋蓋中的“馭方”應(yīng)分別看待。鄂侯馭方鼎“馭方拜手稽首,敢對揚(yáng)天子丕顯休賚”,按照金文常例,“馭方”的位置上是作器者的私名,禹鼎“獲厥君馭方”,“馭方”也應(yīng)理解為鄂君私名。在不其簋蓋中,前文“伯氏曰:‘不其,馭方、獫狁廣伐西俞’”,后文“不其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知不其是私名。比照鄂侯馭方鼎與不其簋的文例,將兩“馭方”等同起來認(rèn)為是官職或尊貴頭銜等有其難以克服的矛盾。總之,鄂侯馭方鼎、禹鼎中的“馭方”為鄂侯之私名,不其簋蓋中的“馭方”為一部族名,二者不必等同起來解釋。
三、余論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左傳·昭公十一年》),論者多以西周中晚期以來所面對的外患及因而覆滅來與此聯(lián)系起來思考,頗具卓識。西周在東南方向上面對淮夷的挑戰(zhàn),在西北方向上面對獫狁的威脅,其中鄂侯馭方所領(lǐng)導(dǎo)的淮夷叛亂是厲王朝及西周晚期政治走向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diǎn),但限于材料,我們無法得知鄂侯馭方與淮夷之間的實際關(guān)系,不排除因面對共同敵人為了利益臨時結(jié)合起來的可能,結(jié)合本文的分析,未可對鄂侯之“馭方”求之過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