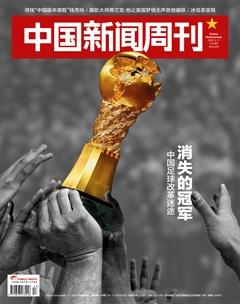出圈:青年亞文化與“主流”的互相靠近
郭超凱 馬帥莎 張蔚然
隨著以“00后”為主體的獨二代的成年,這個在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等新媒介文化土壤中生長起來的“網生代”,正在成為網絡文化的主力軍。而網絡媒介的快速成長和普及,青年亞文化實現了從相對封閉的“小眾團體”向整個社會開放的“普泛化”轉向,青年亞文化也頻頻“出圈”“破壁”。
20世紀30至50年代的芝加哥學派在關于種族、移民、犯罪等問題的研究中涉及青年亞文化,開啟了這一研究領域;發展至60年代,英國伯明翰學派對前者進行了繼承和反思,他們對青年亞文化所涉及的社會群體以及所展現出的“儀式抵抗”更感興趣,深入研究了青年亞文化的政治內涵和文化活力;進入后亞文化時代,青年亞文化“抵抗”精神的弱化以及亞文化自身多樣化、娛樂化、圈層化與消費主義的緊密結合,使得其內涵和價值迭代更為頻繁。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惠園特聘教授、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專家委員廉思表示,“在當前中國,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也存在著對抗與協商、爭鋒與合作的關系,但不同于國外以個人主義為文化核心、富有顛覆性意味的青年亞文化,中國的青年亞文化表現出一種對傳統文化和集體主義的偏好。”
中國新聞周刊:青年亞文化存在哪些熱點現象和熱點群體?他們關注的問題與訴求是什么?
廉思:青年亞文化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新媒體技術的創新而不斷分化,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態勢。在“嗶哩嗶哩”等視頻類平臺上,能夠感受到各種不同的亞文化類型,從動畫片、紀錄片、生活片等原創作品的嫁接和創新,到克魯蘇神話、蒸汽朋克、賽博朋克、艦娘等特定幻想概念,每一個分區都能代表一個熱點群體,其中不斷更新的內容顯示了當前青年亞文化的熱點現象。
從這些熱點現象可以窺見青年亞文化的一些顯著特征,比如符號話語的創制與應用;抽離現實的沉浸體驗,青年可暫時拋卻現實困惱,釋放壓力和焦慮。總之,青年亞文化表現的不再是一種“反抗”,而轉向“自我的彰顯”,也就是對自我的認知、認同與張揚,以及對自我價值的追求。
不同亞文化的背后是青年人共享的價值觀,年輕人通過互聯網擴大自己的社交圈,他們在一起閑聊,一起娛樂,傾訴心中秘密,與陌生人建立起緊密聯系。青年亞文化實踐行為中的“同人”“圈子”“群”“組”“部落”等命名方式,鮮明地反映出年輕人依托網絡進行陌生人之間的圈群化再聚合的特點。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正確看待青年亞文化及相關社會群體“圈層化”的現象?它對社會發展有何利弊?
廉思:青年亞文化以及相關群體“圈層化”的現象實際上是這部分青年彰顯自我存在和力量的結果。這些青年群體往往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地位、聲望等方面缺少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新生群體,但他們又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表達欲求,因此通過共同的興趣和愛好集結成一個個新族群。傳統社會中的族群往往以家庭、社區、學校和單位為紐帶,而很多青年群體則以興趣愛好來聚合、以價值認同為連接。新族群的形成正是亞文化“圈層化”的結果,他們試圖規劃勢力范圍,并通過各種亞文化符號來刷新主流社會對自己的認知。
“圈層化”會對群體中的每個個體產生很強的影響力和約束力,積極向上的青年亞文化對其圈內成員的認知和心態會產生正向影響,青年網絡技術的熱諳程度,以及信息獲取能力、傳播能力、文化產品再生產能力等得到鍛煉和提升。但同時,也要重視某些青年亞文化社群的封閉化傾向,信息繭房帶來的網絡群體極化和社會黏性喪失會在圈層區隔之下表現得更為劇烈。
中國新聞周刊:越來越多的青年亞文化正在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圈”,從原來的“小眾”影響到“大眾”。這些青年亞文化是如何“出圈”和“破壁”的?
廉思: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新媒體技術的普及給青年亞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多元文化融合的環境賦予了青年亞文化更大的發展空間,人們對于青年亞文化的包容度普遍提高,這使得青年亞文化能夠被社會大眾了解和認知。青年亞文化在弱化“對抗”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始對接主流文化和傳統文化,在保留原有的文化元素的同時與主流文化融合并存,亞文化因而具有了某些“主流”色彩。與此同時,主流話語權威也向亞文化尋找靈感和素材,力圖突破呆板僵化的表現形式,借助青年亞文化進行主流意識形態宣傳,如2021年春節晚會上的虛擬歌手、彈幕互動等,“出圈”與“破壁”是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
中國新聞周刊:從“蟻族”“工蜂”的觀察角度,你認為青年群體為什么會沉迷于青年亞文化?
廉思:單從“蟻族”和“工蜂”這兩個青年群體來看,前者是指受過大專以上教育,但收入較低,且處于聚居狀態的青年流動人口,后者是指在大學任教的青年教師,這兩類青年群體存在一定共性。
首先,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他們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識,力圖以知識的力量來改變社會中的某些不合理現狀。其次,他們是社會變革的先鋒力量,有表達訴求的意愿,希望通過自己對于社會公共生活的積極參與,來改善自身的環境,實現價值的追求。這兩類群體如今已經成為政策關注的重要對象。
從“蟻族”“工蜂”擴展到更廣泛的青年群體,我們可以發現,青年亞文化使當代青年在社會關系上呈現出“自我”到“我們”的轉向。年輕人更加自主、更為開放的尋求自我、表達自我和創造自我。而移動互聯網不僅能讓年輕人迅捷地傳遞關于“自我”的海量信息、提高“自我”的辨識度和能見度,還能讓他們在創制、傳播了自身文化后,迅速尋找到志同道合的“圏內人”,進入圈層、得到認同,獲得身份歸屬,反過來強化其“自我認同”。青年亞文化已經成為年輕人尋求身份認同的新坐標和新參照。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看待主流文化和青年亞文化的關系?青年亞文化對主流價值觀產生了哪些影響?
廉思:青年亞文化對于主流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傳播語言、傳播形式、傳播媒介帶給主流文化的借鑒意義。主流文化的傳播可能存在命令式的語言、單向的傳播方式、單調的傳播形式、相對單一的傳播媒介等不足,而青年亞文化的傳播貼合青年群體的特征,能夠消解青年群體對于主流文化的抵觸。可見,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既相互游離,又相互促進,呈現出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關系。當然,也不能否認青年亞文化的存在為主流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某些最初的動力、靈感和實驗。
當前,青年亞文化在促成年輕人交往、聚合、認同時的作用日益顯著,不同的興趣都能藉由互聯網切割出一片天地,將有共同愛好的年輕人跨階層、跨性別、跨時空連接起來。年輕人在宣傳主流文化時,也傾向于采取一些亞文化的方式。因此,要想在移動互聯時代玩轉“注意力政治”,吸引青年關注主流文化,就需要掌握將信息有趣且有效傳遞到青年那兒去的本領,就必須關注青年亞文化的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