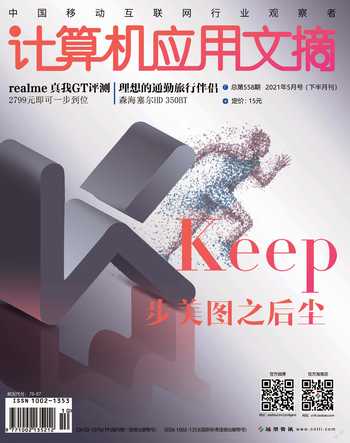奢侈品鑒定報告,可能也是假的
錦鯉財經

假貨蔚然,鑒定成為剛需業務
《2020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研究報告》顯示,受疫情影響,全球的奢侈品市場在2020年多少受到沖擊,只有中國是唯一增長的國家,據悉,2020年中國個人奢侈品市場同比增長48%,達到近3 460億元人民幣。
需要注意的是,這其中二手奢侈品交易占很大一部分。中國舊貨協會二手奢侈品工作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早在2016年我國二手奢侈品市場的年交易額就超過80億元人民幣,且每年以超過20%的速度在增長。據悉,2020年有七成以上的人買經典款的二手奢侈品,比買新款的2倍還多。
時至今日,消費者早已不像從前那樣從心理上抵觸二手舊物,尤其對于奢侈品來說,收藏或許意味著增值與保值,從某種角度上看,這也算是一種另類的投資手段。比如2015年,愛馬仕一款包在中國香港佳士得拍到22.3萬美元的高價。
當然,絕大部分人買二手奢侈品并不是為了收藏保值,紅布林平臺數據顯示,超八成用戶2018年花的錢不到4 000元人民幣,平臺二手奢侈品的定價大部分在市場價的3折以下,性價比是消費者選擇二手奢侈品的關鍵因素。
也正因如此,二手奢侈品市場打著價格戰的幌子,試圖渾水摸魚者甚多,久而久之,交易由一種經濟行為過渡成“玄學”行為,運氣加持下的消費端展開來看就是一場現實的魔幻主義大戲。
奢侈品流通中到底有多少假貨?客觀數據或許可以告訴我們答案。據悉,在2016年海外代購的奢侈品中約60%是假貨,《中國二手奢侈品市場發展研究報告2020》顯示,在2017年,優奢易拍鑒定的所有商品中僅有3成多為正品,且正品率在逐年下降,到2019年,綜合正品率為33.6%,相比三年前下降4個百分點。
特別是社交平臺壓縮了交易路線后,假貨愈加蔚然成風。數據顯示,2019年優奢易拍鑒定的商品中,有53%的假貨來自社交渠道,眼看市場物欲橫流,消費者惶惶不安,真假鑒定逐漸成為奢侈品渠道不可或缺的一環。
近年來,各大平臺的鑒定數量逐漸增加,2019年的鑒定數量約為2018年的2.3倍,且二手產品的鑒定占比高達72%,就算是全新奢侈品的鑒定比例也將近30%。回顧這一場場有風險的懸線生意,“買奢侈品,必鑒定”這是很多涌向消費升級的人的共同心理。
中國約有97%的奢侈品在個人用戶手上,有調查顯示,超過40%的消費者愿意為付費來鑒定產品真假,個人用戶鑒定高達80%以上。2019年以來,相比于此前的線上拍照鑒定,越來越多人更傾向于實物鑒定,2017年實物鑒定僅占25.9%,到2019年這個數值就達到41.3%。
如今,買奢侈品似乎已經深深地烙印在年輕人的價值觀上層,這或許是環境壓力下的無奈之舉,然而可悲的是,當一件件假貨撲面而來,何去何從,誰都沒有確定的憑據。
當制造水平“封神”,鑒定師陷入“精致陷阱”?
提及奢侈品鑒定,在中古文化濃厚的日本最為成熟,公開資料顯示,在日本出自鑒定師之手的鑒定報告,甚至可以得到相關部門的認可。國外奢侈品鑒定師屬于高薪職業,平均年薪都會在10萬元人民幣左右,資深的鑒定師則可以拿到5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
反觀國內,目前國內還沒有針對奢侈品鑒定師開出的培訓課程,也沒有相關的認證體系。職業標準的欠缺致使行業正野蠻生長,不少機構趁機入局瘋狂圈地跑馬,有關奢侈品鑒定的課程源源不斷地涌現。
更關鍵的是,這些課程價格居高不下,一周的培訓費用高達14 000元人民幣到49 000元人民幣。以中奢中心為例,箱包類產品培訓周期為7天,價格高達17 800元人民幣,腕表類產品培訓5天,要價14 800元人民幣。
至少就目前來看,國內專業的鑒定師寥寥無幾,有調查曾經披露過具體的數字,國內的資深鑒定師具體不超過100位。在得物上,平臺鑒定師不到20位,日均鑒定數量卻高達300到3 500件,2019年8月是炒鞋巔峰期,知名的鑒定師日均鑒定數能在2 000雙以上。
一邊是接踵而至的真假產品,一邊是精力有限的鑒定人員,當工作量極端膨脹,鑒定過程卻往往只有幾分鐘,發生鑒錯事故在所難免。更何況,國內的制造水平早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即便是經驗豐富的鑒定師稍不留神,也會陷入“偽精致陷阱”里。
我國制造技術的影響力向來不可小覷,不僅吸引著眾多奢侈品牌紛紛建廠代工,也為龐大的山寨產業孵化了技術溫床。例如耐克,從1981年到現在,耐克在中國的代工廠有近200家,工人總數超過20萬;此前,巴黎世家也將代工廠從意大利遷到中國莆田。
除此之外,阿迪達斯、PUMA、KAPPA、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在莆田代工生產,一時間,潮鞋是年輕人奢侈品中的假貨重災區。
有媒體曝光過部分假鞋產業鏈不僅仿制鞋子的技術出神入化,連鞋盒,購買清單與發票都一應俱全,有的交易平臺甚至在售賣正品鞋盒。曾經有耐克員工在采訪中表示,全球每3雙耐克中,就有1雙是“莆田假鞋”。
不可否認,純熟的制造技術將國內鑒定門檻無形中高了不少,有資料顯示,約有28%的奢侈品假貨能仿造得分毫不差,正常鑒定流程很難區分真假。2019年,在鑒定平臺正品率倒數前十的品牌中,最高的也不過39.4%,在國內有多個代工廠的Michael Kors的正品率低至16.5%。
有意思的是,盡管鑒定師的培訓熱度如火如荼,但培訓學員中真正從事鑒定業務的只有5%左右,絕大部分選擇自立門戶,代購微商或者開二手奢侈品店,其中線下開店的就占30%以上。
另一方面,在鑒定圈,代購與鑒定師相互串通,暗中牟利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之事,甚至一紙鑒定證書只需要十幾元人民幣。鑒定背后或許沒有真假可言,這是一場人心博弈,無論輸贏,只論利益。
奢侈品主義:心理安慰還是游戲?
古希臘時期,奢侈的概念一直是人們持續爭論的熱門話題,支持者認為奢侈品是社會進步推動力和有高追求的標志,反對者則將其視作“意義道德”。
英國工業革命后,消費需求催生出一個神話般的消費時代,這個時代為世界彌留下兩個最重要的理念,一個是營銷,一個是時尚,時至今日,這兩個理念依舊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并不斷踩著消費鏈上的焦慮爽點,制造社交距離。
同樣的,這也是一種新的剩余價值剝削方式,即督促消費,鄙視淡欲。
我國究竟用了多長時間變成奢侈品消費大國的并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那些收入不高卻依舊瘋狂追捧消費升級的人,奢侈品的購買欲望爆炸通常只有幾分鐘的時間。這其中,可能是社交平臺上的一句“心靈雞湯”,也可能是影視劇里的一段對白。
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只有19853元人民幣,但中國消費者卻貢獻了全球32%的奢侈品消費,業內專家預測,2025年,全球46%的奢侈品最終將賣到中國消費者手中。
去年的熱播劇《三十而已》里江疏影有句臺詞“鉆石與珠寶承載著女人的夢想”,雖然這句聽上去資本意味極重的話在微博上曾經掀起一場罵戰,但不可否認,在現實生活中,奢侈品消費在很多人的眼中可以直接與階層感受相掛鉤。
比如我們時常聽到有人說,“男生一定要有一只戴出去不露怯的手表”“女生必須有一個能讓自己底氣十足的包包”……在消費主義面前,一個人與自己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外界的符號價值所提供的,與其說奢侈品販賣的是商品使用功能,倒不如說是其品牌背后象征的身份基因。
不止中國,奢侈品在拉丁語中,除了是價格不菲的物品,還有“創造舒適和愉悅感受的物品”的意思。2013年,巴黎奢侈品導購界統計過一組很出名的數據,99%購買奢侈品導購雜志的人,其月收入在8000歐元以下,形成所謂的“拜物教”,與真正奢侈品的目標客戶群相差甚遠。
誠然,年輕人走向奢侈品的第一步就被醒目的LOGO綁架了購買自由,即使是經濟實力不允許,也要通過各種渠道買一個來歷不明的包,到手之后卻又免不了重重猜忌。正如某資深鑒定師所說,“很多人選擇鑒定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真假,只是為了求一個心安與底氣。”
更諷刺的是,在奢侈品交易中的真假與否僅占購買時考量因素的41%。我們看得見的是一張張鑒定報告,看不見的永遠都藏在不可言明的隱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