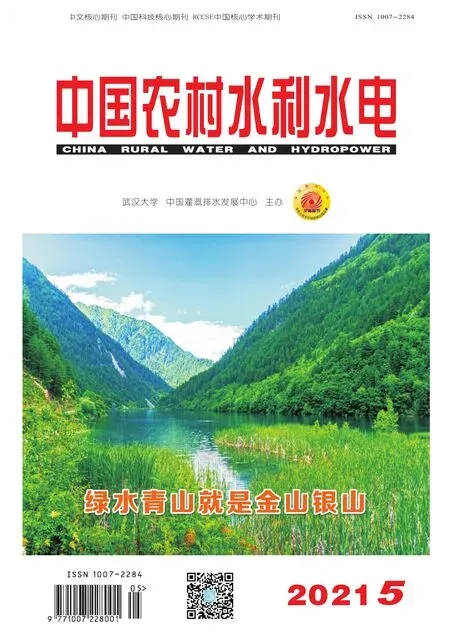2000-2015年中國草地生態系統水分利用效率時空特征及其對氣候要素的響應
陳鑫濤,鄧 超
(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學院,南京210098)
0 引 言
水分利用效率(Water use efficiency,WUE)是指植物消耗單位質量的水分所能固定的CO2或者生產的干物質的量[1,2]。本文中生態系統的WUE定義為總初級生產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GPP)與實際蒸散發(Terrestrial evapotranspiration,ET)之比。它是度量生態系統碳-水循環耦合的關鍵因子,也是評估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影響的重要指標[3]。研究WUE時空變化特征及其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對于理解生態系統在全球碳水循環中的作用,解釋生態系統生態水文過程變化規律有重要意義。
草原生態系統是全球范圍內分布最廣的生態系統之一。中國草地分布廣泛,占國土總面積的近40%,在區域碳收支、水量平衡和糧食安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一些學者在不同尺度上對中國地區草地生態系統的水分利用效率展開了大量研究。Hu等[4]利用渦動通量塔的觀測數據計算WUE,評估了中國4個草原生態系統WUE的多時間尺度變化。裴婷婷等[5]利用MODIS 數據,開展了黃土高原草原生態系統WUE對氣候和植被指數的敏感性研究。常娟等[6]利用LPJ 模型模擬了西北地區草地GPP和ET,計算WUE并對其開展了時空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從氣候要素對WUE的影響來看,氣候要素的變化會引起植被的光合作用增強或減弱導致GPP改變,同時ET也會隨著截留、土壤蒸發和植被蒸騰而增加或減少,從而影響到WUE[5]。如,史曉亮等[2]基于渦度數據研究發現草原站點在溫度升高下,GPP的增加速度大于ET的增加速度導致了WUE的增加。在空間尺度上,氣候因素的空間變異性是影響WUE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Xu 等[8]指出在干旱區WUE在區域上的分布隨干旱指數升高而降低。WUE對關鍵氣象要素的響應研究有利于揭示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響應機制。但目前針對草地WUE與氣象要素的響應研究大多局限于站點和個別區域,大范圍的全國區域的草原生態系統WUE的時空分布以及其對氣候因素響應的研究開展較少。
因此,本文通過引入土壤水分脅迫因子改進PML-V2 遙感估算GPP-ET 耦合模型,利用改進的模型估算了中國草原生態系統2000-2015年的總初級生產力和實際蒸散發數據,討論了GPP、ET和WUE年均值的空間分布和年際變化趨勢,定量分析了年尺度上WUE對氣象驅動因子的敏感程度,旨在為中國草原生態系統水資源合理利用及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參考。
1 研究區域與數據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主要包括內蒙古,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是中國草地的主要分布區域[7]。黃土高原地處中國中部(100°~114°E,33°~41°N),總面積64 萬km2,包括7 個省和自治州。氣候上處于半干旱半濕潤氣候帶,年降水量150~800 mm,年均氣溫4~14 ℃,年蒸發量1 400~2 000 mm;黃土高原土質疏松,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9]。內蒙古地區氣候由東部半濕潤溫帶季風氣候向西部內陸干旱半干旱氣候的過渡;年平均氣溫0~8 ℃,年平均降水量50~400 mm,自東北向西南遞減;青藏高原位于中國西南地區(73°~105°E,26°~10°N),平均海拔4 000~5 000 m,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地貌復雜多樣,氣候類型豐富,主要以濕潤、半濕潤、半干旱和干旱為主;輻射強,溫度低,日溫差大,降水差異顯著是青藏高原的氣候特征,平均氣溫為0 ℃,最大日溫差高達22 ℃,降水100~1 000 mm,由東南至西北遞減[9]。研究區域位置分布見圖1。

圖1 研究區域位置分布圖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氣象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區域高時空分辨率地面氣象要素數據集(CMFD)和普林斯頓氣象要素再分析數據集(PGF)。CMFD 數據是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成的一套中國區近地面氣象與環境要素再分析數據集(http://westdc.westgis.ac.cn/),其時間分辨率為3 h,水平空間分辨率為0.1°。本文采用了CMFD 數據集中的近地面氣溫、氣壓、空氣比濕、風速、下行短波輻射、降水量6 個變量。模型所需要的遙感數據主要為葉面積指數LAI 數據、陸表反照率、發射率,均來自全球陸表特征參量產品(GLASS),空間分辨率為1 km/0.05°,時間分辨率為8 d。植被類型數據來自美國NASA數據中心MCD12Q1數據集。CO2數據來源于NOAA 全球平均海面月平均CO2數據(ftp://aftp.cmdl.noaa.gov/products/trends/co2/co2_mm_gl.txt)。ESA CCI_SM 產品是歐空局研發的空間分辨率為0.25°的逐日土壤水分數據集,分為主動、被動和主被動融合3 種產品。本文采用主被動融合數據作為模型的驅動數據,并采用王國杰等[10]提出的基于三維離散余弦轉換的乘法最小二乘回歸模型插補缺失值。以上柵格數據均重采樣至0.05°,時間尺度上統一到8 d,并使用植被分類數據對中國草地區域進行掩摸,選取時間段為2000-2015年。用以模型驗證的GPP和ET數據來源于FLUXNET2015 數據集中的中國草地生態系統渦度通量塔觀測數據(http://fluxnet.fluxdata.org/data/fluxnet2015-dataset/),站點包括當雄站、多倫(二)站、多倫(三)站、海北草甸站、四子王旗站、長嶺站(表1)。

表1 通量站點信息Tab.1 Description of flux stations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改進
PML-V2模型是Zhang和Gan等[11,12]在Penman-Monteith-Leuning(PML)模型的基礎上,改進構建的新一代GPP-ET 耦合模型。PML-V2 基于生態物理機制,通過氣孔導度公式耦合了GPP和植被蒸騰,同時提升了GPP和ET的估算精度,其性能表現優于同類型的GPP或ET單一模型。
Pei 等[13]在研究中發現PML-V2 模型在干旱年的草地GPP估算中表現不佳。Bagher Bayat 等[14]在研究中通過結合土壤水分脅迫參數和最大羧化能力Vcmax參數,提升了SCOPE 模型在干旱時期的GPP和ET估算能力。由于中國草地生態系統經常遭遇干旱,本文通過引入土壤水分限制系數,調整了模型中與最大羧化能力Vcmax參數性質相似的名義最大羧化能力Vm參數,以使模型更適用于研究區,并利用改進后的模型計算了中國草地生態系統的ET和GPP,并進一步計算了WUE。

式中:SF為土壤水分限制系數;θ為土壤含水量;θw土壤凋萎含水量;θf為土壤田間持水量。SF>1時,SF=1;SF<0時,SF=0。
WUE定義為單位時間內陸地生態系統總初級生產力GPP和實際蒸散發ET的比值:

式中:WUE為生態系統水分利用效率,g/(m2?mm);ET為蒸散發,mm/d;GPP為總初級生產力,g/m2。
2.2 趨勢分析
本文采用Theil-Sen 非參數趨勢分析方法計算2000-2015年中國草地生態系統的GPP、ET和WUE的變化趨勢,并通過Mann-Kendall趨勢檢驗進行顯著性檢驗[15,16]。該方法不要求樣本服從一定的分布,不受異常值的干擾,對線性變化趨勢的估計較為可靠。Sen斜率值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β為時間序列的變化趨勢值;xi和xj分別代表在時刻i和時刻j對應的數據值;Median 為中位數函數。當β>0 的時候,表示上升趨勢;當β<0的時候,表示下降趨勢。
2.3 相關性分析
本文采用二階偏相關分析方法,以在消除其他變量的干擾下研究氣候因素對水分利用效率的影響[17]。二階偏相關分析方法可以在消除其他兩個變量的干擾下,對兩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利用太陽輻射,氣溫,降水和WUE的年均值,對每個柵格計算WUE對太陽輻射,氣溫和降水的二階偏相關系數。首先,進行一階偏相關系數的計算:

式中:rab,c是消除c變量影響的a和b的一階偏相關系數,rab,rac和rbc分別是a和b,a和c,b和c的相關系數。
二階偏相關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rab,cd是消除c,d變量影響的a和b的二階偏相關系數。
3 結果分析
3.1 模型驗證
PML-V2 模型在中國及世界范圍內多種生態系統的應用中,表現優于同類型的GPP或ET單一模型。針對模型對于干旱年的草地GPP估算表現不佳的問題,本文加入了水分脅迫因子對模型中Vm參數進行優化。
通過6個分布于中國地區草地生態系統通量站觀測獲得的ET和GPP數據對改進后的模型模擬結果進行驗證。圖2中結果表明模型在研究區內可以較好地模擬GPP和ET,模型模擬效果在R2和RMSE兩個指標上表現優異。GPP在檢驗中R2為0.651,RMSE為1.046 g/(m2?d),ET在檢驗中R2為0.72,RMSE為0.590 mm/d。

圖2 模型結果驗證Fig.2 Comparison of model result and observation
3.2 GPP、ET和WUE的時空變化特征
3.2.1 空間分布特征
研究區草地生態系統GPP、ET和WUE具有明顯空間差異。多年平均GPP呈現西北向東南遞增的空間變化趨勢,青藏高原東南部是GPP最高值分布的地區,見圖3(a),區域均值為474.3 g/(m2?a)。ET空間分布格局和GPP相似,區域多年均值為407.4 mm/a[圖3(b)]。從圖3(c)中結果可知,WUE多年均值為1.1 g/(m2?mm)且WUE均值的區域分異明顯。研究區內WUE空間分布受GPP影響較大,比較接近于GPP的分布,大致表現為西北向東南遞增的空間格局且高值WUE與高值GPP基本分布于同一地區,見圖3(c)。這與研究區內降水量分布相一致,其主要原因是草地生態系統大部分處于干旱半干旱區,水分是制約這一地區植被光合作用和蒸散發的主要氣候因素[6]。青藏高原西北與內蒙古地區WUE最低[<0.4 g/(m2?mm)],這可能與這些地區受低溫和降水的制約以及植被稀疏有關[18]。

圖3 中國草地GPP、ET和WUE空間分布特征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PP,ET and WUE values for grassland in China
3.2.2 變化趨勢
分別對2001-2015年研究區草地生態系統年際GPP、ET和WUE進行趨勢分析(圖4~6),圖6中左上角小圖中灰色柵格為變化顯著區域(p<0.05)。研究區區域平均GPP、ET和WUE均呈現顯著增加趨勢,且GPP增加斜率大于ET,這也是WUE增加的主要原因。在2012年之后WUE有顯著增加趨勢,其潛在原因可能是2012年之后降水的顯著升高所引起的GPP大幅上升[6]。在趨勢的空間分布上,研究區內大部分區域的ET和GPP均呈增加趨勢,顯著增加的區域面積均占到了47%。WUE的顯著增加和顯著減少面積為0.25%和0.11%(圖5)。其中黃土高原WUE顯著上升的人為原因可能來源于生態恢復工程在近年來的大規模建設[19]。

圖4 中國草地區域平均GPP、ET和WUE年平均變化趨勢Fig.4 The inter-annual change and trends of China's grassland GPP,ET and WUE

圖5 中國草地GPP、ET和WUE不同趨勢等級的面積占比Fig.5 The proportion of grassland area in China with different trend levels of GPP,ET and WUE
由于WUE的變化趨勢與GPP和ET二者變化趨勢密切相關,本文進一步基于柵格辨析了WUE變化趨勢的主導因素,即當GPP和ET處于相同趨勢時將趨勢程度大的一方作為影響WUE趨勢的主導因素[圖6(d)]。其中內蒙古地區由于GPP和ET的相反變化,WUE變化趨勢為整體增加中部減小。青藏高原則由于ET的強勢變化,WUE變化趨勢的空間分布和ET相反,為整體減小東部少量地區增加。黃土高原地區由于GPP增加趨勢大于ET,GPP作為主要因素使得WUE減少且趨勢大小的空間分布與GPP均由西北向東南增加(圖6)。影響WUE趨勢的主導因素在地區之間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其可能與生態系統的生物過程(如光合作用、蒸騰)和物理過程(如土壤蒸發、截留)在WUE變化中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有關[20]。如,在植被茂盛區域,蒸騰在是ET的主體組成,WUE在數值上與GPP與蒸騰的比值相近,則WUE的變化更多地依賴于生物過程而不是物理過程。而在植被稀疏的區域,土壤蒸發在ET中的比重上升,物理過程更多地影響到WUE的變化。

圖6 2000-2015年中國草地GPP、ET和WUE變化趨勢及其主導因素Fig.6 The change trend of China's grassland GPP,ET and WUE and its dominant factors from 2000 to 2015
3.3 敏感性分析
為了直觀地表現氣候因子對WUE年際變化關系的空間分布,本文基于柵格計算了2000-2015年中國地區草地生態系統WUE與年降水量、年平均氣溫和年太陽輻射輻射的偏相關系數,用以分析氣候因子和WUE的年際變化的關系。如圖7(a)所示,在研究區大部分地區(65.9%)降水和WUE為負相關,少部分正相關關系地區分布在青藏高原東北區,黃土高原東北部和內蒙古北部。氣溫與WUE的相關關系與降水和WUE的相關關系在整體上相反,62.5%面積的研究區氣溫與WUE呈現正相關關系,零星的負相關關系地區分布在青藏高原中部和內蒙古南部[圖7(b)]。草地生態系統WUE的年際變化對于太陽輻射的響應呈正相關和負相關的區域分別占總面積的48.8%和51.2%。相比于正相關關系的分布的區域,負相關系區域分布較為集中,主要位于黃土高原和內蒙古中部[圖7(c)]。
本文進一步通過標準化3 個氣候因子對WUE的相關系數計算了其對WUE變化的相對貢獻度[圖7(d)]。圖中柵格顏色越靠近圖例中氣溫、降水和太陽輻射之一所代表的純色,就意味著這個顏色對應的氣候因子對WUE變化的影響越大。研究區大部分區域分別受太陽輻射和氣溫的主要影響。特別是青藏高原東部和內蒙古北部WUE主要受氣溫主要影響,且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些地區植被常年處于低溫的生長環境,在氣溫升高影響下,光合作用增強幅度相比于植被蒸騰和土壤蒸發更大,導致了GPP增長強于ET增長,從而導致了WUE上升[21]。同時太陽輻射在內蒙古中部和黃土高原南部為WUE的主要影響因素,且為強負相關關系。表明在較低輻射下,這些地區生態系統的WUE較高,和宋成剛等在青海海北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能是植被實現最優水分利用效率的適應性策略[22]。

圖7 中國草地生態系統WUE與氣象因子相關性以及相對貢獻圖Fig.7 Correlation between WUE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China's grassland ecosystem
4 結 語
本文通過引入土壤水分脅迫因子改進PML-V2 遙感估算GPP-ET 耦合模型,基于改進的模型估算了中國2000-2015年草地生態系統總初級生產力GPP和蒸散發ET,并進一步估算了水分利用效率WUE。采用趨勢分析和偏相關分析方法,探討了WUE的時空變化規律及與氣候因素的相關性。主要結論如下。
(1)引入水分脅迫因子對PML-V2 模型中Vm參數進行制約實現對模型的優化,改進后的模型在研究區內GPP的估算值與通量站GPP數據的R2和RMSE分別為0.65和1.046 g/(m2?d),而兩者ET的R2和RMSE分別為0.72和0.590 mm/d。
(2)中國草地生態系統WUE具有明顯空間差異,大致表現為西北向東南遞增的空間格局。這樣的變化格局主要來源于總初級生產力GPP的影響。
(3)中國草地生態系統區域平均WUE增加趨勢顯著,在空間分布上為整體上升,少量下降趨勢地區分布在青藏高原東部和內蒙古中部。研究區東部和西部WUE變化趨勢分別受ET和GPP的主要引導。
(4)研究區的大部分地區降水和WUE為負相關,氣溫與WUE為正相關。WUE與太陽輻射的相關性空間分布復雜,負相關區域主要集中在黃土高原和內蒙古中部。研究區大部分地區受到氣溫與太陽輻射的主要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