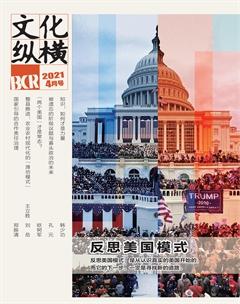鄉村振興的理論與實踐
農村是我國近六億農村人口賴以生存的土地,是糧食供給和生態安全的根本保障。城市與鄉村問要素的流動、整合、轉換,貫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城鄉關系也因此成為理解當代中國的關鍵線索。2020年,隨著最后5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三農”工作重心發生歷史性轉變。202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今后農村工作的重點,這是繼2017年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再次將鄉村振興戰略放在農村發展的首要位置。
從新農村建設到脫貧攻堅再到鄉村振興,農村工作的政策指揮緊隨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構變遷。在新發展階段,農村既不能單方面服務于城市發展,也不應單方面依賴城市的幫扶。農村應成為真正的發展主體,在經濟發展、社會協調等方面發揮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鄉村振興戰略釋放出的,正是這一發展轉型的關鍵信號。如何理解鄉村在中國未來發展中的作用和位置?如何從理論上理解、在實踐中推動這一轉變的發生?本期“鄉村振興的理論與實踐”專題,試圖從頂層設計、地方推動和村莊發展這三個層面,展現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對鄉村振興的構想與實踐。
準確把握戰略意圖,是有效推動改革的基礎。宋棠的《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一文,從幾組關鍵概念的辨析入手,解讀了作為政策術語的“鄉村振興”背后的改革意向與戰略意涵。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不僅僅是動員口號的更迭,更是一整套政策體系的轉向。農村發展定位的轉變、新型城鄉關系的提出,也要求鄉村研究發展的進步。作者指出,或許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農村問題”,研究者應該把視角打開,用城鄉的視野觀察農村,以更大的區域單位研究村莊。地方政府是將改革意圖轉化為改革實踐的關鍵執行人。總體方向明確后,地方政府如何結合地方知識與地方資源,協助搭建起改革的行動空間?王立勝、劉岳的《整縣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濰坊模式”》一文以濰坊農業產業化的成功經驗為例,從政府角度,總結了推動鄉村振興的地方經驗。在濰坊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在產業政策制定、資金投入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性的引領作用,成功將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體系對接;在治理層面,特別把握住了縣域這一關鍵的發展單元,實行整縣推進,讓濰坊在依托第一產業進行內生性發展的條件下,從一個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發展為較發達地區。村莊是鄉村振興的具體行動者。劉炳輝《鄉村振興的“寧波經驗”》一文就聚焦于村莊這個基本發展單位,展現了寧波五個不同地理條件、不同資源稟賦的村莊,探索最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的歷程。盡管背靠寧波優越的區位條件,五村都經歷了曲折的探索過程。作者將村莊的具體實踐放在一個較長的歷史跨度中加以審視,從微觀經驗透視出時代景深,并由此總結出:在村莊發展道路的司題上,或許并不存在一個標準答案,但保持對政策動向和歷史趨勢的敏銳洞察,或許是萬變中的不變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