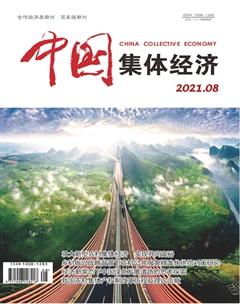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現狀研究
趙仁睫


摘要:基于成渝城市群2008年到2018年共11年數據,從三個角度切入,分析研究近年來成渝雙城經濟圈的結構分布、區域差異和發展趨勢,得出如下結論:從經濟的整體發展來看,成渝雙城經濟圈呈現“中心競爭,散點乏力”。從產業結構來看,成渝經濟圈整體以第二產業為主。從消費和投資來看,經濟圈整體消費水平和科技投資并不高。
關鍵詞:成渝雙城經濟圈;成渝城市群;成渝
自2020年1月3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后,相關落地工作在川渝兩地的各個層面持續推進。4月2日,四川省人社廳與重慶市人社局簽訂《共同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川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合作協議》。4月29日,川渝兩地國資國企宣布共同出資組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發展基金,基金總規模300億元,首期規模計劃100億元。
盡管四年前國務院批復《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后,成渝城市群正式邁入歷史。但受制于種種原因,成渝地區的發展困于戰略層面,行動上的進展有限。如今成渝雙城經濟圈的提出,更加清晰的明確了戰略方向:對標京津冀等三大城市群,形成西部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打造內陸開放戰略高地。
為了更直觀的了解成渝地區近年來的發展。本文第一部分針對成渝城市群的人口、產業、內需外貿等宏觀經濟層面,選取2008年到2018年共11年16個地市級及以上城市為對象。從人口和產業結構、貿易和進出口、科技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三個方面多角度切入,探析成渝經濟圈的整體構架和區域差異,力求更立體、全面的找到打造成渝雙城經濟圈的方向。第二部分總結現狀,得出結論并提出建議。
一、成渝城市群經濟發展對比
(一)人口和產業結構
整體來看,從2008年到2018年,16個地市級及以上城市GDP均顯著增長。如圖1,所有城市2018年的GDP比2008年的GDP增長均超過一倍,超過兩倍的城市有11個,成都更是直奔三倍。
但從個體來看,兩極分化的情況十分嚴重。重慶和成都遙遙領先其余14城。2008年重慶和成都兩座城市的GDP總量占16個城市的GDP總量的57.69%。這種懸崖式的斷層現象并沒有隨時間的流逝而改善,2018年,重慶和成都兩座城市的GDP總量占整個城市群GDP總量的62.09%,比2008年增加了約5個百分點。排名第三的綿陽的GDP僅是排名第二的成都GDP的15%,排名墊底的雅安的GDP只有成都GDP的4.2%。
觀察十一年的人口數據發現,除了重慶和成都有明顯的增長態勢外,其余城市常住人口并沒有顯著的增加,甚至出現連續數年下滑,比如資陽。對比2018年和2008年兩年的數據,僅有不到一半的城市,2018年的人口比2008年的人口有所增加。所有城市中,只有成都一個城市增長率超過10%,達到28.53%。重慶隨排名第二,但增長率,僅為9.26%。但呈現人口負增長的城市中,負增長率超過10%的城市卻有三個之多,資陽更是達到-40.66%。
成渝城市群16個城市,每個城市相比于GDP的成倍快速增長,人口的增長率都顯得微不足道。即使是領頭的重慶和成都,其各自人口的增長速度和經濟的增長速度差距也很大,說明對人口的吸納能力還亟需挖掘。除此還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廣安雖然人口增速呈現很大的負增長,負增長值甚至僅次于資陽,排第二,但是廣安的GDP增長速度卻并不慢,在所有城市中達到中等水平。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重慶和成都均為二產占比逐年降低,三產占比逐年上升。但是直到2015年,重慶的三產占比與二產占比的差距才開始逐漸拉開。2018年三產占勉強超過50%,二產占比降為40.9%,三產占比與二產占比的差值首次突破10%。而成都2008年三產占比就已經達到49.4%,三產和二產的占比差距始終保持3.5個百分點以上,近三年連續突破10%。說明從根基上,重慶更偏重于制造業、建筑業等第二產業,而成都則維持并穩步擴大著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其余14座城市二產占比和三產占比的曲線均表現為“眼狀”變化。即二產曲線在三產曲線之上,二產占比先增后降,三產占比先降后升。大多數城市直到2018年,三產占比仍舊低于二產占比。只有綿陽、樂山、達州三座城市三產占比實現反超。
但從產值絕對量來看,無論是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重慶和成都都以絕對的優勢甩開其它城市。2008年重慶和成都第二產業產值合計占16座城市總值的55.35%,2018年占比增加到60.21%。2008年成渝雙城第三產業產值合計占16座城市總值的69.04%,2018年占比為67.83%。第二產業產值排名第三的城市是德陽,三產產值排名第三的城市是綿陽。雅安無論是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產值排名都墊底。二產產值增長率最快的城市是成都和瀘州,重慶排第六。三產產值增長率最大的前兩個城市是樂山和眉山,增長率超過成都和重慶的城市有9個。
綜上所述,重慶和成都兩座城市是整個成渝經濟圈的兩大絕對核心,其余城市無論從GDP總量、增速,人口總量、增速都遠不及成渝兩城,整體發展呈現懸崖式的落差,且這種差距從2008年到2018年并沒有縮減,甚至更為嚴重。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從產業結構上看,盡管成渝仍然是短期內無法撼動的大頭,但是其余14座城市在第三產業產值增長上的貢獻還是肉眼可見的。
(二)貿易和進出口
本文采用全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衡量各城市貿易情況,進出口總額衡量各城市外貿情況。從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的絕對量來看,2008年到2018年十一年間,重慶以第一領跑,成都緊隨其后,到2018年,重慶達到7977億元,成都達到6802億元。其余14座城市,消費總額最高的是綿陽有1149億元,只有成都消費總額的16.9%,最低的雅安僅為242萬元,不到成都消費總額的3.6%。表明在消費內需上,依舊呈現重慶和成都兩大頭斷崖式領先的局面,且差距比各城市GDP間的差距還大。
從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的增長來看,16座城市消費總額增速在2010年后均呈現逐年放緩的態勢,即使部分城市在2015年有少許波動,但是仍然改變不了整體下滑的走向。尤其是2018年增速的下降十分顯著,包括重慶在內的四個城市甚至出現負增長的情況。
進出口總額的變化與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的變化不同。2013年以前,重慶的進出口總額并不及成都,2013年開始重慶進出口實現反超,隨后兩年持續擴大了差距。但2015年以后成都增長加速,在2018年逐漸逼平重慶。從總量上來看,成都進出總額最大值出現在2018年,而重慶出現在2014年。從增長率來看,成都進出口總額增長率最快為2017年的42.25%,而重慶最快為2011年的135.13%。表明成都近幾年外貿行業的發展增長更穩定和持續。
(三)科技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
為深化改革開放,發展高科技是助力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條件。為此中央自2006年頒布二十多項政策意見指導各地區發展科技。本文選取2008年和2017年科技支出以及科技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值,對比各城市在科技層面的發展狀況。
相關數據表明,除德陽和資陽,其余14座城市2017年科技支出比2008年增長都超過一倍。瀘州以高達846%的增長率遙遙領先,其次是成都,增長率為526%,重慶以292%的增長率排名第四。單從科技支出來看,成渝城市群的在科技層面的進步十分迅速,但是從科技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值來看,16座城市對科技發展的重視程度并不如預期。
具體而言,16個城市中有7個城市的占比增長率為負,最低的占比增長率是資陽的-47.73%,超過60%的城市只有成都、瀘州、綿陽、雅安,重慶的占比增長率僅為30.96%,比成都低了50個百分點,綿陽是唯一一個占比翻倍增長的城市。總的來說,無論是科技支出還是科技支出占比,重慶、成都、瀘州、綿陽、內江、雅安六個城市的發展還是相對較好的。
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的拉升作用是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反映出固定資產投資效率,以及經濟對投資的依賴程度。
如圖2,從曲線上看,瀘州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最快,雅安的增長最慢,除了重慶、成都、綿陽、雅安和資陽,其余11座城市的增長率均超過100%。從比重變化來看,重慶、成都等8座城市2018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較2010年有所下降,且均低于2018年全國的比重,說明重慶、成都的經濟發展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程度降低。
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前文三方面的數據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結論。
1. 從經濟的整體發展來看
成渝經濟圈呈現明顯的“中心競爭、散點乏力”的狀態。“中心競爭”指重慶、成都經濟發展以絕對優勢遙遙領先其它城市,成為成渝經濟圈的毋庸置疑的兩個中心。同時重慶和成都在發展上存在諸多相似的路徑,造成資源爭奪、產業過度重復的競爭局面。“散點乏力”指除重慶和成都外,其余城市的發展沒有形成區域化、一體化的結構。它們不僅沒有倚仗地理上的近鄰優勢,受成渝雙城發展的輻射影響,也沒有彼此聯結相互作用。如果將重慶和成都看作成渝經濟圈的第一梯隊,德陽、綿陽、宜賓和南充四城則是第二梯隊。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這四座城市只有德陽緊挨著成都,其余三城與成都和重慶都間隔了至少一座城市。德陽、綿陽和南充靠北,宜賓在最南邊,它們均不處在重慶和成都連線的中間地帶,而中間地帶的資陽反而是發展最差的城市之一。
2. 從產業結構來看
成渝經濟圈整體仍是以第二產業為主,重慶和成都已經實現從二產過渡到三產,成都在第三產業的發展相較于重慶更成熟。遂寧、南充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齊頭并進,廣安、瀘州第二產業的增長勢頭更好,德陽、樂山、眉山第三產業增長更顯著。這意味著成渝地區產業結構協調性不夠,田莎莎(2018)也提出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定位不清晰,產業同質化問題嚴重。
3. 從消費和投資來看
成渝經濟圈整體消費水平并不高,超過全國平均值(除港澳臺)的城市只有重慶、成都和綿陽。除此之外,從2008年到2018年,成渝經濟圈消費的增長率逐年下降,包括重慶在內的四個城市2018年甚至出現負增長的情況。由此可見,消費的疲軟不僅影響本來水平就不高的城市,還影響到“中心”之一的重慶。另一方面,超過一半的城市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程度降低,包括重慶和成都,以及第二梯隊的德陽和綿陽,但這四座城市對科技的投入力度較大。對于多數成渝經濟圈的城市而言,在發展規劃上,對科技產業的投資并不是重點。
(二)建議
未來一段時間,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有關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兩中心兩地”的發展定位,如何實現會議上提出的“推進科學城建設、共建合作產業示范園區等”目標,根據前文對成渝地區發展現狀分析的結論,可考慮在以下三個方面重點發力。
1. 構建雙城良序競合關系
成都和重慶的現有產業結構同質化較為嚴重。以兩地最有代表性的園區產業布局為例,重慶兩江新區重點發展汽車、電子信息、新材料等產業,而成都天府新區同樣也將汽車、電子信息、新材料等作為主要產業,兩大新區之間的合作交流不夠。重慶和成都這兩個核心城市的產業競爭必將影響了整個四川和重慶的合作。因此需要強化城際間產業鏈分工,整合成渝共有優勢的汽車、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產業資源,推進聯合研發和配套協作。發揮重慶配套產業體系全與成都研發創新能力強的優勢,打破成渝“兩點式”獨立發展模式,架起“成渝大橋”,帶動成渝雙城間資陽、眉山、遂寧、內江的汽車、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產業鏈式發展。
2. 優化城市規模結構,建設主城核心區和次級增長極
重慶市和成都市作為成渝城市群里兩個超大城市,對周邊城市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還明顯不夠。一方面積極推進重慶、成都主城擴容工作,增強雙核驅動發展動能,擴大成渝雙城的輻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培養德陽、綿陽、宜賓、南充等城市成為次級增長極,分擔中心雙城的分職能,發揮其在城鎮體系中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成為區域小范圍支點和過渡點。
3. 加強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共建人才引進培育計劃
充分發揮重慶和成都兩地高校眾多、人力資源富集的優勢,提高科技與創新對高質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解決人才在流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就業創業、社會保險等問題。適度分離經濟區和行政區,加強對兩地人社領域公共政策的比較研究,逐步縮小政策差異。
參考文獻:
[1]田莎莎,季闖.成渝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的路徑研究[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15(04):25-27.
[2]徐翔,陸國斌,王超超.成渝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研究[J].中國科技資源導刊,2019,51(05):21-25.
[3]莫遠明.加強頂層設計 唱好成渝“雙城記”[N].經濟日報,2020-03-16(012).
[4]葉文輝,伍運春.成渝城市群空間集聚效應、溢出效應和協同發展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9(09):88-94.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潼南區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