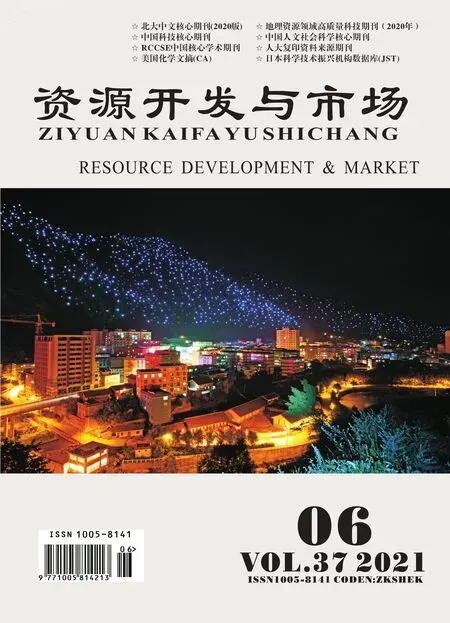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的脫鉤關系及驅動效應分析
——以甘肅省榆中縣為例
程東林,陳 英,謝保鵬
(甘肅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730070)
農村居民點作為農村人地關系的表現核心,是農村人口生產和生活等綜合功能的載體,是農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組成部分[1]。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在“城市拉力”與“農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非農化程度不斷提高,導致各種要素、資源迅速向城鎮集聚,促進了城鎮建設用地的快速膨脹[2]。理論上,農村人口減少,農村居民點用地也應逐漸減少。然而,現實與理論存在著很大的偏差,城鎮建設用地在快速膨脹的同時,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不減反增[3,4]。據統計,1999—2018年我國農村人口共減少了2.56億人,下降了約31.2%,而同期農村居民點用地卻增加了約11.8%。因此,在農村人地關系矛盾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探索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變化的協同關系及其驅動因素,是科學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優化國土空間格局的重要途徑[5,6]。
近年來,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關系的相關研究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馮應斌、周海濤、李佳薇等學者側重研究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時空演變特征,對其影響因素和驅動機制進行了分析[7-9]。同時,學者們也從不同層面對二者之間的耦合關系進行了研究。從全國層面來看,學者們發現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二者之間增減協同演進的良性格局還沒有出現[10],農村人地關系呈現失調發展的態勢[11];受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平原地區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展速度更快[12]。從省域尺度看,王婧、方創琳、李裕瑞發現全國有1/3的省區人口與建設用地極不協調[13]。但綜合分析已有文獻,當前學者們從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或農村人口變化等單維度、單要素研究較多,而聚焦于農村人地耦合關系方面研究較為薄弱,且從國家、省域和市(縣)域等宏觀尺度研究較多,對鎮域等微觀尺度研究不足。鄉鎮處于我國行政體系的基層位置,是人們開展生活和生產的基礎單元,也是人口數據發布的基本單元,較國家、省域和市(縣)域單元反映出較為豐富的空間異質性[14],也比村、社尺度表現出更強的規律性[15]。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農村人地變化關系視角,利用脫鉤模型對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2010—2018年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的脫鉤程度及驅動效應進行了分析,明確農村人地關系的變化特征,揭示發展過程中二者存在的問題,探索推動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路徑,以期為該縣優化農村人地關系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甘肅省榆中縣位于35°34′—36°26′N、103°49′—104°34′E,地處隴西黃土高原,地勢南高北低、中部低洼,呈馬鞍形,地形分為南部石質山地、中部川塬丘陵溝壑、北部黃土丘陵。北部山巒起伏、溝壑縱橫、干旱少雨,包括韋營、中連川、貢井、哈峴、上花岔、園子岔6個鄉鎮,以中藥材和百合種植為主;西南部為高寒陰濕區,海拔1900—3000m,包括馬坡、新營、龍泉3個鄉鎮,以高原夏菜種植為主;中部為川塬河谷區,海拔1400—2000m,包括城關、小康營、高崖、甘草店、清水驛、夏官營、金崖、青城、定遠、連搭、和平11個鄉鎮,是主要產糧區和經濟作物區。2018年,全縣國土總面積32.94萬hm2,其中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為10455.07hm2;全縣總人口45.80萬人,其中農村戶籍人口35.02萬人,農村常住人口32.24萬人。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變化
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及類型判別:目前農村居民點變化主要通過絕對變化、相對變化和年均變化等指標進行表征[16,17]。在同等變化比率和規模下,農村居民點分布在集中區和稀疏區變化顯著不同。綜合考慮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的總量和比率變化的綜合指標,同時具備二者優勢,方能準確表達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的增減趨勢。本文參考喬陸印、劉彥隨與楊忍[18]的研究,采用凈變化率(LNR)表征農村居民點用地總量的變化,反映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的增減趨勢;結構變化率(LSR)表征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比率的變化,反映農村居民點用地增減的緩急程度。

式中,LNRi和LSRi分別為第i個單元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凈變化率、結構變化率;Dn、Dm分別為研究基期和研究末期第i個研究單元的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Tn、Tm分別為研究基期和研究末期第i個研究單元的城鄉建設用地面積總量;m為末期年;n為基期年。
農村人口數量變化及其類型判別:本文參考戚偉、趙美風與劉盛和[19],劉盛和、鄧羽與胡章[20]的研究,綜合凈變化率、結構變化率,將農村人口人口數量變化劃分為4種類型。

式中,PNRi、PSRi分別為第i個單元農村人口數量變化的凈變化率、結構變化率;Dn、Dm分別為研究基期和末期第i個研究單元的農村人口數量;Tn、Tm分別為研究基期和研究末期第i個研究單元的人口總量;m為末期年;n為基期年。
綜上,采用綜合指標法將農村居民點及農村人口變化類型劃分為4種類型,分別為活躍增加型、平穩增加型、平穩減少型、活躍減少型。其標準定義為:活躍增加型LNR(PNR)≥0,且LSR(PSR)≥0;平穩增加型LNR(PNR)≥0,且LSR(PSR)<0;平穩減少型LNR(PNR)<0,且LSR(PSR)≥0;活躍減少型LNR(PNR)<0,且LSR(PSR)<0。
2.2 Tapio脫鉤模型
“脫鉤(Decoupling)”最初來源于物理學領域,就是使具有響應關系的兩個或多個物理量間不存在依賴 關 系[21,22]。我 國 臺 灣 學 者 首 次 明 確 將“Decoupling”理解為“脫鉤”,OECD的專家將阻斷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聯系或者說使兩者的變化速度不同步定義為脫鉤[23,24]。將脫鉤理論應用到土地利用問題中來分析和探討農村居民點與農村人口變化之間的關系,其模型可界定為:

式中,e為脫鉤彈性系數;rL為農村居民點面積增長率;rP為農村人口變化率,Lm、Ln為末期年和基期年農村居民點面積,Pm、Pn為末期年和基期年農村人口數量;m為末期年;n為基期年。
Tapio等學者以脫鉤彈性系數0.8和1.2為依據,將脫鉤模型劃分為擴張連結、衰退連結等8種類型。但在目前農村人口減少的背景下,農村居民點與農村人口變化脫鉤狀態大多處于負脫鉤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單元的脫鉤狀態比較不是很明顯。因此,本文參考劉書暢、葉艷妹與林耀奔[5]的研究,對負脫鉤狀態進一步劃分,結果見表1。

表1 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變化脫鉤狀態
2.3 擴展的Kaya恒等式
農村居民點利用集約度、城鄉人口結構、城鎮化和區域總人口等因素會影響農村居民點變化,因此采用Yoichi Kaya提出的Kaya恒等式來分解影響農村居民點變化的驅動因素[25]。恒等式為:

式中,S為農村居民點總面積;I為農村居民點利用集約度;T為城鄉人口結構;U為城鎮化水平;P為區域總人口;Pr為農村人口,Pu表示城鎮人口。
2.4 LMDI分解法
采用Ang B W[26]提出的LMDI分解法分析研究基期年(n)到末期年(m)農村居民點用地的變化,分解形式為:

式中,△Stot表示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總效應;△SI表示農村居民點利用集約度效應;△ST表示城鄉人口結構效應;△SU表示城鎮化效應;△SP表示區域總人口效應。其中,各驅動因素的計算公式如下:

若各因素效應為正值,表明該因素會促進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的增加,稱之為增量效應;如各因素效應為負值,稱之為減量效應,將起到抑制作用;若效應值為0,則為無顯著影響。
2.5 數據來源
本文涉及數據主要包括農村居民點數據和城鄉人口數據。其中,人口數據主要采用常住人口統計數據,來源于榆中縣2011—2019年統計資料和榆中縣公安局提供的統計數據;農村居民點用地數據則來源于榆中縣2011—2019年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庫。
3 結果及分析
3.1 農村居民點用地與人口變化時空格局分析

圖1 榆中縣農村居民點用地(a)和農村人口(b)變化類型
榆中縣2010—2018年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變化時空格局見圖1a。從圖1a可見,榆中縣農村居民點用地呈現線性增長態勢,由2010年的9544.25hm2增加至2018年的10244.78hm2,9年時間共增加了700.53hm2,凈變化率為7.34%。其中,只有10%的鄉鎮農村居民點面積減少。活躍增加型區域共有8個鎮,占研究單元的40%;平穩增加型區域共有10個鎮,占研究單元的50%;活躍減少型區域有2個鄉鎮,占研究單元的10%。活躍增加型主要分布在榆中東部和南部地區,包括中連川鄉、韋營鄉、龍泉鄉等;平穩增加型主要分布在城關鎮、和平鎮等中部川區和園子岔鄉、貢井鎮等北部山區;活躍減少型主要分布在哈峴鄉和馬坡鄉。同期榆中縣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凈增加值為1809.49hm2,是農村居民點增長面積的2.58倍,說明在城鎮建設用地快速膨脹的同 時,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不減反增。榆中縣2010—2018年農村人口數量變化時空格局見圖1b。從圖1b可見,自2010年以來,榆中縣農村人口數量總體減少,呈現“先增后減”的態勢,在2014年達到峰值。研究期內共減少了3.6萬人,凈變化率為-9.31%;農村人口在全縣總人口中的占比由89.21%下降至76.48%,下降了12.73個百分點。具體來說,2010—2014年農村人口數量呈現緩慢增長的趨勢,由2010年的38.62萬人增加至2014年的39.61萬人,共增加了0.99萬人,年均增長率為0.63%。2014—2018年,榆中縣農村人口數量呈急劇減少的趨勢,由2014年的39.61萬人減少至2018年的35.03萬人,共減少了4.58萬人,年均減少率為3.03%。農村人口數量變化體現了較少的異質性,表現為70%的鄉鎮呈農村人口總量和農村人口占比雙減少的單一模式。由圖1b可知,活躍減少型區域共有14個鄉鎮,占研究單元的70%,其他3種類型區域各占研究單元的10%。其中,活躍減少型主要分布在金崖鎮和夏官營鎮等榆中北部地區;活躍增加型主要分布在馬坡鄉和小康營鄉等榆中南部地區;平穩減少型、和平穩增加型在各個地區交叉分布,沒有形成集中分布區。同時發現,農村居民點面積增加地區大多也是農村人口數量減少地區。榆中縣90%的鄉鎮都存在農村居民點和農村人口呈“人減地增”的截然相反的趨勢,特別是以定遠鎮、青城鎮等經濟較發達地區較為明顯。
3.2 農村居民點用地與人口變化脫鉤關系分析
榆中縣2010—2018年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變化的脫鉤彈性值結果見表2。從表2可見,二者之間的動態關系變化,可以看出擴張負脫鉤、弱脫鉤、擴張連結和強負脫鉤是榆中縣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變化脫鉤關系的主要狀態,呈現出這4種狀態的期數分別為2、1、1、4,分別占統計期數的25%、12.5%、12.5%、50%,其中表現為負脫鉤狀態的狀態期數合計占統計期數的75%。可見,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的脫鉤狀態總體處于負脫鉤狀態,研究期內有4個年期處于強負脫鉤狀態,反映出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之間的人地關系處于最不理想狀態。

表2 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變化的脫鉤狀態
脫鉤彈性值e的變化趨勢呈現出的脫鉤變化狀態為“不協調狀態一相對比較和諧狀態一最不理想狀態”的周期性變化。根據脫鉤彈性值的波動情況,本文將研究期劃分為以下3個階段:2010—2013年、2013—2014年、2014—2018年。
第一階段(2010—2013年)。總體來看,該階段經歷了擴張負脫鉤一弱脫鉤的過程,由不協調狀態向相對比較和諧狀態轉變。2010—2012年,榆中縣居民點用地增長速度超過農村人口增長速度,脫鉤彈性值分別為2.082和4.658,為擴張負脫鉤狀態,農村人地關系整體處于不協調狀態。2012—2013年,榆中縣農村人口增長速度超過居民點用地增長速度,脫鉤彈性值為0.498,為弱脫鉤狀態,農村人地關系處于相對和諧狀態。第二階段(2013—2014年)。該階段經歷了弱脫鉤一擴張連結的過程,榆中縣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速度和農村人口增長速度二者協調增長,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速度較為緩慢。這一階段農村人地關系整體處于相對比較和諧狀態。第三階段(2014—2018年)。該階段經歷了擴張連結一強負脫鉤的過程,農村人地關系由相對比較和諧狀態向最不理想狀態轉變,這一時期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快速擴張,農村人口急劇減少,農村人地關系失衡,農村居民點用地集約利用水平較低。
通過分析榆中縣2010—2018年各鄉鎮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變化的空間差異性發現,研究期內各地區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變化的脫鉤狀態主要有強脫鉤、弱脫鉤、擴張連結、衰退連結、擴張負脫鉤和強負脫鉤6種狀態(圖2),其中80%的鄉鎮農村人地關系脫鉤狀態處于擴張負脫鉤和強負脫鉤;處于強脫鉤、弱脫鉤、擴張連結和衰退連結狀態的鄉鎮各占5%,說明榆中縣農村人地變化的負脫鉤程度較為嚴重,農村人地矛盾日益加劇。

圖2 榆中縣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變化脫鉤類型空間分布
從各鄉鎮情況看,榆中縣中部川區、東北部山區和東南部山區農村人地變化的負脫鉤程度較嚴重。其中,處于強負脫鉤狀態的鄉鎮有15個,占研究單元的75%,同一狀態下,城關鎮、定遠鎮等8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川區鄉鎮負脫鉤程度更加嚴重,其次是青城鎮和龍泉鄉2個經濟次發達鄉鎮,再次是園子岔鄉、上花岔鄉等5個經濟欠發達的北部山區鄉鎮。連搭鎮處于擴張負脫鉤狀態,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均為增加,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速較農村人口增長速度更快,雖然農村人地關系趨于協調,但是未達到合理狀態。清水驛鄉、哈峴鄉和小康營鄉3地農村居民點用地和農村人口處于“同增同減”的協調狀態,增速(減速)相當,但小康營鄉農村人口增長增速較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速快,表現為弱脫鉤,農村人地關系整體處于相對比較和諧狀態。僅有馬坡鄉表現為強脫鉤,這一時期隨著農村人口數量增加,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減少,農村人地關系處于最佳狀態,說明該鄉農村土地集約利用程度最好。
3.3 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驅動效應測度
榆中縣2010—2018年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驅動因素分解結果見表3。從表3分解效應中可以看出,集約度效應和區域總人口效應對農村居民點擴張有促進作用,為增量效應,而城鄉人口結構效應在研究期中有兩期為增量效應,其他時期為減量效應,總體來說對農村居民點擴張有阻礙作用。城鎮化效應有兩期為減量效應,其他均為增量效應。

表3 榆中縣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驅動因素分解結果
從分解的效應值的絕對值來看,城鄉人口結構效應是榆中縣農村居民點變化最主要的驅動力因素。2010—2018年,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的比值由8.26下降至3.25,主要是農村人口由38.25萬人下降至35.03萬人,下降了9.19%,而同期城鎮人口增加了130.62%,城鎮人口規模迅速擴張。這說明在人口轉型過程中,農村人口數量的下降對農村居民點的減少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城鎮化效應是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現在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兩方面,二者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27]。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過程中,城鎮建設用地資源日漸緊缺,必然會向外拓展,導致周圍農村居民點用地轉化為城鎮建設用地,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另外,對于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的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原有居民點用地規模不斷擴大,進而發展成小城鎮,農村人口也變成城鎮人口,人口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土地城鎮化進程。榆中縣城鎮化率由2010年的10.79%上升至2018年的23.52%,城鎮化效應值總體表現為正值,說明它對農村居民點變化有促進作用。
農村居民點集聚效應是農村居民點規模擴大的主要驅動力之一。農村居民點建設自然演變過程中,無序的外延式擴張和雜亂分散的布局會導致農村居民點規模的擴大和土地資源浪費,不利于耕地保護,也增加了村莊內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成本,不利于居住社區的形成。榆中縣人均農村居民點面積由2010年的252.16m2增加至2018年的298.46m2,可見該縣農村土地集約利用水平低下、浪費嚴重,呈粗放型發展,致使農村居民點規模不斷擴大。
區域總人口效應也會促進農村居民點擴張,但影響相對較小。區域總人口效應促進農村居民點面積的擴張主要體現在農戶基本的住房需求上。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農戶非農化,非農經濟收入快速增加,農戶對住房環境需求逐漸強烈,促使農民新建住房,增加居民點用地面積[28]。2019年,榆中縣閑置宅基地戶數達到2975戶,說明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農村宅基地并沒有有效退出,存在大量的閑置宅基地。總體上,區域總人口效應對促進農村居民點擴張的貢獻度相對較小。
本文通過對驅動效應分解的區域差異分析結果(表4)可以看出,2010—2018年各鄉鎮的農村居民點變化總量效應中,全縣20個鄉鎮中只有哈峴鄉和馬坡鄉2個鄉鎮農村居民點總面積出現減少,其他均為增加,說明這一時期榆中縣各鄉鎮總體對農村居民點規模的管控力度較差。
從農村居民點的變動幅度來看,2010—2018年榆中縣除哈峴鄉和馬坡鄉兩地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下降外,其他地區均表現為用地規模的增加,研究期平均增幅為6.6%。這一時期農村居民點不斷擴大,各地區農村居民點變化存在明顯差異。
城鄉人口結構效應總體表現為減量效應,對各鄉鎮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擴張具有抑制作用。從分解效應的絕對值來看,是農村居民點變化的最主要驅動力因素。定遠鎮城鄉人口結構比值在榆中縣的地區變化最大,是農村居民點規模減少的主效應,而上花岔鄉、韋營鄉等4鄉鎮城鄉人口結構效應對該地區農村居民點規模的擴張起到了促進作用。集約度效應總體表現為增量效應,對各鄉鎮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擴張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其中定遠鎮、城關鎮、和平鎮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鄉鎮對榆中縣農村居民點集約度總效應中的貢獻度較大,說明該地區農村居民點集約利用水平較差。同期哈峴鄉、馬坡鄉集約度效應表現為減量效應,說明該地區農村居民點集約利用水平較高。城鎮化效應在各鄉鎮表現各異,總體表現為增量效應,其中連搭鎮、定遠鎮等鄉鎮城鎮化效應值較高,而龍泉鄉和清水驛鄉等地城鎮化效應相對其他鄉鎮較弱,說明城鎮化效應對縣城周邊地區的影響程度較為顯著。區域總人口效應負值集中表現在榆中縣北山幾個鄉鎮,說明北山地區農村總人口的減少對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的擴張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4 榆中縣各鄉鎮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驅動效應分解結果
4 結論與討論
主要結論:①榆中縣2010—2018年農村人口總量減少,而農村居民點面積逐年遞增,全縣90%的鄉鎮農村居民點和農村人口均呈現“人減地增”的逆協同局面,在區位條件、地理位置優越的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②研究期內,農村居民點與農村人口變化的脫鉤關系主要呈現出擴張負脫鉤、弱脫鉤、擴張連結和強負脫鉤4種狀態。從時序性變化看,有75%年份表現為負脫鉤狀態;從空間差異性看,80%的鄉鎮農村人地關系脫鉤狀態處于擴張負脫鉤和強負脫鉤狀態。可見,榆中縣農村人地變化的負脫鉤程度較為嚴重,農村人地關系失衡,人地關系處于不理想狀態。③農村居民點變化驅動效應測度中,城鄉人口結構效應對農村居民點擴張的貢獻度最大,集約度效應和城鎮化效應次之,區域總人口效應對農村居民點擴張有抑制作用。從空間差異性看,區位條件較好的地區農村居民點擴張主要驅動因素為城鎮化效應和集約度效應,為增量效應;城鄉人口結構效應和區域總人口效應在區位條件較差地區顯著,為減量效應。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優越程度與地區人地關系變化密切相關。研究發現,地理位置優越的鄉鎮農村居民點用地與農村人口關系負脫鉤程度更為嚴重,農村人地關系更為不協調,這與劉燕、楊慶媛與何星[15]的研究結果一致。農村人口與農村居民點用地出現逆協同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城鎮化和工業化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城市二、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催生了城市經濟對農村勞動力的旺盛需求,促使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另一方面,農民務工收入較之務農收入具有絕對性優勢,城鄉收入的巨大差距誘導著以勞動力為主的農業資源轉向城鎮非農部門[29]。然而,家庭收入的增加使農民有了新建和擴大宅基地的經濟基礎[30],同時家庭結構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變遷的基礎上,使得建房需求旺盛,但村莊規劃不合理、政策引導不到位都會導致農村居民點用地“不減反增”[31,32]。因 此,建議對不同類型、不同區域、不同經濟條件下的農村閑置宅基地因勢利導、分區制宜,盤活現有土地資源,遏制農村“人走房空”、村莊“外擴內空”等不良現象,促使農村土地人地關系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