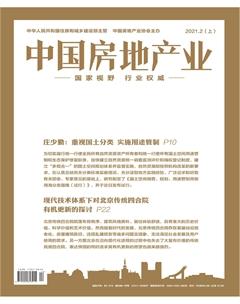《民法典》居住權(quán)立法的制度檢視
【摘要】居住權(quán)入典有很強(qiáng)的制度價(jià)值。既有利于黨和中央有關(guān)住房政策的落地,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在住房問題上的具體體現(xiàn)。但面對實(shí)踐中弱勢群體的幫扶保障以及市場流通性的需求,《民法典》仍然存在規(guī)范配置不足的問題,可以通過設(shè)定法定居住權(quán)、適當(dāng)突破不可轉(zhuǎn)讓性的牽制以及對居住權(quán)人的義務(wù)規(guī)定來調(diào)和理論與實(shí)踐需求的矛盾,彌補(bǔ)相關(guān)制度的缺位。
【關(guān)鍵詞】居住權(quán);人役權(quán);法定居住權(quán)
1、居住權(quán)的立法流變
居住權(quán)肇端于羅馬法,以人役權(quán)的面貌現(xiàn)世。其最初設(shè)立目的旨在通過為缺乏勞動(dòng)能力的非所有者設(shè)立居住他人房屋的權(quán)利,以此解決其基本的生存問題,不至于生無所居、老無所依。而后,其理念與制度幾乎全盤移植于歐洲,同時(shí)在此基礎(chǔ)上,歐洲各國做了進(jìn)一步擴(kuò)充。如《法國民法典》將契約作為居住權(quán)的普遍設(shè)立方式;《意大利民法典》對費(fèi)用的承擔(dān)進(jìn)行規(guī)定;其中最具創(chuàng)造意義的當(dāng)屬《德國民法典》,為順應(yīng)社會的發(fā)展,在上述傳統(tǒng)居住權(quán)的范圍之外,衍生出“長期居住權(quán)”。長期居住權(quán),將其作為土地的負(fù)擔(dān)規(guī)定為一種特殊的限制物權(quán),是對公寓化住宅中的住房享有的以居住為目的的一種使用權(quán)。[1]它具有可轉(zhuǎn)讓和可繼承的特點(diǎn),更加疏通了利用的渠道。至此,德國形成了單純調(diào)整婚姻家庭內(nèi)部關(guān)系的“社會性”居住權(quán)加之更為靈活的、可產(chǎn)生收益的“投資性”居住權(quán)的初始分類。在西學(xué)東漸過程中,東亞各國(除我國澳門地區(qū))未能延續(xù)對居住權(quán)此類的人役權(quán)的繼受,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出自于東西方習(xí)慣不同,自古以來養(yǎng)老撫幼的傳統(tǒng)也導(dǎo)致難在住房問題上發(fā)生爭執(zhí)[2]。但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仍舊篤定的認(rèn)為在東亞國家不存在居住權(quán)生發(fā)的條件是不合適的,還是要依據(jù)各地的物質(zhì)生存條件做出相應(yīng)的判斷。
2、居住權(quán)的制度價(jià)值分析
居住權(quán)系我國自歐洲引入的全新的用益物權(quán),我國歷史上未曾有相關(guān)規(guī)定。如前述所言,即使民國時(shí)期在學(xué)習(xí)西方《德國民法典》的過程中,居住權(quán)亦未進(jìn)入當(dāng)時(shí)《民法》的視野[3]。引入的這一新概念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價(jià)值。
(1)有助于“房住不炒”的制度落地。如何去貫徹黨十九大報(bào)告提出的“房住不炒”的戰(zhàn)略安排,實(shí)現(xiàn)“住有所居”的美好愿景,居住權(quán)提供了一個(gè)新思路。首先,在調(diào)控房地產(chǎn)價(jià)格以及構(gòu)建保障性住房雙重安排下,解決了一部分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但僅僅通過住房數(shù)量的增新不足以實(shí)現(xiàn)保障的全覆蓋,此時(shí)居住權(quán)在不另增住宅用地的情況下發(fā)掘了房屋的存量,更為物盡其用,為現(xiàn)行制度提供有力補(bǔ)充。其次,居住權(quán)作為用益物權(quán),在遭受第三人侵害時(shí)可以提供物權(quán)法上的救濟(jì)手段要求第三人排除妨害,對于住房保障體系的構(gòu)建有所補(bǔ)充。
(2)有利于促進(jìn)社會和諧。最初最高法在司法解釋中規(guī)定,夫妻離婚時(shí),可為困難一方設(shè)立房屋居住權(quán)解決其住房問題,但因其僅有債法上的約束力卻不能提供物權(quán)法上的救濟(jì),因此一直未能如愿產(chǎn)生效果。當(dāng)居住權(quán)入典后,從法律層面確立其物權(quán)效力,釋放制度紅利,回應(yīng)民生熱點(diǎn),為弱勢的離婚女性群體提供制度救濟(jì)。此外,居住權(quán)還可以兼顧各方利益。既可通過為與其存在特定關(guān)系之人賦予其居住權(quán),來保障自己受撫養(yǎng)的權(quán)利;也可以通過將所有權(quán)和居住權(quán)做切分的方式幫助親友,促進(jìn)社會和諧。
(3)適應(yīng)財(cái)產(chǎn)處理方式多元化的現(xiàn)實(shí)需求。制度并非會一直停滯不前,隨著社會發(fā)展,居住權(quán)的內(nèi)涵會進(jìn)一步擴(kuò)大是肯定的。暫不論居住權(quán)的傳統(tǒng)人役權(quán)屬性,居住權(quán)為當(dāng)事人提供更多的選擇權(quán),通過居住權(quán)制度對權(quán)利的調(diào)整,可以充分滿足房屋所有人、居住權(quán)人和其他第三人之間的利益需求,多樣化房屋標(biāo)的的利用方式以實(shí)現(xiàn)其效益價(jià)值[4]。回顧我國《民法典》,立法也是建立在承認(rèn)以居住權(quán)合同方式為意定方式設(shè)立的居住權(quán)基礎(chǔ)之上,充分尊重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尊重其對財(cái)產(chǎn)處理的自決意識。
3、居住權(quán)的問題梳理
民法典用寥寥數(shù)條對居住權(quán)做了大致性的規(guī)定,但仍有一些問題未能明確,對于未盡事宜如何進(jìn)行補(bǔ)充,使其更好地服務(wù)于民眾的需求,且未雨綢繆為未來經(jīng)濟(jì)發(fā)展留足增補(bǔ)空間也是需要設(shè)想的問題。
(1)未設(shè)定法定居住權(quán)。通過對《民法典》條文的梳理不難發(fā)現(xiàn),民法典366條至371條對居住權(quán)的設(shè)立是建立在意定的基礎(chǔ)之上,具體體現(xiàn)為合同和遺囑兩個(gè)形式,同時(shí)采取更偏向于傳統(tǒng)人役權(quán)的保障形式,即增設(shè)滿足“生活居住需要”的前提。人役權(quán)最初因幫扶弱者目的而設(shè),但是僅僅依靠合同和遺囑不足以實(shí)現(xiàn)周全的保護(hù)。我國現(xiàn)行法采取的是登記生效主義,若未有法定居住權(quán)進(jìn)行兜底性的保護(hù),未登記的居住權(quán)有可能因房屋被第三人善意取得而消滅。此時(shí)可能會與立法目的背道而馳,無法發(fā)揮其社會扶助職能。
(2)不可轉(zhuǎn)讓屬性限制居住權(quán)功能發(fā)揮。法律是一定社會和文化條件下的產(chǎn)物,雖然社會性居住權(quán)有其合理性,但過分強(qiáng)調(diào)傳統(tǒng)人役權(quán)的屬性不利于財(cái)富的流通。前述已明,德國在傳統(tǒng)人役權(quán)之外,為應(yīng)對市場活性的需要增設(shè)了“長期居住權(quán)”,賦予其轉(zhuǎn)讓的權(quán)能。而反觀我國《民法典》明確規(guī)定了居住權(quán)的不可轉(zhuǎn)讓性。其意不代表外國民法的一切都需要不加辨別的繼承,而是通過對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狀況的審視與我國作對比性分析。建立統(tǒng)一的居住權(quán)市場之前,應(yīng)當(dāng)對意定居住權(quán)的財(cái)產(chǎn)屬性有一定的認(rèn)識,一刀切的禁止轉(zhuǎn)讓對于物盡其用的價(jià)值有所減損。現(xiàn)代居住權(quán)制度如何融入社會快速發(fā)展的需求之中,筆者認(rèn)為有必要在尊重意定的基礎(chǔ)之上,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和完善。
(3)未對居住權(quán)人的義務(wù)予以明確。我國《民法典》對居住權(quán)的規(guī)范配置稍顯不足。盡管考慮到法典的體系化及法律不言廢語的精神,可以不將法律規(guī)定拓展過多導(dǎo)致冗長,只需對居住權(quán)區(qū)別于其他人役權(quán)的特殊內(nèi)容做出規(guī)定,其他方面準(zhǔn)用用益權(quán)的規(guī)則即可[5],但是在法典中也未能對準(zhǔn)用性規(guī)則予以釋明。對于存在空缺結(jié)構(gòu)的法律,需要運(yùn)用法律漏洞填補(bǔ)規(guī)則;對于不確定的概念,則要進(jìn)行價(jià)值補(bǔ)充;雖不足以如數(shù)學(xué)證明般精確,但也有補(bǔ)于世。在此處則需要運(yùn)用類推適用的手段,來回穿梭于法律規(guī)定之間,找尋符合《民法典》467條規(guī)定的準(zhǔn)用性參考的規(guī)范,即與居住權(quán)制度構(gòu)造最為相似的租賃合同來有所取舍的適用于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
4、居住權(quán)的制度完善
(1)增補(bǔ)設(shè)定法定居住權(quán)。此處的法定居住權(quán)僅指在雙方當(dāng)事人無合意的情況下,通過法院裁判為一方設(shè)立為困難一方提供居住的義務(wù),且不能被合同和遺囑隨意剝奪。婚姻法解釋中為困難一方設(shè)立的居住權(quán)當(dāng)屬此類。除此之外,例如父母用盡全部積蓄為子女購買房屋,此時(shí)父母的權(quán)利如何保障?又如在多子女家庭中如何體現(xiàn)對非不動(dòng)產(chǎn)繼承人的照顧,居住權(quán)為住房問題劣勢一方的保障打開了新思路。不能簡單認(rèn)為以國家強(qiáng)制力為后盾的法定居住權(quán)與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則之間存在不可彌合的罅隙。實(shí)際上實(shí)踐案例中當(dāng)事人對居住權(quán)的約定并非沒有蘊(yùn)含法定居住權(quán)的內(nèi)容,但受限于我國沒有相關(guān)立法,唯有通過約定滿足其住房需要。在結(jié)合實(shí)踐需求以及在進(jìn)行公平價(jià)值與自由價(jià)值的衡量之后,筆者認(rèn)為有設(shè)立法定居住權(quán)的必要。當(dāng)然,在設(shè)立時(shí)也要明確法定居住權(quán)適用的對象、適用情形,對規(guī)定進(jìn)行嚴(yán)格限制。既為幫扶群體提供法律救濟(jì),落實(shí)住有所居的政策,體現(xiàn)人文主義的關(guān)懷,同時(shí)也在限定范圍的情況下,尊重私法自治,實(shí)現(xiàn)公平與自由價(jià)值的平衡,實(shí)現(xiàn)完滿保護(hù)多價(jià)值的愿景。
(2)適當(dāng)突破傳統(tǒng)人役權(quán)掣肘。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迅速,民眾有關(guān)財(cái)產(chǎn)處理要求也愈發(fā)多元。在有法定居住權(quán)對弱勢群體承擔(dān)生存保障功能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適當(dāng)突破傳統(tǒng)人役權(quán)的牽制。需要明確的是,兩者并非完全對立,而恰恰可以通過賦予其轉(zhuǎn)讓權(quán)能,實(shí)現(xiàn)居住權(quán)的交換價(jià)值利用最大化,抵消其固化的負(fù)面效應(yīng),促進(jìn)經(jīng)濟(jì)活力。尊重居住權(quán)的不同屬性、不同需求,可以反哺成為新型社會保障的新渠道。
(3)在尊重約定優(yōu)先的情況下,明確居住權(quán)人的義務(wù)。在居住權(quán)人的義務(wù)方面,一是要承擔(dān)合理修繕的義務(wù)。《民法典》規(guī)定雙方可以約定“居住的條件和要求”,這便暗含了居住權(quán)人負(fù)擔(dān)法定的合理用益義務(wù),在居住權(quán)生效后,應(yīng)當(dāng)盡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wù),應(yīng)遵從不超出假想范圍、不變更房屋性質(zhì)、不毀損屋內(nèi)財(cái)物等原則來合理使用所有物。二是對于屋內(nèi)用品的自然損耗,其維修費(fèi)用也應(yīng)當(dāng)由居住權(quán)人自行負(fù)擔(dān)。在這一點(diǎn)上不能完全照搬租賃合同由出租人承擔(dān)的規(guī)定,其正當(dāng)性在于租賃權(quán)并非如物權(quán)般穩(wěn)定,一概由承租人承擔(dān)是不合理的。而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重大維修,若不僅不會使住房受損且能延長房屋使用年限使所有權(quán)人獲益的情況下,所有權(quán)人作為最大的受益者,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相應(yīng)費(fèi)用。三是返還的義務(wù),在期限屆滿或其他導(dǎo)致居住權(quán)滅失的情形下,居住權(quán)人應(yīng)當(dāng)向所有人返還房屋。期限屆至,由有權(quán)占有轉(zhuǎn)變?yōu)闊o權(quán)占有,所有權(quán)人可行使物權(quán)請求權(quán)要求居住權(quán)人返還。
參考文獻(xiàn):
[1]申衛(wèi)星.視野拓展與功能轉(zhuǎn)換:我國設(shè)立居住權(quán)必要性的多重視角[J].中國法學(xué),2005(05):77-92.
[2]王澤鑒.用益物權(quán)·占有[M].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北京,2001:73
[3]梅仲協(xié).民法要義[M].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北京,1998:3.
[4]錢明星.關(guān)于在我國物權(quán)法中設(shè)置居住權(quán)的幾個(gè)問題[J].中國法學(xué),2001(05):13-22.
[5]汪洋.民法典意定居住權(quán)與居住權(quán)合同解釋論[J/OL].比較法研究:1-21[2020-11-20].
作者簡介:
張一珺(1996-),女,漢族,湖南益陽市人,法學(xué)碩士 單位:南京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法學(xué)院憲法學(xué)與行政法學(xué)專業(yè),研究方向: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