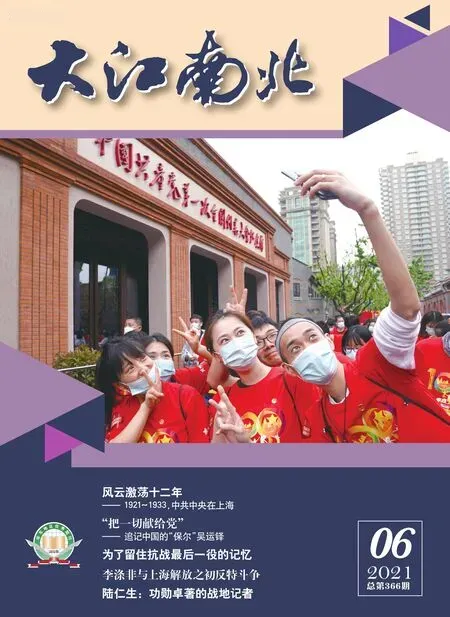最完整的《共產黨宣言》首譯本何以被珍藏
□ 趙 暢
1991年“七一”前夕,我尚在浙江省上虞縣教委工作,聽聞時任上虞縣黨史辦公室主任、全國優秀黨史工作者,亦是我的岳父邵水榮說起,上虞縣豐惠中學副校長夏云奇準備向縣檔案館捐贈他父親夏禪臣珍藏多年的《共產黨宣言》首譯本。
聽聞消息,我在岳父的引領下,迫不及待地趕赴縣檔案館一睹為快。懷著一份莊嚴崇敬的心情,我戴起專用手套,小心翼翼地翻閱這本珍貴的書籍。

▲在上虞檔案館珍藏的《共產黨宣言》首譯本封面

《共產黨宣言》首譯本內頁
這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長18厘米,寬12厘米,平裝,小32開,僅僅56頁。封面為紅色、繁體字,封面上方有4行字,從上到下依次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大寫的“共產黨宣言”(初版誤印為“共黨產宣言”)、“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封面正中,是一幅水紅色的馬克思半身像。封底自左至右依次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原著者馬格斯·安格爾斯”、“翻譯者陳望道”、“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所”。
1992年,上虞縣黨史辦公室與縣檔案館專門攜《共產黨宣言》首譯本赴上海,請上海市檔案館和中共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專家鑒定。專家認為:“上虞這本《共產黨宣言》與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版完全一樣。”那時,獲悉我國有關部門曾搜集到七冊首譯本,但上虞的這一冊最為完整。因為其他六冊或是再版本、第三版本,或是無封面、殘損本,只有上虞的這一冊不僅沒有破損、沒有污漬,而且紙張完好。
想當年,《共產黨宣言》首譯本在國內問世后,馬克思主義便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毛澤東主席生前曾多次談到,1920年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閱讀過陳望道的最早譯本《共產黨宣言》,這本書對他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給予了極大的啟示,并堅定了他投身革命的信念。新中國成立后,有關部門也一直在尋找最早的譯本。1975年,全國四屆人大會議期間,周總理見到時任上海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先生時,問道:“《共產黨宣言》最早的譯本找到了沒有?”陳望道搖搖頭。周總理遺憾地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這是馬列老祖宗在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找不到它,那可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病啊!”想不到,而今竟在上虞發現,且保存如此完好,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若周總理有知,不也了卻他老人家的一塊心病嗎?
不能不說的是,首譯本在封面右下角印有一枚淡紅色篆體章——“華林之印”。華林是浙江富陽人,早年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時,與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王一飛、葉天底等為同窗。其中王一飛和葉天底均是上虞人。因此,這冊原本屬華林的書傳到上虞籍的同學手里,也是合乎邏輯的。
只是,這冊書究竟是通過王一飛還是葉天底傳到夏禪臣手里的,似乎存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據夏禪臣妻子推測,王一飛與夏禪臣為同鄉,均就讀師范學校,且因兩家家庭貧困,所以兩人思想傾向相近,以后夏禪臣還在經濟上資助過王一飛,王一飛對夏禪臣心存感激。王一飛赴蘇學習,常與夏禪臣有書信往來。因此,首譯本很可能是王一飛贈送給夏禪臣的。而我的岳父邵水榮卻另有說法,他曾經告訴我:1962年,采訪葉天底革命活動情況時找過夏禪臣,夏與葉都是浙江一師的同學,年齡相仿,走得又很近。上世紀二十年代國共合作時,葉天底回上虞組建國民黨區分部,葉是書記,夏是執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葉在上虞被捕,夏遠走他鄉,躲過一劫。這本當年由上海外國語學社發行,并作為學員教材或宣傳資料的小冊子,由華林傳到葉天底手里,后由葉帶回上虞,作為共產主義理論的教材送給夏閱讀。后幾經戰亂,早期共產黨人均已犧牲,這冊書就留在夏手里了。
對于我岳父的說法,夏云奇也覺得有點道理。盡管存有上述兩種不同說法,但有一點讓人深信無疑:《共產黨宣言》首譯本,作為早期革命先驅的遺物,最后由夏禪臣珍藏至1963年4月,后交給兒子夏云奇保管。
夏云奇告訴我,父親去世后,他才鄭重其事地打開了父親的書箱,并第一次看到了首譯本。母親的回憶,父親生前曾經的敘說,以及自己的親身經歷,令夏云奇想起了首譯本珍藏的艱難歲月和傳奇故事……
“四·一二”政變后,王、葉兩位先烈相繼慘遭殺害。其時,不必說革命活動被迫轉入地下,一些宣傳革命真理的書籍也均被燒毀,保存革命書籍會遭滅頂之災。“在這種形勢下,這冊共產主義的宣言書,是繼續保存還是立即燒毀,關系到全家的生命安全。面對烈士的鮮血、音容笑貌,以及成千上萬的為著理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先烈,我父親勇敢地選擇了保存。就這樣,這一本小冊子就靜靜地躺在木質的書箱里。”說到父親當年的毅然之決,夏云奇不禁流露出敬佩和自豪之情。
說及保存首譯本,走過的自是一條充滿險情的路途。據夏云奇介紹,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日本侵華,上虞相繼淪陷,日本占領上虞豐惠后,無惡不作,如發現有抗日和“赤化”的資料,就可能燒殺整個村子。為此,全家南遷到虞南山區。八年抗戰,這本小冊子在虞南山區輾轉數年,也歷經日寇數次進虞南山區“掃蕩”,并遭日寇飛機轟炸之險,但不管碰逢怎樣的困境,夏禪臣帶著全家東躲西藏時,始終沒有丟下過那只藏有小冊子的木箱。盼到豐惠解放,全家才得以回老家。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早已投敵的田岫山匪部將豐惠作為其盤踞地,且極盡燒掠之能事。有一天,夏禪臣家的堂屋被點燒,瞬間大火熊熊燃起。幸好一個點火的士兵碰到一個熟識的鄰居,良心發現,才提議將火熄滅,令木箱又躲過一劫。見豐惠戰火不斷,夏禪臣全家又被迫逃難到外地親戚家。自然,木箱也一同帶往。
……
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學》上看到作家李存葆、王光明寫的報告文學《大王魂》,講述了山東省廣饒縣大王村群眾在殘酷的戰爭年代,怎樣用鮮血和生命保護了一本1920年8月由陳望道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的動人故事,這給夏云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著這樣一本《共產黨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組織上捐贈這本珍貴文獻的念頭。在與母親錢詠萍商量后,決定捐獻。
1991年建黨70周年前夕,夏云奇與90歲的母親寫下了一份捐贈報告:“……幾十年來,經歷了戰爭和白色恐怖,唯有這冊《共產黨宣言》伴隨著主人的足跡,輾轉南北,雖屢遭不測但均化險為夷、安然無恙。如今,共產主義事業經歷七十年的風風雨雨,在中國古老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累累,將《共產黨宣言》獻給黨、獻給國家,以慰烈士在天之靈……”文末,任化學老師的夏云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此書限于當時歷史條件,紙頁含酸過多。根據山東廣饒的經驗,應送中央檔案館作去酸處理,以便長期保存而不致老化變質。”
1991年6月,這本《共產黨宣言》首譯本終于進入上虞縣檔案館珍藏,堪稱“鎮館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