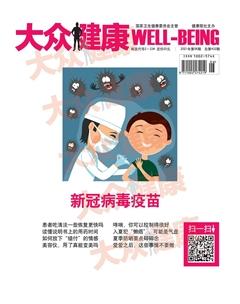終結新冠流行,還有哪些關卡
蘇靜靜
控制和根除疾病是人類自古就有的愿望,而從愿望變為可實現的目標,有賴于醫學技術的發展。疫苗接種被認為是醫學科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被認為是回報率最高的公共衛生投入,不論是對于個人還是人群來說。美國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在《科學》雜志上撰文稱,“面對世界大流行,開發有效的疫苗始終是最為緊急的優先事項”,這似乎代表了醫學界普遍的共識。
二戰后,針對多種傳染病的疫苗和抗生素陸續問世,曾經給人們帶來無盡的樂觀。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全球徹底消滅天花,這是人類迄今為止唯一通過疫苗接種消滅的疾病。那么,新冠病毒疫苗會是這次疫情的答案嗎?
可以說,疫苗是新冠疫情的答案,不過目前這個答案還很不完整。正如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的,全球免疫行動的成功,必須有賴于實現和保持高的疫苗接種率。而要實現高水平的疫苗接種率,還有若干問題有待克服。
疫苗猶豫
如果我們回頭來看天花根除的歷史,可以發現,牛痘疫苗作為人類阻斷天花傳播的有效方法,早在18世紀中期便已誕生,但人類徹底消滅天花的歷程足有200多年。

實際上,疫苗發明的歷史一直伴隨著一部“反疫苗”的歷史,其中有科學的理性,但也裹挾著政治、商業、國家安全、文化和宗教等各種力量的角逐。世界衛生組織免疫策略咨詢專家工作組將疫苗猶豫定義為:一種受到多種因素影響接種疫苗的行為,即從完全接受者到完全拒絕者之間的連續范圍的一組人群。
疫苗猶豫是一個在特定背景下的復雜問題,根據時間、地點和疫苗的不同而變化。其影響因素包括誤導信息(接受反接種疫苗組織的宣傳或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的相關言論),缺乏信心(不相信疫苗或對醫務人員和衛生保健系統等不信任),自滿情緒(認為不需要疫苗,不重視疫苗),便利程度(接種疫苗路途較遠),費用較高,以及對疫苗安全性的質疑等。當今自媒體時代,有關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的真假消息飛速傳播,加劇了人們對接種疫苗的猶豫。
接種政策
通過疫苗這種技術手段控制疫情,并不是一直順利的。世界各國的疫苗接種政策差異很大,有的國家很早就出臺了強制性的疫苗接種政策,而有的國家則很晚,比如法國在1902年前,一直沒有強制性的疫苗接種政策。1840年,英國的疫苗接種法案就規定,給窮人免費接種疫苗。然而,當一些國家通過強制性疫苗接種法律并開始執行時,疫苗接種工作卻常常會遭遇抵制。
英國在1853年通過強制性疫苗接種立法,并在1867年和1871年嚴格執行。由于天花疫情的暴發,政府借助罰款和監禁等懲罰手段強推疫苗接種工作,但強制措施反而引發了激烈抵制。19世紀80年代,英國大約出現了200個反疫苗接種組織。最后,國家取消強制接種的做法,1898年通過了新的疫苗接種法案,表面上規定疫苗接種仍是強制性的,但事實上卻對出于道義的抵制行為網開一面,從而使得嬰兒的接種率大幅下降。
美國社會對強制接種的抵制比英國還要強烈,盡管各州的情況迥異,但其總體接種率低于大部分通過強制性立法的歐洲國家。在美國的農村地區,接種率常常不足10%。因此,美國的天花發病率相當高。直到20世紀80年代,疫苗接種才在美國成為慣例。
世界衛生組織在剩余的少數國家進行根除天花的運動,當時受到推薦的標準做法,是在某種形式的強制性立法支持下,開展大規模的免疫接種目標,設定在三五年內覆蓋這幾個國家至少80%的人口。1964年,世衛組織天花根除專家委員會設立了更高的接種率建議,要求百分之百覆蓋這一地區人口。這個推薦數據建立在印度經驗上。由于印度人口稠密天花發病率很高,80%的疫苗接種率被認為并不足以阻斷天花疫苗病毒傳播。
疫苗的安全危機
1882年,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確定了結核病的致病菌——結核桿菌。20世紀20年代初,因法國科學家阿爾伯特·卡邁特和卡米爾·介蘭發明了結核疫苗,故該疫苗被稱為卡介苗(BCG)。這是目前唯一以發明者姓氏命名的疫苗。他們于1921年開始進行人體試驗,經累積案例與統計,接種疫苗的肺結核病患死亡率約為2%。這一系列試驗被視為卡介苗有效的有力證據,接下來他們為巴黎查理特醫院的一名嬰兒接種了該疫苗。孩子的母親在分娩后死于結核病,孩子口服卡介苗后沒有得病。之后,隨著越來越多的孩子接種疫苗,卡介苗的接受度也日益增加,特別是在法國和北歐國家。
1928年,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推薦卡介苗普遍應用于新生兒,但一場悲劇差點斷送了卡介苗的前程。德國呂貝克衛生部門于1930年2月24日開始實施嬰兒接種,共有256名新生兒接受了口服卡介苗,結果造成76名嬰兒死亡,131名嬰兒發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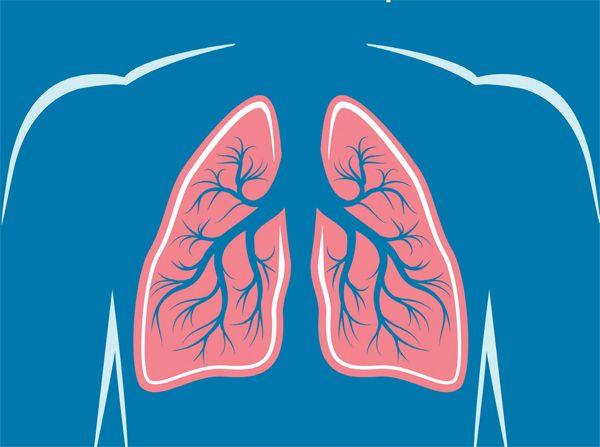
后來的調查證實,是因為疫苗在生產過程中意外污染了結核桿菌的有毒菌株,致病和致死并非卡介苗本身的問題。但出于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擔憂,德國中止了卡介苗接種。這一悲劇的發生,推遲了卡介苗在英國和美國的推廣。二戰期間,結核病在歐洲和亞洲死灰復燃,卡介苗才得以大規模使用。
全球的不公平
目前,全球多個國家已經開始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工作,但在這項全球疫苗接種運動中,存在嚴重的疫苗分配不均的情況。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警告稱,這種不平等的疫苗政策,使得世界正面臨著災難性的道德失敗,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需要為這種失敗付出生命和生計的代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指出,當前免疫工作“嚴重不平等且不公正”。在所有已完成的疫苗接種中,75%的疫苗接種集中在10個國家,“受到沖突和不安全因素影響的群體尤其面臨掉隊的風險”。他毫不諱言:“疫苗公平是人類社會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道德考驗。”
根據英國醫學雜志(BMJ)的一篇文章提供的數據,目前富裕國家已經從全球領先的13家疫苗生產商那里,獲得了至少一半的新冠病毒疫苗。中低收入國家只能使用剩余的小部分。盡管這些國家擁有世界上85%以上的人口,但他們卻只擁有著全球不到一半的新冠病毒疫苗。該文章預測,即使這13家疫苗生產商以最大產能生產,到2022年,世界上至少還有1/5的人口無法接種疫苗。

新冠病毒疫苗分配不公,凸顯了日趨嚴重的全球性不平等現象,一幅不平等的圖畫也展現在世人面前,很多貧困國家的兒童并沒有疫苗接種。最新開發出的兩種兒童疫苗是針對“被遺忘的殺手”肺炎球菌病(肺炎鏈球菌可導致肺炎、腦膜炎和其他感染)和輪狀病毒。然而,在衛生條件較差的低收入國家,5歲以下兒童死于肺炎球菌病和輪狀病毒感染的風險遠高于高收入國家。由于這些國家的衛生服務基礎設施匱乏甚至缺失,這些疫苗恰恰是無法負擔和不可及的。
“非洲腦膜炎帶”便是令人心痛的證據,盡管純化的、對熱穩定的凍干流腦疫苗早已問世,流行性腦膜炎依然在從西部塞內加爾到東部埃塞俄比亞的非洲地區周期性肆虐,病死率高達10%~50%。
疫苗生產能力
疫苗的生產過程復雜,涉及上下游產業鏈,主體眾多,即便美國公開疫苗專利,相關國家短期內也很難獲得疫苗生產能力。新冠病毒疫苗的產業鏈,涉及多個領域,具有覆蓋廣、流程多、業務大等特點。
新冠病毒疫苗產業鏈的上游為疫苗的包裝和原材料,主要涉及藥用玻璃瓶、預灌封注射器、瓶蓋、藥用輔料等。中游為疫苗研發生產,主要涉及相關疫苗研發和生產企業。下游為疫苗的終端使用和疫苗的處理,主要涉及注射器及醫療廢物的處理等。此外,新冠病毒疫苗的流通貫穿產業鏈的全過程,主要涉及冷鏈設備、冷鏈運輸、冷鏈流通和冷鏈物流等。新冠病毒疫苗的原材料供需缺口也嚴重不平衡。
全球范圍內新冠病毒疫苗的需求量將超過100億劑,這需要約20萬次托盤裝運、約1500萬次冷藏箱運送以及約15000架次航班運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療運營管理學教授戴廷龍(Tinglong Dai)甚至表示,新冠病毒疫苗的供應鏈將是有史以來最復雜的(醫藥物流)供應鏈之一。一些新冠病毒疫苗需要低至零下80℃~零下20℃的溫度,覆蓋約有30億人口的地區物流基礎設施尚不發達,疫苗運輸所需的冷鏈設備也大量缺乏。
總之,盡管疫苗的開發取得了巨大進步,終結新冠疫情流行的最大希望是接種疫苗,但是,上述難題也是橫亙在全球衛生治理者面前的一個個關卡。問題的解決,還有待于多邊多元深入合作的開展。
(編輯 余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