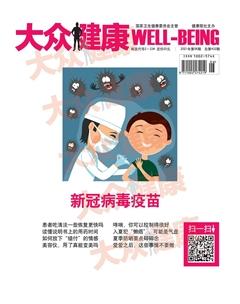打疫苗的心理建設,請做好
高文斌 唐義誠 王翔
新冠病毒疫苗已正式投入使用數月,公眾對打疫苗的看法大相徑庭。有人急不可待,踴躍地排隊接種。也有人懷著顧慮,不愿意前往接種點。為什么人們對疫苗的態度,會有這么大的差異呢?下面,我們就從心理學的角度聊聊這個問題。
從眾心態
人是群體性動物。很多時候,接種疫苗是受到從眾效應影響的。從眾行為是指個體在群體的壓力下改變個人意見,而與多數人取得一致認識的行為傾向。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曾提到,“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感,個體愿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倍感安全的歸屬感”。與身邊人的行為趨同,是扎根于人性中的重要傾向。
阿希是一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他在1952年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探索了從眾心態的影響。實驗其實很簡單:阿希給出12個線段,讓大家量出長度并報告自己的答案。當然,報告的方法是挨個口頭報告,因此實驗者可以聽到周圍人的答案。阿希讓他的“同伙”將其中7個答案故意說成錯的。結果發現,有1/3的實驗對象會屈從于明顯錯誤的答案。
也許,我們都不敢在眾目睽睽之下讓自己顯得像異類,其他人的選擇就會對我們產生群體壓力。當你發現身邊的人都去排隊打了疫苗,甚至將打疫苗視為重要談資的時候,還未接種疫苗的你就難免有些尷尬,從而產生去打疫苗的動力。
負面偏好
接受負面消息的頻率也影響著打疫苗這一行為。偶爾聽到的關于疫苗副作用的傳聞,會讓我們主動接種的意愿下降,即使媒體反復強調疫苗的安全性,也難以打消內心的焦慮感。這一現象源自我們的負面偏好。
負面偏好是一種很古老的生存機制,它把我們變成挑刺的人,把關注點放在錯誤的事情上。因為在遠古時期,一個錯誤可能就會讓自己甚至整個部落送命。到今天,大部分錯誤對人類的威脅已經沒那么大了,但大腦的“負面機制”仍在,我們仍對負面信息更加關注。在“9·11”事件之后,很多美國人覺得坐飛機風險更大,紛紛改為開車出門旅行。這好像沒錯。畢竟,剛剛在電視里看到了恐怖襲擊的鏡頭,心有余悸。然而,基準比例告訴我們,公路上的事故發生概率要遠遠超過飛機事故。也就是說,很多人選擇了一種更不安全的出行方式。
負面偏好還會導致人們因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某些人只看到打疫苗會耽誤自己的工作時間,往返難免周折,這種“短期可見”的痛苦讓他們逃避接種疫苗。這依舊是一種非理性的判斷。眾所周知,相較于罹患疾病帶來的痛苦體驗、嚴重的后遺癥、高額的醫療費和工作延誤,幾小時的接種往返時間明顯更加劃算。
了解了負面偏好這一心理傾向,當你看到一個朋友打完疫苗有了較嚴重的不良反應,內心產生一種焦慮情緒時,就不妨覺察一下:這種焦慮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負面偏好影響的?這種自我反思,有利于降低不必要的抵觸與恐慌感。
心理成本
為了方便疫苗的接種工作,以高校、社區和公司等為單位集體組織接種疫苗的做法,極大地方便了公眾。這既不會過多占用大家的時間,也保證了整個過程中的組織與紀律性,減少混亂。這其實就是在降低公眾接種疫苗的心理成本。
我們對于容易做到的事情,往往會更加喜歡去做。當然,降低接種疫苗的心理成本,還有許多其他方式。譬如,媒體對疫苗效果的多次宣傳,可以逐漸搶占民眾認知,消除對疫苗的陌生感。人們往往喜歡和習慣于自己熟悉的東西,對不熟悉的東西傾向于做出負面的評價。越是熟悉的事物越能為自己帶來安全感。新聞報道長期宣傳疫苗,可以增加人們對于疫苗的認知。當個體掌握的知識越詳細時,對疫苗的抗拒心理就會越弱,接種的心理成本就會降低。
正常化偏誤
有人不去打疫苗是出于一種“僥幸心理”,認為不打疫苗也沒大礙。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正常化偏誤。這個概念是說,當一個災難已經發生的時候,人們往往意識不到災難的發生,還以為一切正常,這樣就耽誤了自救的最佳時機,導致自己面臨更大的危險。
正常化偏誤導致我們不去提前應對可能的風險,以至于在災難發生時難以全身而退。歷史上,因正常化偏誤導致的悲劇不勝枚舉,龐貝古城的慘劇就源于這種認知偏差。我們知道,龐貝古村是在一次火山爆發的時候,整體被火山灰淹沒的,全城兩萬多人幾乎都死了。考察龐貝遺址時會發現,人們死前似乎還在做日常的事,根本就沒有反應時間。但事實是,從火山爆發到火山灰抵達龐貝城,中間有好幾個小時。
另一個例子是納粹統治時期德國那些富有的猶太人。1935年,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政策已經非常明顯了,有10萬猶太人逃離了德國,但還有45萬人選擇了等待。他們總覺得“或許不至于吧”——結果都被送到集中營遭到迫害。
當你陷入正常化偏誤,認為不打疫苗或許“也不會出事”的時候,不妨想象一下感染新冠病毒的嚴重后果。這種對不良結果的想象可以降低對風險的低估,幫助我們做出理性選擇。
性格影響
接種疫苗的主動性與人格特質也有較高關聯。一般來說,主動接種疫苗的人通常具備較高的盡責性和宜人性特質。宜人性高的個體,處處為他人著想,共情能力強,看重他人的感受,接種疫苗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有益于公眾健康的利他行為。而盡責性強的人有很強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愿意為了集體利益做必要付出。接種疫苗具有較高的公共價值,對他們來說是社會責任的擔當,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不愿意打疫苗是出于一種“不愿意為公眾利益做奉獻”的人格特質。心理學上有一種“馬基雅維利主義人格”,是指為達到目標,挑戰常規道德準則,不惜使用欺詐等手段來操縱他人的個體。這類人性格冷漠、擅長操縱他人,看重結果卻忽視道德。他們更愿意操控他人獲取利益,不會關心公眾和社會的利益。對這類人來說,打疫苗或許只是一種對自己時間的浪費,看不到接種背后的社會意義。
調整心理
如果你也對接種疫苗懷有過度擔憂,可以嘗試以下方法對自己的心理狀況做些調整:
1.尋求社會支持:家人朋友是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來自家人朋友的鼓勵可以讓個體更愿意接受疫苗。
2.隔離負面信息:互聯網時代,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由我們想看到的信息編織的繭房里,媒體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少看手機,多接觸生活當中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多接觸大自然,久久不能散去的焦慮恐懼的情緒就會悄悄消失。
3.學習放松技巧:我們還可以使用一些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正念冥想和瑜伽。這些簡單的技巧都可以幫助我們放松心情,不被負面情緒裹挾。當我們冷靜下來后,自然能更好地做出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學習心理學知識,掌握心理自助技巧,建立心理學頭腦,將有助于更好地應對外部世界的突發狀況,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保持穩定的心態。 (編輯 余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