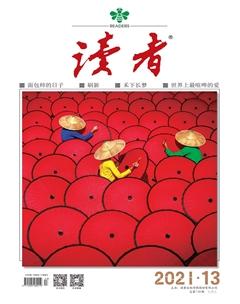我在母親身上看見(jiàn)了自己
母親已經(jīng)去世20年了。
這么多年來(lái),我一直在夢(mèng)里找媽媽?zhuān)傄舱也坏剑缓罂扌选V钡綆啄昵埃谖业膲?mèng)里,她不再出現(xiàn)了。
也許,是我終于釋然了吧。
她走的那一年,我還在讀碩士研究生。我沒(méi)告訴舍友,她們只知道我媽媽病了。我裝得若無(wú)其事,白天跟她們一起吃飯、說(shuō)笑,夜里獨(dú)自輾轉(zhuǎn)反側(cè)。怎么就這么倔強(qiáng)?想來(lái),一是不愿暴露自己是孤兒(父親已先于母親5年去世),不想看見(jiàn)別人同情的目光;二是自己也拒絕接受現(xiàn)實(shí),有逃避心態(tài)。母親的葬禮結(jié)束后,一個(gè)堂姐看著我哭了:“你以后可怎么辦啊?”我甚至還笑了一下說(shuō):“沒(méi)事。”
接下來(lái),我碩士畢業(yè),然后去南京大學(xué)讀博。沒(méi)人知道我父母雙亡,跟大家一樣,我讀書(shū)、逛街、談戀愛(ài),為論文苦惱,唯有在夢(mèng)里會(huì)找媽媽?zhuān)也恢瑔柩手褋?lái)。
我也會(huì)問(wèn)自己:這么多年過(guò)去了,為何還不能放下?
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心結(jié),母親是我生命里最原初的痛與愛(ài)。
每一代人的父輩,都有時(shí)代的烙印和個(gè)體的缺憾——大環(huán)境簡(jiǎn)單粗糙,自己還沒(méi)長(zhǎng)大,就倉(cāng)促間為人父母。結(jié)果,夫妻關(guān)系、親子關(guān)系和社會(huì)關(guān)系,攪在一起,成了一團(tuán)亂麻。
我是“70后”,母親是“40后”。父親是小學(xué)校長(zhǎng),謹(jǐn)慎內(nèi)斂,又敏感細(xì)膩。母親是小學(xué)老師,天真得一塌糊涂。她好像永遠(yuǎn)都搞不懂自己的社會(huì)角色,不會(huì)跟別人打交道。父親經(jīng)常因?yàn)槟赣H說(shuō)錯(cuò)話(huà)、做錯(cuò)事而大發(fā)雷霆,與此同時(shí),母親就爆發(fā)頭痛,然后蒙頭大睡。多年后,我終于恍然大悟,其實(shí)這是焦慮導(dǎo)致的神經(jīng)性頭痛:她知道自己錯(cuò)了,但不懂自己錯(cuò)在哪里,又知道自己改不了,頭痛是一種應(yīng)激反應(yīng),也是她的自我懲罰。
所以,在我的心中,母親不只是母親,還是一個(gè)孩子。我跟她一起焦慮,一起難過(guò),一起頭痛,也一直不放心她——父親生氣,我總替母親打圓場(chǎng);她去外婆家,我會(huì)一直等,直到她騎著自行車(chē),歪歪扭扭地出現(xiàn)在村口的小路上,才歡天喜地地一起回家吃晚飯。
這是一個(gè)沒(méi)長(zhǎng)大的小孩,對(duì)一個(gè)永遠(yuǎn)長(zhǎng)不大的大人,混沌而強(qiáng)烈的同理心和責(zé)任感。
原生家庭的影響是深遠(yuǎn)的。母親的天真和幼稚,讓我一直對(duì)社會(huì)和他人,既恐懼又好奇,既敏感又疏離。
中國(guó)人一向認(rèn)為,個(gè)體一定要被群體接受,社會(huì)是個(gè)體的歸宿,成熟的標(biāo)志便是個(gè)人價(jià)值被社會(huì)承認(rèn)。融入社會(huì),就像一滴水匯入大海,一粒沙隱入沙漠,然后才有安全感。一個(gè)人被社會(huì)拋棄,是可恥的。
在西方語(yǔ)境里,盡管也有社群主義,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性,但總體上,個(gè)人與社會(huì)保持著某種緊張和對(duì)立。所以,對(duì)西方式的“自我”而言,社會(huì)是敵人,是異化的力量。因此,尼采才會(huì)對(duì)群氓充滿(mǎn)警惕,薩特才會(huì)說(shuō)“他人即地獄”。
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痛苦,單純激烈;中國(guó)人有中國(guó)人的痛苦,復(fù)雜曖昧。并非所有人都像薛寶釵那樣,天生適合集體生活,并認(rèn)為社會(huì)化是理所當(dāng)然的。
對(duì)有些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融入社會(huì),其實(shí)是被殘酷絞殺的過(guò)程,兇險(xiǎn)、慘烈,受到的創(chuàng)傷,甚至伴隨一生。母親的癥狀是非定期發(fā)作的劇烈頭痛,我的癥狀則是在自我貶斥、自我懷疑和自我肯定之間,來(lái)回?fù)u擺。
不過(guò),值得慶幸的是,正是在這種巨大的折磨中,自我才逐漸形成、顯現(xiàn)。我們才能真正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樣的人生,成功的定義是什么。
世事如此,自我也如此。自我是流動(dòng)的,成長(zhǎng)是一個(gè)不斷破碎、不斷重建的過(guò)程。
我想起林黛玉。她小時(shí)候也孤傲、任性,談戀愛(ài)的時(shí)候也耍各種小性子。因?yàn)閷?duì)這個(gè)世界有愛(ài),有期待,所以格外敏感多疑。但我們也看見(jiàn),她在一點(diǎn)點(diǎn)長(zhǎng)大,開(kāi)始理解賈寶玉,甚至接納了寶釵,越來(lái)越心平氣和。《紅樓夢(mèng)》第七十六回里,她跟史湘云在凹晶館聯(lián)詩(shī),天上一輪皓月,湘云說(shuō)要是坐船吃酒該多好,“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倒是黛玉笑道:“古人常說(shuō)的好,‘事若求全何所樂(lè)。”黛玉還說(shuō):“不但你我不能稱(chēng)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無(wú)論事大事小,有理無(wú)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

這樣的黛玉,這樣通情達(dá)理、心平氣和,我為她開(kāi)心的同時(shí),居然有點(diǎn)兒悵然若失——她的沉醉忘情、跌宕多思,就這樣一去不復(fù)返了。而這些,往往是詩(shī)意和自由的來(lái)源。
所以,過(guò)去、現(xiàn)在和未來(lái),到底是得還是失?都很難說(shuō)清楚。
母親的天真,未嘗就一定要拒絕、要排斥。她的數(shù)學(xué)特別好,在學(xué)校里,她講的課永遠(yuǎn)最好。如果天地足夠廣闊,天真就是生命的源泉,內(nèi)在的活力。
有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這個(gè)道理。
作家安·蘭德在《源泉》里說(shuō):“創(chuàng)造者所關(guān)心的是征服自然,而寄生蟲(chóng)所關(guān)心的是征服他人。”
創(chuàng)造者為他的工作而生存,他并不需要其他人,他的首要目的存在于自身;而寄生蟲(chóng)通過(guò)侵占的方式生存,他需要其他人,其他人成了他首要的動(dòng)機(jī)。
所以,她說(shuō):“對(duì)一個(gè)創(chuàng)造者來(lái)說(shuō),所有與他人的關(guān)系都是次要的。”
所以,她說(shuō):“成功就是捍衛(wèi)自己的完整性,跟功成名就沒(méi)什么關(guān)系。”
年輕的時(shí)候,我懼怕自己活成母親的樣子。
現(xiàn)在我知道,母親是我的基因,我的血液。我不能拒絕她、否定她,要愛(ài)她和接納她。她是我的過(guò)去,也是我的起點(diǎn)。
母親在我的夢(mèng)里不停地出現(xiàn),我尋她不得,焦慮哭泣,其實(shí)是因?yàn)槲覂?nèi)心缺乏安全感。等我理解了她,接受了她,就是理解了過(guò)去,接納了自己,從此,她便從我的夢(mèng)里消失了。但我知道,她已經(jīng)以另一種方式,跟我和平共處了。
父母和兒女,就這樣互相折磨,也互相成全。
盡管我的父母都不完美,但我知道他們愛(ài)我。我愛(ài)吃水果,父親會(huì)騎著自行車(chē)去果園,買(mǎi)一大麻袋蘋(píng)果、梨子,打開(kāi)袋子的時(shí)候,香味四溢,那一天就是我的節(jié)日。
母親特別會(huì)做紅燒茄子,可是父親每次買(mǎi)回來(lái)的茄子都老掉牙了。母親切開(kāi)茄子,看見(jiàn)滿(mǎn)滿(mǎn)的籽:“唉,又這么老!不是教你怎么辨認(rèn)老茄子和嫩茄子了嗎?你咋就學(xué)不會(huì)呢!”
哎,媽?zhuān)业浆F(xiàn)在也不會(huì)辨認(rèn)呢。這一點(diǎn),我真像父親。
父親責(zé)備了母親一輩子,最后他遭遇車(chē)禍癱瘓了,是母親給他做飯,帶他看病,背他上廁所,背他曬太陽(yáng)。一次,我看見(jiàn)父親拉著母親的手,掉起眼淚,母親也哭了。
我早就知道,他們是互相愛(ài)著對(duì)方的。
這是我父母留給我的最寶貴的東西——不管世人如何,我一直相信愛(ài)。即使傷痕累累,也無(wú)怨無(wú)悔。
(甘 泉摘自微信公眾號(hào)“劉曉蕾的紅樓夢(mèng)”,李 娟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