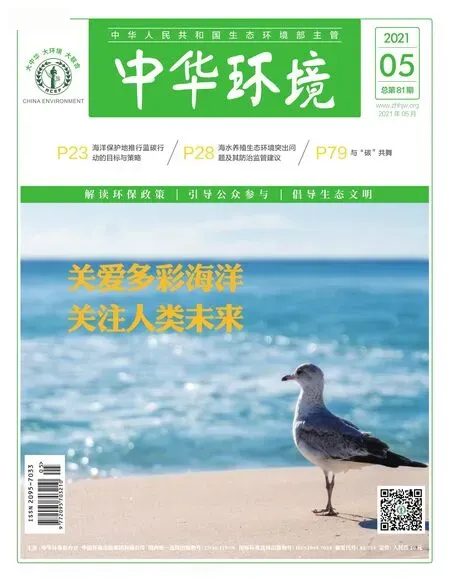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體系建設
文 陳惠珍 白續輝
氣候變化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產生了深遠影響。當前,氣候變化法、生物多樣性法、海洋保護法“各管一塊、彼此割裂”的格局,削弱了國際社會在氣候變化背景下應對海洋生物多樣性挑戰的制度性能力與效率。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推動建設綜合性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框架,成了中國與世界的重大戰略選擇。
2021年4月召開的第三十次“基礎四國”氣候變化部長級會議,向國際社會發出了進一步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號召;同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對外發布的《海洋碳綜合研究:海洋碳知識摘要及未來十年海洋碳研究和觀測協調展望》報告,則迫切呼吁各國高度重視海洋與氣候相互作用帶來的影響,凸顯了氣候變化背景下海洋生物多樣性面臨的挑戰。可喜的是,定于2021年10月在昆明召開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將制定《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這無疑是各國推動氣候變化背景下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體系建設的一次重大戰略契機。海洋與氣候相互作用機制研究的深入,為近年來人類完善相關藍色挑戰應對方案與制度框架提供了重要基礎。
氣候變化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海洋遺傳多樣性、海洋物種多樣性、海洋生態系統多樣性、海洋景觀多樣性四個層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現代工業驅動下的全球氣候變化,不僅向海洋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施加了巨大作用,更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產生了日益顯著的影響,引發了生態系統功能與社會經濟領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導致人類與海洋的關系空前復雜。
物種分布空間變化
溫度被認為是影響海洋生物地理分布的重大環境因素之一。近幾十年來,全球變暖引發了持續的海洋化學與物理過程變化,在這一背景下,許多海洋生物因無法適應升高的溫度或其食物鏈因海水升溫而遭到破壞,被迫遷往水溫較為涼爽和食物較為豐富的海域。例如,美國《氣候變化指標》第四版透露,美國龍蝦、黑鱸、紅鱈魚和其他100多種海洋物種的棲息位置已經發生明顯北移。即便是在低溫季節,澳大利亞海域的鯨鯊等也會向南或向東進行更遠的遷移,以便尋找更冷的水域。海洋物種分布空間的變化,既導致了原海域生物多樣性的退化,也在高緯度地區引發了外來生物入侵,進而改變該地的生物多樣性結構與整體面貌。
物種局部滅絕
國際科學界預測,在氣候變化機制下,由溫度、鹽度變化和海水酸化驅動的局部物種滅絕概率可能會比較高,熱帶地區大規模喪失物種的可能性最高。無法向適宜海域遷移的海洋生物,面臨一系列的生存不確定性,最終極可能走向消亡(如白化珊瑚)。底棲生物向適宜海域遷移的速度遠遠落后于游泳生物,所以也面臨日益嚴酷的生存挑戰。而且,受海水酸化的影響,相關貝類的外殼變得不再像過去那么堅固,更易于被其他生物大規模捕食,因而種群前景堪憂。北極地區海冰的消融和水溫的上升,則可能對當地整個生態系統和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樣性產生重大威脅,特別是導致極地原有相關海洋生物的滅絕。極地冰山融化導致的全球海平面升高,還給沿海地區的紅樹林等海洋生物和濱海濕地帶來了被淹沒的巨大風險。與此同時,隨著海洋酸化等問題的加重,海洋中的含氧量可能進一步降低,當前海洋中的貧氧區和“海洋死區”的范圍有擴大趨勢,許多生物因為面臨“呼吸障礙”而無法生存。而那些受到氣候變化嚴重影響但并沒有立即滅絕的物種,種群規模則可能會被不斷壓縮,從而面臨遺傳多樣性等方面的挑戰。
海洋生態功能喪失
海水升溫導致的淺水層浮游生物特別是浮游動植物的死亡,將破壞海洋食物鏈的基礎與用于制氧的光合作用機制,并進而動搖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整個框架。海水酸化導致的珊瑚大滅絕,將導致魚類喪失重要的產卵棲息地,并可能使數千種海洋物種無法獲得相應的生存支持。浮游植物、海草床、海岸帶紅樹林、濱海沼澤等的喪失,將極大地削弱海岸帶的儲碳能力,破壞人類的藍色碳匯進程。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海洋變暖會增加蒸發到空氣中的水量,增加氣候的不確定性和極端天氣出現的頻次、強度,這不僅可能催生破壞力驚人的暴雨和洪水,給人類經濟社會造成巨大的損失,更可能引發局部火災、氣旋、干旱、極寒等異常現象,威脅整個地球的生態安全。不過,當前令科學界更為擔心的是,未來吸收了過量碳的海洋,不僅可能會停止吸收碳,喪失調節氣候的能力,而且可能會變成新的排放源,轉而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從而導致溫室效應加劇,此即發生海洋生態功能的大逆轉。
國際法響應的不足
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海洋生物多樣性挑戰,近幾十年來國際社會試圖利用法律工具進行必要的應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臨著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
國際法碎片化
一般來講,民事合同僅對合同當事人產生拘束力,即“合同相對性”。與此類似,國際條約一般僅對締約方具有拘束力,這被稱為“條約相對性”。條約相對性從根本上決定了相關國際法的適用范圍和效力,也引發了“國際法碎片化”問題。例如,原則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都僅適用于簽署了該公約的締約國,這三大國際條約之間不存在“誰是誰的上位法”“誰比誰大”或“誰能管誰”的法律關系。實際上,當前氣候變化法、生物多樣性法、海洋保護法三大體系互不統屬,不同國際法體系下的項目重復建設、綜合資源浪費問題和法律原則、規則之間的不協調問題也逐漸顯現。坦率地說,國際“海氣相互作用”法律領域的制度碎片化雖然還沒有達到危害國際法體系穩定性的程度,但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國際法體系內的資源分配效率,削弱了整體的規制效果,制約了人類對“海氣相互作用”機制下生物多樣性危機進行綜合制度性反應的速度和能力。
權威性與有效性不足
首先,國際法自身的權威性不足。一般來講,國內法是由一國的最高主權者所制定,對該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均具有法律約束力,部分國內法甚至還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與此不同,由于當前國際上并不存在統一的世界政府,各國之間沒有一個超主權者“話事”,國際法只能在各國認可的情況下有效運行,其本質上是國家間共同意志的載體和國家利益妥協的產物。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除少數經濟制裁、技術禁運、公開譴責等措施外,國際社會也往往難以對其進行有效的懲罰。因此,國際法在規制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問題時,往往會受到很多挑戰。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大力發展高碳產業,即是對國際法權威的嚴重挑釁與侵蝕。
其次,國際氣候變化法、生物多樣性法領域存在著大量的國際軟法和部分不易被承認的國際習慣法規則,導致相應國際機制的國際法權威不足。1982年的《世界自然憲章》、1986年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公約草案》、1992年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017年的《世界環境公約(草案)》等均是一些綱領性或指導性文件,以倡議為主,權威性、強制性不足,相關制度框架的穩定性較差;而部分在理論上可能被認為具有適用性的國際習慣法則面臨識別和證立方面的難題,甚至和國際軟法難以區分。
最后,相關國際法對綜合性生態環境挑戰的制度干預能力有限。例如,1911年的《保護海豹條約》、1946年的《國際捕鯨管制公約》等誕生于“前危機時代”,面向新形勢、新問題的針對性不強。與此同時,國際法不同分支的實施機制所依賴的動力源不同,這也導致了治理方向的分散和相關指向性的弱化。其中,從利益激勵視角來看,氣候變化法的實施主要由關注工業危害的國際可持續發展進步力量和清潔能源勢力驅動,其核心目標是通過減少碳排放來穩定地球氣候系統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生物多樣性法的實施主要由關注地球生物圈安全的國際生態保護與科學力量驅動,其核心目標是通過確保生物多樣性來實現人類與自然的永續發展;海洋保護法則主要由面臨生態環境威脅的沿海國驅動,其核心目標是通過確保海洋生態環境質量來維護與增進國家海洋權益。這種“分門別類”的制度運行格局導致氣候變化法應對海洋生物多樣性挑戰、生物多樣性法和海洋保護法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有效性均有所不足。
科學基礎的缺陷
西方一些學者和官員認為,碳排放和全球氣候變化的關系在科學上尚未得到徹底證實,因而持續質疑相關國際法律制度的科學性與正當性。與此同時,藍碳捕獲技術、海洋生物多樣性監測技術、海洋生態修復技術等均尚未完全成熟,甚至部分技術仍處于研究和開發階段,極大地限制了國際法律制度的賦權、賦能和規制、保護范圍。例如,北半球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海洋生物空間分布變化案例被發現和確認,而對南半球的類似變化則缺少必要的系統化關注和研究。部分學者認為,海洋生物棲息地北移現象較為突出,可能是因為南半球的海水變暖程度沒有北半球的高。另一些學者則指出,南半球國家、人口相對較少,人類對南半球海洋物種的情況了解不足,是導致“北移”研究較多而“南遷”案例較少的重要原因,南半球生物的南遷規模與趨勢亟須國際社會的進一步關注。從科學與制度的復合型視角來看,地球生物圈是一個整體,南北半球的海洋生物多樣性演進態勢、規律共性與差異,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背景下海洋生物多樣性挑戰時需要的“重要情報”,關系到相關法律制度框架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因此“不可不察也”。
國家間的利益博弈
首先,國家間的制度需求緊迫性不同。氣候變化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不同,因而許多國家對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問題呈現出了不同的立場與態度。其中,隨著北半球溫度帶的北移,高緯度國家階段性地成了氣候變化的“受益國”,其海洋生物多樣性水平非但沒有下降,反而大為上升,并進而推動了其經濟社會的發展。馬爾代夫等島嶼國家因面臨迫近的生存危機,對氣候變化與海洋保護問題反應劇烈。這種“影響差異”不僅導致了國家間對呼喚國際法干預的迫切程度不同,還導致了國家間對具體國際法制度內容訴求與取舍的差異。
其次,主要國家履行相關國際義務的動力不足。過去幾年里,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出現了嚴重倒退。拜登政府雖然擺出了“碳減排”姿態,但其首要目標是重塑美國的綠色形象、重建美國的生態道義優勢和重獲國際社會的信任,從而提升美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地位,在具體政策實施上則存在不少動作虛化現象,影響了國際社會在氣候變化框架下應對海洋生物多樣性危機的能力。
最后,國家間對海洋生物多樣性領域的經濟利益訴求不同。近年來,國家管轄范圍外海域生物多樣性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問題(BBNJ)國際協定談判成為國家間海洋利益博弈的前沿戰場。例如,發達國家反對將海洋遺傳資源認定為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反對在國家間分享海洋遺傳資源機密信息,反對在海洋遺傳資源知識產權領域適用強制來源披露制度,從而利用其海洋科技優勢獲取較大的經濟與技術收益。發展中國家則與之持相反立場。這類國家間利益博弈嚴重影響了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體系建設進程。
中國的相關選項
中國應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威脅、海洋保護領域的新挑戰,通過提供氣候變化背景下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體系建設的中國方案,引領國際生態環境保護潮流,進一步獲取國際話語權和制度性權利,為維護人類福祉與地球安全做出更大貢獻。
明確目標與工具

■ 全球變暖引發了持續的海洋化學與物理過程變化
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在本質上是生態安全與資源安全問題,需要納入總體安全觀框架下進行綜合性的制度建構。其目標底線應當是避免海洋生態系統崩潰,并建立有效的氣候變化適應框架,最終訴求則應是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免受根本性和不可逆轉的破壞,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與可持續發展。為此,至少需要兩類規制工具。一是旨在管控和消除威脅的目標管理性工具。其主要應針對氣候變化挑戰,加強碳排放管理。2020年中國向世界宣告了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這類承諾作為氣候變化管理工具,有利于世界減少和消除氣候變化威脅,從而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二是推動世界適應氣候變化現實的制度性工具。生產模式和生活習慣的制度性誘導變遷是重要的戰略選擇,以經濟有效的方式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則更加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支持與推動。考慮到海洋對氣候與生物多樣性的巨大影響,對氣候變化事務的管理和對生物多樣性的管理在海洋領域進行制度性交叉融合,將可能會極大地提升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
推動國際造法
從氣候變化影響的角度來看,單靠《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已無法有效應對海洋生物多樣性銳減問題,避免污染、控制捕撈、養護種群等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海洋生物面臨的海水物理與化學環境劇變危機,《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等對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義正在日益凸顯。可以看到,海洋保護、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法律正在國際規制領域發生融合。中國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主動加速這一制度融合進程,提升“氣候變化法藍色化”水平。例如,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里,中國可以建議設立專門的氣候變化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管理制度,特別是建立海洋保護法、氣候變化法、生物多樣性法的協調機制,明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下的法律地位與功能設定,為世界打造“海氣生”三合一國際法文本奠定軟法基礎。同時,中國可以聯合部分締約國,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之下發布專門的《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倡議》,進一步明確相關理念、主張、原則和制度、政策建議等。
強化國家實踐
中國應加快制定和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應對法》,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法治體系和體制機制建設。一方面,推動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法向國內法轉化,同時還可借鑒移植外國一些良好的氣候變化應對法律制度,強化國內規制“海氣生”威脅的制度能力。另一方面,盡快將氣候變化背景下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體系建設的中國方案法律化、制度化、權威化,向世界提供“海氣生”威脅應對領域的“示范法”和樣板工程。其制度核心,應當至少包括三大內容:一是改進生產生活模式,推動社會經濟全面綠色化低碳化轉型,通過聯動解決社會和生態問題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二是推動建立國家級的全球性海洋立體觀測監測網絡,基于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海氣互動機制建立海洋生物多樣性損害評估、預警和應對體系。三是建立國際化的海洋保護區網絡,依托國家海洋公園等網格化管理單元,利用保護規劃和修復技術防止生物多樣性喪失,并有效維持和提升海洋生態系統碳匯能力。
現代人類文明是以規模龐大的物質生產與人類再生產為基礎的,客觀地講,這確實對地球大氣系統和海洋生態系統造成了巨大壓力,海洋生物和人類本身當前均難逃其害。從戰略上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人類進步與海洋可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也是建設現代生態文明的題中之義。在氣候變化時代,人類的發展應當“優雅”,更應當“科學”。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突圍,不僅需要多重技術的進步,更需要人類理念的更新。在自然面前,謙遜與保護既是一種人類美德,更是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