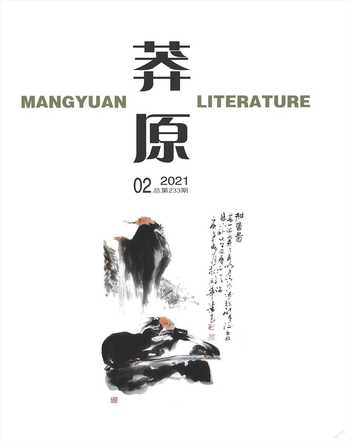功德圓滿
傅友福
1
人民醫(yī)院的病床上,母親安祥得有點夸張,孩子般乖巧,熟睡了。
“都說忙,可這時候了,誰也不來個電話,好像老人是我一個人的……”文心紅著眼圈對丈夫劉城說,又像是在自言自語。
“唉,老人都到這時候了,咱們就辛苦一點吧……”劉城無奈地嘆口氣。
文心兄弟姐妹四個,她下邊有兩個弟弟,二弟文水幾年前出了車禍,腿腳落下殘疾,行動不便,跟他老婆靠低保過日子;三弟文成好些,跟弟媳秀蓮在深圳開了個小公司,忙得抽不開身,一年難得回家?guī)状?上邊是大哥文海,早就去世了,只留一個寡嫂,守著農(nóng)村老家那個院子。原本母親一直由大嫂照顧,其他三家每月各出一千元,合起來三千元,算作母親的贍養(yǎng)費。年初時,大嫂的類風濕又犯了,聲稱自己身體不行,照顧不了母親,讓他們趕緊想辦法。姐弟三人湊到一起,商量了一天一夜,最后的辦法是——把母親送到養(yǎng)老院。
臨上車的時候,母親似乎知道了自己下一站的去處,她孩子似的央求著文心:“讓我留在家里吧,我,我不去養(yǎng)老院……”
“媽你凈說胡話,回家回家,回家誰照顧你?”文心嚴厲地反駁了母親。
母親怯怯地望著文心,像做了什么錯事似的,渾濁的眼睛里填滿了無助和恐懼。
文心的車子是豐田越野,座位寬敞又安穩(wěn),可母親卻把拐杖緊緊攥在手里,好像在找一種虛無的平衡感,才不至于被甩到車外。
鎮(zhèn)上有一家叫“夕陽紅”的養(yǎng)老院,條件不怎么樣,費用卻不低,一個月四千五百元。價錢是貴了點,可母親總算有了個歸宿,免除了大家的一樁心事。
母親被送進養(yǎng)老院的第二天,遠在深圳的小弟文成就給文心來了電話:“大姐,媽在大嫂家住,二哥每月只給五百,我知道他困難,也沒說什么;現(xiàn)在養(yǎng)老院一個月要四千五,他是不是也得漲一點?我這幾年生意不順,負擔也重,光是每個月貸款利息就得一萬多。否則……”
文成每次的“否則”,都是一種巧妙省略。文心知道他喜歡這道程序。在文成為數(shù)不多的電話里,每次都故意省略了后面的主題,像章回小說的且聽下回分解,讓你自己揣摩。
文心就把文成的意思跟文水說了。文水也是明白人,自己不能照顧母親,出不了力,出錢也是應當應分的。可是,他和他媳婦一個月的低保才三千元,扣除伙食水電費物業(yè)費,能剩下的也就一千多一點。只是這錢不出不行,一來明面上不好看,二來內(nèi)心也有愧疚感,便答應了。
大嫂這邊卻不好說。大哥生前患有精神分裂癥,四十大幾才托著關系把大嫂騙到家里,生下兩個孩子后,大哥犯了病,失足掉進水塘死了,大嫂就離家出走了。當時,兩個孩子還沒成人,只能由奶奶照顧,可老人畢竟歲數(shù)大了,長此以往也不是辦法。他們東找西尋,總算勸大嫂回來了。可是大嫂卻提出一個要求,讓文成把家里的老院給她,好讓她和兩個孩子有個安家的地方。文成和他媳婦一商量,馬上否定了大嫂的訴求。“房子是我的,你想怎么住都行。再說了,我遠在深圳,以后也不可能回家,你何必這么較真?”這事就一直拖著。現(xiàn)在讓大嫂出錢,難。
難就難吧,誰家沒本難念的經(jīng)呢?好在丈夫劉城不計較,說大嫂那份咱們出吧。母親才進了養(yǎng)老院,兄妹幾個暫時回歸各自平靜的生活,一時相安無事。
可這份平靜并沒保持多久。昨天養(yǎng)老院突然打來電話,說母親不小心摔了一跤,傷了胯骨,人竟不能動了。文心和丈夫趕忙開車回去,把老人接到了醫(yī)院。做了CT,醫(yī)生看完片子,說是髖骨骨折,做這手術得六萬多元。文心又是這個那個打了一通電話。
電話那頭,文水陷入了長久的沉默。文心能想象出來,電話在文水手里,都快要捏碎了。這錢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shù)字。這么多年來,文水已經(jīng)習慣了沉默。沉默,讓他巧妙地躲過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沒有錢,腰桿挺不起來,裝點傻充點愣,就省略了那些蒼白無力的空洞解釋。文心知道,跟文水說這些,猶如對牛彈琴。但這是一個必走的程序,口頭通知等于給了文水某種暗示。就像上面下達了文件,能落實多少,得看執(zhí)行的能力了。
文成答應得倒是爽快,說該他出的錢他肯定會出,但母親是大家的母親,必須讓大家心里明白。
不料,醫(yī)生對母親做進一步檢查,立即下了病危通知書。醫(yī)生說,母親之所以摔倒,是因為嚴重的腦血栓;昏迷不醒,也是突發(fā)中風所致。目前,血栓嚴重堵塞了血管,如果此時動手術,病人有可能下不了手術臺。醫(yī)生的言外之意,母親只能回家等待最后的日子。
畢竟是大姐,文心很快就讓自己鎮(zhèn)定下來。于是,趕緊把電話打給文水,又打給了文成。文水聽到這個消息,竟長長出了一口氣。文心本想罵他兩句,語氣卻硬不起來,心里想想,自己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便把罵文水的話罵給了自己:良心都叫狗給吃了!
文成說,既然都這樣了,那就趕緊把媽弄回家吧,葉落歸根,可別落一個外喪。
文心叫了一輛120,把母親送回了闊別三年的家里。
2
大嫂得知消息后,早早把母親的房間收拾好了。
安置了母親,大嫂對文心說:“媽都這樣了,就我們倆人守著?”
大嫂的意思文心明白,一是文成,二是文水,這倆兒子都沒有回來,鄰居知道了,閑言碎語肯定到處飛。評判別人的是非,向來是大家熱衷的話題——誰能背后不說人?誰能背后沒人說?可是,文水腿腳不方便,文成有生意走不開,不到關鍵時刻,他們能回來嗎?
“我現(xiàn)在就打電話,讓文水先回來吧。”文心安慰大嫂。
母親不知家里紛亂的事兒,躺在床上,雙目緊閉,吃喝拉撒一應免了。也許,老人回家了,心也就安了,什么都可以放下了。
文水一到家,見到母親人事不省,怎么呼喚也不會應答,一下子就跪在了母親床前,任由臉上的眼淚婆娑而下:“媽,對不起……”
“現(xiàn)在哭有什么用?一些馬上要用到的東西,還得準備準備。”大嫂說。“還有,辦媽的后事,需要很多人幫忙,都得一一上門請到,禮多人不怪。”
文家的人都在外面,只有大嫂在家應付著村里的紅白喜事。按照鄉(xiāng)下的風俗,你在別人家有事時出面幫忙,別人才會在你家場面上幫你支撐。這是一種互換感情的投資方式,誰也不能免俗。要不是大嫂在家里支應,媽的事,也許就沒人愿意出面。特別是現(xiàn)在,年輕人都出去了,真的有事了卻沒人幫忙,面子上會很尷尬。
文水知道大嫂的意思,母親的裝殮壽衣等喪葬用品,必須提前準備,免得到時手忙腳亂。可他本來就日子過得拮據(jù),加上匆忙回來,不曾有所準備,口袋里沒有幾個錢,也就習慣性地默不作聲。
大嫂見文水沒有說話,哼了一聲,走出了母親的房間。
見大嫂出來,文水趕緊拐著腿,跟在她身后。
“比如茶葉,比如煙酒,都得先備下。有人來探望,總不能讓人家干坐著吧?總得喝口茶,總得吸根煙吧?咱們不準備,到時候讓人家安排,怎么鋪張咱們也不能說啥話。我是為你們兄弟著想,能省幾個是幾個吧。過幾天媽走了,讓別人操持,錢怎么花,花多少,咱們說了不算。這事兒我見多了。”大嫂經(jīng)常在家為文家撐面子,若說村里的世俗禮節(jié),都沒有大嫂通透。
話說到這份兒上,文水馬上掏出錢包,里面只有一千塊錢,他抽出兩張,把剩下的八百塊遞給大嫂。
大嫂騎上摩托車,出了家門。
大嫂走后,文水坐在沙發(fā)上抽煙,想一些亂麻一樣的事兒。
文心走到家門口,望著不遠處已經(jīng)成熟的稻子。稻子低著頭,她也低著頭。
這時候,阿三來了。
阿三和文心同齡,又是同學。阿三畢業(yè)后當了兵,訓練時壞了一只眼睛,從部隊復了員。畢竟當過兵,阿三做事干練,敢說敢做,幾年前當選為村民小組長,村里大事小情、特別是婚喪嫁娶,都是他在張羅,別人根本插不上手。
也許是親戚關系,否則,沒人恭請,阿三是不會主動來到事主家的。
見阿三到來,文心趕緊泡茶招待。落了座,阿三的話題就轉(zhuǎn)移到文心的母親身上。
“啥情況?”
“還是人事不省的……”文心搖了搖頭。
“醫(yī)生說沒用了。”文水提著小心說。
“那得早點準備,不能再拖了。你們有什么想法,不妨說說。我只是想提醒你們,老人到了這年紀,也是高壽了,功德必須做。”阿三接過文水遞過來的香煙,叼在嘴上,啪嗒一聲,把煙點著了。一股煙霧騰起來,把他的臉面給遮蓋了。
文心看了看文水,文水沒有馬上回答。
阿三得不到準信,只是一個勁兒地抽煙,茶也喝了幾壺。他的右眼安裝了義眼,藍得發(fā)綠的眼睛,讓人瞧著發(fā)怵。
“多謝你提醒,只是這事我做不了主,得等文成回來再說。你也知道,就我目前的狀況,根本說不上話。”文水想了很久,給阿三一個模棱兩可的答案。
“是啊,是啊,家里的事向來都是文成拿主意的。”文心跟著說。
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娘家的事,她不能多嘴。這是鄉(xiāng)下的風俗。
“那行,等文成回來,需要我?guī)兔Φ模M管說話。再怎么說,咱們也是親戚,該管的事兒,我一定負責到底。”
阿三站起來,準備離開。
“是啊,是啊,到時免不了得麻煩你。”
“麻煩什么,自己人嘛。”
3
送走阿三,文心進了母親房間,很快又出來了。
“文水,我看媽呼吸急促,怕是撐不了幾天了……”
文水吸了一口煙,嘆著氣又噴了出來。
“爹走得早,媽年紀輕輕就守了寡,艱難百倍,好不容易過上幾天好日子,卻又摔成這模樣……”
文水吸一口煙,嘆一口氣,就是不說話。
“媽生了咱們兄妹四個,老了老了,進養(yǎng)老院不說,最后連做個功德,也這么為難。要我說啊,你跟文成好好商量一下,再怎么著,也得讓老人走的時候,風光一點。我知道,困難是有,咱得想辦法解決……”
文水扔掉煙頭,這才開口:“這事,還得等文成回來拿主意。”
“村里好多人都看著哩,如今誰家老人去世,不做功德?我跟你姐夫商量了,實在不行,我們就多出點。都是自家兄弟姐妹,能幫上的盡量幫忙。不過話說回來了,我們再怎么幫,也是有限。”
文心的話,在文水聽來,也句句在理。可他的心思,一碰到“功德”二字就打戰(zhàn)。按眼下的行情,做一場功德,沒個十萬八萬下不來,手稍微一松,就得十萬出頭。說到底還是個錢。文水知道,在做功德的事情上,有人吵,有人鬧,有人借了還不了,也有為這拖了幾年饑荒,更別說兄弟間反目成仇了。
錢和面子,似乎哪一方面都很重要。最后,文水干脆什么也不想了。
大嫂回來了,買了茶葉和一次性水杯,還有一些冥錢,順便也提了二斤豬肉和幾斤面條回來。大嫂把東西往客廳桌子上一擱,胸部還在微微起伏著。
“錢啊,飄樹葉一樣,風一刮就沒了……”
可是,大嫂并沒有告訴文水花了多少錢,文水也不好意思問。
吃過晚飯,有不少鄰居來探望。喝了茶,吃了煙,簡單的客套和寒暄之后,大家就把話題轉(zhuǎn)移到母親的后事上來,討論的熱情也很高漲,特別是在做功德的問題上,大家有著相同的看法。
人們說,母親八十八,是高壽,是有福氣的人。按照當下的風俗,到了這個歲數(shù),老人去世后,必須在七天內(nèi)做功德。
所謂做功德,就是讓事主家請道士做一場法事,為死者超度,在陰間過上好日子。功德做了,禮儀盡了,哀傷也就過去了。可是,近年來的功德,大大超出人們的承受能力。一場功德下來,少則七八萬,多則十幾萬,加上如今物價猛漲,若是要做功德,前前后后的吃喝,又得多出幾萬元來。但是,大家為了臉面,一旦老人去世,七天內(nèi)做功德,成了約定俗成的慣例。樹活一層皮,人活一張臉,再怎么節(jié)儉,也不應該省下這筆錢。否則,子孫有不孝之嫌。
聽了大家的意見,大嫂說:“我倒是愿意,只是我說了不算,有錢好做人,可我沒錢。”
這時候,文義說話了:“文海哥當年走的時候,就沒有做功德,如今正好是個機會。你們最多花點靈房錢,道士的禮金,一并付了,還不省事?”
說來文義也是族親,一筆寫不出兩個文字。他是有名的百事通,凡世俗之事,都能說出個道道來,別人不知道的彎彎繞,他也通曉幾分。所以,他在村里的能量不在阿三之下。
大嫂聽文義這么一說,一時勾起了很多傷心事。這是一舉兩得的大好事,她何嘗不想這樣?只是這事要文成牽頭才行,他不出聲,十幾萬的事兒,誰也擺平不了。
文義好像看出了大嫂的心事,開導說:
“這事也沒有那么難辦,等文成回來,我們也會給他提供一些建議。再說了,主事的也希望他站出來,把這事給辦了……”
話還沒說完,就聽到母親房間里發(fā)出咕嚕嚕的聲音。
大嫂趕緊沖進母親房間。只見母親張大著嘴巴,卻還是說不出話來。母親已經(jīng)四天水米沒進了。剛回來那會兒,大嫂給她喂過一點米湯,母親閉著嘴,米湯順著嘴角流下來了。湯水不進的母親,卻保留著最后一口氣,好像在等待什么。
“媽,媽……”
大嫂叫了幾聲,母親呆滯著沒有回應,喘息卻加重了很多。
在母親身邊待了一會兒,大嫂出來了。大家聽了母親的情況,都說,老人這是在等文成回來,哪怕只有一口氣,她也不愿意咽下去。很多臨終的老人,之所以不愿意咽下最后一口氣,是因為牽掛的親人還沒到齊。
這么一說,就有人抹起了眼淚。嘆氣、惋惜的聲音,蜜蜂出巢一樣,嗡嗡地響成一片。
看到時間不早了,大嫂趕緊張羅著煮吃食。不一會兒,面條上來了,大家一邊吃,一邊就功德的話題,進行又一次的討論。
文心想了想,掏出手機撥打電話。
“文成,生意再忙也得回來。媽的情況很不好,你再不趕緊回來,只怕是見不到最后一面了……”
大家就隨聲附和著說:“是啊是啊,怕就是天黑天明的事兒了……”
吃罷了點心,大伙陸續(xù)散去。客廳一下子冷清下來。大嫂又進了母親房間,不一會兒就出來了。
文心問道:“媽怎樣了?”
“張著嘴,呼吸很困難……今天晚上咱們得注意了。我看這樣吧,上半夜我在跟前守著,下半夜你和文水輪流看著。總不能媽走了,咱們都不知道個具體時間……”
文心說:“我這幾天身子總不舒服,怕是血壓升上來了。要不,上半夜讓文水看著,下半夜你陪著我一起。我,我一個人害怕……”
大嫂“哎”了一聲,算是應了,馬上進房間去了。不一會兒,大嫂有節(jié)奏的打鼾聲,在房間里徘徊,讓本來寂靜的房子,有了點鮮活的氣息。
文水一個人待在客廳里,不停抽著煙,想些無邊的心事。大約下半夜2點多的時候,外面突然傳來“咕——嘎嘎嘎,咕——嘎嘎嘎”的尖叫,聲音短促,卻很凄慘。文水聽出是貓頭鷹的聲音,心頭一緊,不禁汗毛豎起來了。想要叫醒大嫂,又覺得不妥,母親的房間,卻不敢進去了。于是,他就歪在客廳的沙發(fā)上,無聊地劃著微信,轉(zhuǎn)移自己的心緒,好讓那顆狂躁的心,平靜下來。
暗夜漫長,文水強撐著挨到凌晨四點,不見大嫂和文心起來接班,也進房間睡去了。
4
文水睜開眼睛,已是上午九點了。
問起母親的情況,大嫂說還是老樣子。正說著,文成來了電話,說是已經(jīng)坐上了動車,下午就能到家。
文心聽說文成就要回來了,懸著的一顆心,終于落了下來。
正準備做午飯,文義來了。
一邊喝茶吃煙,一邊免不了又是一番感嘆。感嘆之后,就把話題挪到當下關鍵的事情上來。文義是遠近聞名的廚師頭兒,凡是村里婚喪之事,都有他忙碌的身影。通常,文義會依照主家的情況和意思,開起菜單。鎮(zhèn)上幾家海鮮果菜日用雜品批發(fā)商店,都和文義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文水借著機會,問起有關做功德的事兒。
文義一副行家的姿態(tài),說:“這個得看實際情況。經(jīng)濟上過得去的,正餐那天要么一桌一千七,要么一桌一千八;法事前幾天倒是好說,一葷兩素一湯,就應付過去了。你們家的情況,正餐估計得有二十幾桌,加上煙酒算下來,一桌在兩千以內(nèi)就可以了。”
文義說得輕描淡寫,卻讓文水瞠目結(jié)舌——這么說來,單是酒席就得五萬?
又簡單說了一些相關事宜,文義就起身告辭了。
文水一臉謙卑:“謝謝,到時候免不了麻煩你。”
把文義送走,文心感嘆著說:“太可怕了,這鄉(xiāng)下酒席的錢,都趕上城里了。”
文水望著文心,想說什么,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自顧自地抽起煙來……
傍晚時分,文成帶著媳婦兒子,從深圳回來了。
三個人進了母親房間,呼喚著母親。文心、文水免不了陪著感傷落淚。文成媳婦以前過年時偶爾也回來過,對于母親,她突然有種說不清楚的陌生感。這幾年春節(jié),因為要照顧上學的孩子,不曾回來。文成每年春節(jié)倒是回來,但因為生意忙,也待不了幾天,就匆忙地走了。
“幾年不見,沒想到媽成了這個樣子……”文成媳婦回到客廳,手揉著眼角。
眼下事情很多,一團亂麻一樣,文成從母親房間里出來,就和文水文心談起母親的后事。
文水便把阿三和文義交代的情況,向文成說了,特別強調(diào)了為母親做功德的事。
文成一時沉默起來,掏出手機算了很久,嘴里不停地嘟囔著,顯然花費數(shù)目過大,超出了他的心理預期。
文水見文成沉默不語,也不好多說什么。
沒過多久,文心和大嫂做好了晚飯,一家圍在一起吃飯,氣氛輕松了很多。這溫馨的場景以前也曾經(jīng)有過,現(xiàn)在竟如同做夢一樣。大家誰也沒有說話,都把頭埋在飯碗里,好像這是一餐多么可口的菜肴。
大家表演啞劇一樣吃完了晚飯,丟下了飯碗,文成在他媳婦的暗示下,來到門口。
大嫂收拾了碗筷,端進了廚房。
文心局外人一樣,進了房間,關緊了屋門。
文水的眼睛則追逐著每個人的背影,來回移動著。
也不知道文成和他媳婦談了多久,天色徹底暗下來的時候,他們進了客廳。
這時候,他兒子神色慌張地喊:“爸,媽,奶奶……”
眾人聞訊,趕緊沖進母親房間:“媽,媽……”
母親的嘴大張著,似乎還想告訴他們什么,卻是僵硬的,靜默的。
大嫂一摸母親的臉,一陣冰涼迅速傳遞到手上。
“媽早就沒了,看看時間,就當是剛沒的吧……”
“媽……”
他們這才痛哭起來。
“別哭了,得趕快給媽穿衣服。”
大嫂沖著大家吼叫,馬上動手套衣服。她動作干練,沒有一點拖泥帶水。文心則站在一邊發(fā)呆,不知道該幫什么忙才好。見大嫂發(fā)火,她卻退到一邊觀望。好在大嫂是經(jīng)過世面的人,在文成的幫助下,費了半天勁,總算勉強給母親穿上了壽衣。
但文水發(fā)現(xiàn),母親的褲子穿歪了,本來想提醒他們,想想又算了,人都死了,也不在乎褲子歪不歪、好看不好看、舒服不舒服了。
母親去世的消息一傳出去,該來的人都來了。還是阿三有魄力,在他的張羅下,馬上叫來哀樂,并很快播放起來。大家擠在狹小的客廳里,在煙霧繚繞中商量著后事。
如今,母親大喪中做功德的事,便鄭重地擺上了桌面。不管怎么說,阿三和眾人都贊成給母親做功德。什么事死如生、懿德流芳,什么不做不成體統(tǒng),惹人笑話等等,一串一串的話從他們口中蚯蚓一樣爬了出來。他們的理由很充分,母親是高壽,是大喜喪;再則,文成在深圳事業(yè)有成,還能花不起這幾個小錢?
他們有很多種理由讓文成接受,也有很多種方案讓文成選擇。可是,文成還是搖著頭,沒有馬上表態(tài)。
“時間緊,如果做功德的事情定不下來,那得先安排出殯的事兒。首先是樂隊,要請什么樂隊?請幾隊?一隊多少人?另外,花圈要幾個?定什么價位?”阿三抽了一口煙,接著說,“按照去年二嬸的排場,樂隊應該請八隊,花圈十二個,另外,二十四孝和哭喪隊,怕也少不了,這是最低要求了,你們自己考慮考慮。”
正說著,文義來了。文義在村里沒名沒分的,可他整天四鄉(xiāng)八里跑著事情,交際很廣,五行八作的人都認識,其中就有不少樂隊班子,村里誰家有喪事,他就上門幫主家聯(lián)系樂隊,價格也優(yōu)惠很多。
看到文義進來,阿三的臉立刻沉下來了,那種傲慢和不屑的眼神,在他的獨眼里生發(fā)出來。
這時候文成正要上廁所,文義趕緊跟了上去。
不一會兒,文成回到客廳,阿三卻已經(jīng)走了。
文成對文水說:“二哥,文義說他聯(lián)系的樂隊便宜一點,也沒有中間抽成,平均一隊可以省下200多元。你看,是不是咱讓文義幫著聯(lián)系樂隊?”
“不妥,如今是阿三主事,文義算個啥?如果樂隊不讓阿三聯(lián)系,只怕咱們會有麻煩……”文水有些猶豫,并向文成說了夏天剛剛發(fā)生的事兒——
也是文家一個宗親的喪事,老人的年齡和母親差不多。當初主家不識禮,自己叫了樂隊不說,連煙酒菜肴也都自己安排了。到了老人出殯這一天,阿三說要外出談生意,撂下一攤子事不管了。而道士定下的出殯吉時和火葬場那邊已確定的時間,都逼在眼前,一刻也耽誤不得。看看外面群龍無首,哪個人負責哪件事兒,都沒有半點頭緒。主家沒有辦法,只好厚著臉皮,買了兩條中華到阿三家道歉,阿三這才答應幫他把事情處理好。
“你不是不知道,阿三家兄弟多,他又是村民小組長,哪方面都很強硬,不聽他的還能聽誰的?文義是自家近親,得罪不了的。”文水進一步開導文成。
“村里的事情這么復雜啊……我很少在家,算了,就依著阿三吧,回頭我跟文義解釋。”文成搖搖頭妥協(xié)了。
文水有了文成的許可,馬上趕去告訴了阿三。
阿三微微一笑:“我就說嘛,村里什么事少得了我?你們放心吧,我知道該怎么安排。”
文義知道自己沒戲了,氣得幾天吃不下飯。
5
一開始,吵鬧聲是憋悶著,從門縫里輕輕傳出來,像蒼蠅在飛舞。后來,爭執(zhí)的雙方由小聲到叫喊,爭吵也慢慢升級了,聲音一下子把洪亮的哀樂壓了下去。
文成感到不妙,不得不進了房間。一進去,就看到地上的煙頭橫七豎八地躺著。再看看阿三和文義兩個人,一個黑著臉,站在窗前抽煙,另一個臉紅紅的,醉酒一樣正坐在床邊發(fā)呆。
看到文成進來,阿三似乎找到了傾訴的對象,他馬上從窗口邊向文成走來:“文成你說說,咱村里哪一場事不是我盡心盡力地操持?哪一場事不是辦得很完美?可文義每次都有各種理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要控制在他手里,把我的意見當成耳邊風,這叫我怎么安排?”
“不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是你手太長、管得太寬了。廚房的事情,應該是我說了算,可租桌椅你要租,菜你也要安排,搭鐵棚的事你還要管……煙酒你叫了,樂隊你也叫了,道士你都安排了,你說,這還有我什么事兒?”
文義接過阿三的話,也向文成吐了不少苦水。
阿三兄弟多,財力一般;文義路子廣,財力略勝一籌。在很多場合里,他們總是為一些事情發(fā)生沖突,針鋒相對。
文成看看阿三,望望文義,攤開雙手苦笑著對他們說:“你們都是我請來的幫忙料理母親后事的,我非常感激。至于你們所說的事,我常年在外,也不大了解。希望你們不要傷了和氣,好好商量著辦吧。”
“我不是想爭什么,但我畢竟是組長,這是我的責任,人事安排上應該我說了算才是。我敢說,要是我不安排,村里什么事情也辦不了。不信你們試試,誰有本事處理得了?再說了,文義,你們廚房有工資,一天三百,我可是一分錢也沒拿,要不是看在自家人的份上,我才懶得多管閑事哩。”
阿三黑著臉,語言上多了些憤慨和抱怨。
“那行吧,桌椅我來安排,搭鐵棚的事也歸我,其他事情你來安排,這總行了吧?”
最后,文義妥協(xié)了,掏出香煙丟一根給阿三。
“好了,就這樣吧,別讓外人看笑話,說咱們不明事理。”
阿三說著,離開了房間。
文義望了文成一眼,雙手投降做無奈狀,也跟著出去了。
文成最后出來,進了母親房間。從傍晚到現(xiàn)在,一直在處理亂七八糟的瑣事,也沒有去看一眼母親。好在哀樂的聲音十分響亮,想必母親不會感到寂寞。
進了母親房間,老人安詳?shù)靥稍陟`床上。上前摸了摸母親的臉,涼得像冰一樣。文成站在母親跟前,想著寵他疼他的母親就這么去了,鼻子一酸,流下了眼淚……
吃過晚飯,阿三早早來到文家。他一來,就把文水文成叫到一邊,商量著明天母親出殯的事情。當然,話題的重點,還是關于做功德。
阿三說,糊紙房需要幾天時間,如果現(xiàn)在決定不了,恐怕時間就來不及了。
“可是,十幾萬不是小數(shù)目,你讓我們考慮考慮吧。”文成說。
“誰說要十幾萬?咱們省著點不行嗎?我給你詳細算了,頂多也就八萬。你要相信我,村里村外我辦過那么多事情,心里有一本賬呢。這次做了功德,以后周年、三年的大祭就可以免了,也省得你來回辛苦奔波。你想想,你們從深圳回來一趟,得花多少錢?得耽誤多少時間?現(xiàn)在誰家不是老人去世就做功德?再怎么著,你也得爭這口氣。”
文成還是沒有明確。
文心來了,不一會兒,文水媳婦、文成媳婦也擠進來參加討論。阿三把剛才說過的話,又重復了一遍,好讓大家聽個明白。
文成望著他媳婦,沒有說話。
一直沉默著的文心,開口了。
“阿三說得在理,你們兄弟倆好好考慮一下。”文心說著,看了看兩個弟媳婦,“你姐夫說了,要是你們決定做功德,我們可以多出點錢。二十四孝我們包了,靈房的錢我們也出,這筆開支差不多三四萬。我知道你們不容易,文水腿腳不好,又沒有工作;文成的公司剛剛成立,也貸了不少款。所以,我們多盡點心意,為的是好好給咱媽做一場功德,免得別人說閑話。再說了,媽這輩子受了那么多苦……”
文心的大方,眾人聽了直叫好。
“這才是當大姐的榜樣,有了文心的支持,這場功德就沒什么困難了。如果你們再猶豫,后悔就來不及了。”阿三一邊豎起大拇指為文心點贊,一邊橫著眼睛望著文成。
可文心的話,卻讓文成媳婦陷入了沉思,許久許久,她都沒有說話。
這時候,大嫂進來了。
也許是大嫂的到來,讓文成媳婦有了靈感,有了發(fā)揮的余地。
“既然阿三和大姐都這么說了,我想我們再不近人情,也說不過去。做功德畢竟要花很多錢,都壓在我們身上,我們也負擔不起。如果大家同意,二哥和大嫂各出兩萬,其余的我們包了。說實在的,要是生意順利一點,我們哪會為了這幾萬塊錢,讓大家為難?”
“不行,我沒那么多錢,至多出一萬。再說了,要不是看在兩個孩子的份上,文家的門我都不想進來了……”大嫂一聽說要出錢,一臉委屈,把陳芝麻爛谷子的往事,一一抖摟出來。說到最后,大嫂的眼淚,泉水一樣流出來了。
阿三安撫著大嫂,低聲對她說著什么。
文水望望文心,又望望大家,突然大方地下了決心:“事情都這樣了,我同意。”
“這就對了,兄弟間計較那么認真干什么?”阿三笑著說,那只瞎了的右眼,也跟著活躍起來。
盡管大嫂只肯出一萬,但她和文水的表態(tài),還是讓文心十分滿意。
“當初文海沒有做功德,這次你可以自己出點靈房錢,把他的一起做了。”阿三笑著對大嫂說,滿意地離開文家,一走出房間,馬上掏出手機,打起電話來。
6
文水媳婦終于趕在婆婆出殯前,回了家。一進婆婆房間,她先是揭開婆婆的蒙臉布,仔細看了差不多小了一號的婆婆,接著嗚嗚咽咽地哭訴起來:“媽,別怪我不孝,我要工
作,又要照顧文水和孩子……”
按照鄉(xiāng)下千百年來的慣例,哭喪時的語言,必須有所指向。比如哭的內(nèi)容,應該圍繞老人一生的不易,歷數(shù)老人的艱難困苦,以及老人帶給后人的各種恩澤,人們對老人的生平褒獎等等,來進行表達,這里面有傾訴,有緬懷,有歌頌,也有不舍和惋惜。哭得好的話,語言運用得當,腔調(diào)拿捏準確,整個程序像一曲纏綿悱惻的頌歌,娓娓道來。而文水媳婦完全亂了章法,不僅不得要領,言辭也一直含混不清,雖然語氣悲切,眼睛里卻沒有多少淚水,別人也聽不清楚她哭訴的詳細內(nèi)容。
文水媳婦一向大大咧咧的,完全不懂得這些鄉(xiāng)風民俗,完全由著自己的想法來。她邊哭邊以手捶打呆坐在身邊的文水:“要不是你身體拖累,何苦讓咱媽進了養(yǎng)老院?媽,我心中的苦,有誰知道……”
文水待在他媳婦身邊,任由媳婦捶打。媳婦的哭聲,像春蠶拉絲一樣,斷斷續(xù)續(xù),沒完沒了。文成媳婦是外地人,本地特色的哭喪,對她來說猶如遙遠的歌謠,她根本掌握不了哭的訣竅,也沒有想哭的動機,索性呆坐在一邊,像個聆聽者,也像是在思考什么。
文成燒給母親買路的紙錢,有點潮濕,產(chǎn)生了很大的煙霧,在房間里彌漫起來。文水媳婦被嗆著了,眼淚流了出來。不知道什么時候,房間里安靜下來,只有文水媳婦含混嗚咽的低泣,不清不白地纏綿著。大嫂在外面注意到屋里冷清,趕緊進來吩咐著:“有人來了,大家都要哀起來,別讓人家笑話。”
大嫂的聲音很大,文心在房間里聽到大嫂這么一嚷,像得到一道什么指令,趕緊跑出來,并迅速閃進了母親房間,找個凳子坐下來,馬上扯開喉嚨,有板有眼有條理地哭起來。畢竟是家中的大姐,經(jīng)歷多,見識廣,入戲也快,哭得很有章法,也很有味道。她心中好像早就準備好一本記載著母親故事的小冊子,從母親嫁進文家開始,一直到父親早逝,母親守寡,艱難地帶著四個孩子過日子,最后,中心點轉(zhuǎn)移到現(xiàn)階段,說母親苦命,做了曾祖母還要進養(yǎng)老院,最后一跤摔得十分凄慘……等等,內(nèi)容翔實,有事實,有依據(jù),層層推進,聽者無不動容。文心哭完一遍,再重復一遍,像復讀機一樣。不管怎么說,文心很有這方面的造詣,深得哭喪的精髓,也很會掌握聲調(diào)和節(jié)奏,時高時低,時長時短,抑揚頓挫地表達著對母親的哀思。
不管怎么說,文心悠揚的哭聲,總算讓冷清的房間,有了點熱鬧的氛圍。
正哭著,丈夫劉城進了房間,手中拿了一個專門用來哭喪的錄音機。也不知道多少人用過了,機子表面上陳舊的痕跡,說明這東西很盛行,很搶手。不過,這東西真是好,一插上電源,里面的哭聲如泣如訴,纏綿感人,腔調(diào)也勝過文心很多。哭聲通過小喇叭一傳送,悠揚到外面來。
有了這機子,文心閉了嘴,掏出紙巾擦著額頭上不斷涌出的汗。
“長時間的哭泣,也不是個辦法,這個是我找哭喪隊租的,一天二百。”
劉城說完,拉著文心出了母親房間。臨離開時,又對文水文成說:“你姐身體不好,讓她休息一下。如今有了這個,你們也不用哭了。”
畢竟是機器,哭聲聽起來多少有點失真。只是,紙錢的灰燼到處飛揚,母親身上蓋的大紅被子上,落下了很多紙灰,形成了很多不規(guī)則的圖案,有的像天真的小孩,有的像委屈的老人,還有一些像奇形怪狀的動物。
“文水,文水,文水呢?”阿三在院里一聲一聲地叫。
文水聽到外面有人叫,就出了房間。
原來阿三是來報賬的,說六個樂隊的錢,必須先付清。
但文水沒錢,突然想到自己應該出的兩萬元份額,只好向文心開了口:“姐,你先借我兩萬吧,我……我爭取到年底還給你。”
說爭取,就是給自己留一個臺階,以后好有個委婉的說辭。文水自己也知道,他年底根本還不起這錢。
“那好吧,只是這錢是你外甥做生意的錢,你別拖太久就是。”
文心說著,馬上給她兒子打了電話,兩萬塊錢很快就轉(zhuǎn)過來了。
原本說好了的,由文水做賬,現(xiàn)金由文成媳婦管著。收到文心替文水轉(zhuǎn)的兩萬元,文成媳婦的眉頭皺了一下,卻沒有說話。
有錢就有效率,老人的喪事按部就班地進行,很順利。文水突然想起電視廣告上的一句臺詞“你好,我也好”,他改了一下:錢好,事也好。
7
巡棺,是出殯儀式中最隆重的一步。
道士們在前面敲著鈴鐺,揮著拂塵,咿咿呀呀地念著經(jīng),孝子賢孫跟在道士后面,繞著母親的棺材,像一群循規(guī)蹈矩的驢,一圈圈地轉(zhuǎn)著。
隨后,巡棺停止了,道士們專門給孝子賢孫留下一小段空當時間,讓親人向逝者作最后告別。一時間,大嫂和文心帶著兩個弟媳婦,一起涌向母親的棺材,哀號聲震天動地,把悲傷推向高潮。特別是文心,一邊哭,一邊拍打著母親的棺材,那種痛苦、悔恨、不舍,一時間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見此情景,不少人都陪著流下了傷心的眼淚。最后,文心哭得沒了力氣,眼看就要癱下去了,丈夫劉城趕忙上前攙扶。
人生像一出戲那樣簡短,母親的出殯儀式也很快就結(jié)束了。
從殯儀館回來,文水走進母親的房間。那張母親剛剛躺過的小床,被扔到門外去了。房間里空得有點虛無,好像這房間從來就沒有人住過一樣。文水拐著腳在房間里來回走了幾趟,像在丈量著房間的面積。
這時候,阿三來了。
阿三把收到的禮金合計一下,有七萬多元,加上文成深圳朋友的禮金,總金額超過了八萬元。扣除母親喪事開銷的兩萬多元,尚有六萬多;大嫂交了一萬,文水交了兩萬,這么一來,文成媳婦手中還有九萬多元——做功德的錢,應該綽綽有余了。
文水收起了錢和賬本,裝在一個小鐵盒里,就像把母親裝在了里面一樣。
送走了母親,一家人緊繃的神經(jīng)總算松弛下來。有了點空閑的時間,都想好好地補一覺。
老屋那邊卻熱鬧起來——糊紙房的師傅們來了好幾個,他們正忙著搭建母親和文海的冥房子。
吃過早飯后,大嫂開始張羅一些瑣事,文水媳婦走過來,問起母親喪事的開銷。大嫂說花了兩萬多,禮金收了八萬。文水媳婦一合計,說,那不是還有九萬多元?
大嫂這才猛然醒悟,說:“我和文水出了三萬,這么一來,文成就不用出錢了?”
沒什么文化的大嫂,對于金錢對于數(shù)字,卻十分敏感,何況這只是簡單的加減法而已。
文水媳婦的眼睛詭異地向周圍脧了一圈,見沒什么人,就悄悄地告訴大嫂:“事情還沒結(jié)束,現(xiàn)在還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緊接著,又在大嫂耳邊如此這般說了些什么。
大嫂點點頭沒說話,小眼睛卻一直眨個不停。
這邊大嫂和文水媳婦正打著小算盤,那邊文義和阿三,前后腳相繼來到文家。他們一來,就把文水、文成叫到身邊,似乎要商量什么事兒。
喝著茶,抽著煙,文義把自己擬好的正餐菜單,擺在桌子上。
“這個單子我和阿三商議過了,按一桌一千六百元的標準。我們參考了之前別人家的功德酒席,有的人家一桌兩千元,也有的是一千三百元,一千六,算是個折中價吧。”
阿三也點頭稱是。
文水有點納悶,他們前天還爭得臉紅耳赤,這會兒卻這么默契,已經(jīng)看不出他們曾經(jīng)爭吵的痕跡了。
文成把菜單從頭到尾看個仔細,有鮑魚,有海參,有魷魚,有鰻魚,還有鱖魚什么的,海鮮占了大部分;雞鴨豬肉牛羊肉,倒成了配菜。文成在深圳吃過不少酒席,怎么看這都是一桌十分豐盛的菜肴。
見文成沒有說話,文義把話題轉(zhuǎn)向文水。
“文水,你弟弟長期在深圳生活,不大了解我們這里的行情,你來決定吧。這可是最省錢的開銷了,我們知道你們的經(jīng)濟條件并不那么寬裕,開這單子的時候,阿三也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議。”
文水沒有說話。他知道,去年村里有場功德,一桌的費用才九百多元,即便現(xiàn)在物價漲了,也開不到一千六百元啊。同樣是文義主廚,同樣是文義開的菜單,怎么這次高出這么多?但文成沒有發(fā)話,他也不敢說什么。
“讓你們費心了,能不能再省一點?”文成看了很久,終于發(fā)話了。
阿三聽了文成的話,回頭看看文義,又看看文水。
“其實,再省錢的酒席,我們也開得出來。只是一味節(jié)省,讓人家邊吃邊說三道四,錢花了,也不落好。要是普通人家,也就罷了。可是,像你文成能在深圳開公司的,能有幾個?我覺得,做人還是面子重要,大家的眼睛,可都看著你呢。”
文水見文成沒能把酒席的價格降下來,就打起圓場,說:“這樣吧,你們再斟酌一下,一桌定在一千五左右。不是煙酒還沒算嗎?加上煙酒,一桌少說也得一千七了。”
文義想了一會兒,和阿三會意一下,也就點頭答應了。
根據(jù)阿三的經(jīng)驗,因為文家沒什么親戚,最終就定下了正餐二十五桌,他讓文義把菜單修改一下,這事兒算是有了個了結(jié)。
母親的功德如期開始了,幾乎整個村子的人,都動員起來了。人們平常日子過得寡淡,好不容易遇到了大事,也不管紅事白事,都跟著激動。
文成要跟著道士們轉(zhuǎn)靈;所有的女眷們,也要在靈房那邊哭靈。文水的腿腳不方便,就坐鎮(zhèn)在家里,負責支應阿三、文義和辦事的人。
按規(guī)定,母親的功德要做三天。從頭一天開始,凡是來幫忙的人,每人每天早上發(fā)一包香煙;到了晚上,再發(fā)一包。阿三拿走一條香煙,不一會兒就沒了,再過來拿。阿三每拿走一條煙,就像割去文水的一塊心頭肉。
最后,阿三跟文水說:“干脆這樣吧,事情太多了,你也忙不過來,反而耽誤事。接下來也不必一一報賬了,等我統(tǒng)一辦好,讓他們開好單據(jù),最后再一總算賬吧。”
阿三的話看似商量,卻是肯定的語氣,不容文水反駁。
文水找了文成,說了阿三的意思。文成想了一會兒,也只能點頭默許。
這么一來,文水倒是閑了,坐著也是無聊,便拐著腳來到門口。那里擺著一臺電子臺秤,是從文義家借來的,專門稱那些送來的肉啊菜啊什么的。
文水小心站在臺秤上,電子屏上顯示他體重七十八公斤。不對呀,前幾天在商場的電子秤稱過,是七十六公斤,怎么幾天就漲了兩公斤?
下來,再上去,還是七十八公斤。
“文水,你可小心點兒,別那邊的事情沒弄好,又添加了你摔倒的事兒。”文義看到一直在和電子秤較勁的文水,戲謔了一句。
幾個廚師也同時附和著。
“這秤有點怪,這幾天沒睡好,反而重了四斤。”
文水自言自語,聲音也不大。
剛好阿三走過來,聽了這話,呵呵一笑:“你呀,沒心沒肺,老媽死了還那么貪吃。”
一邊說著,到灶邊端了一盆昨天晚上剩下的紅燒肉,往他家里走去。
“這菜是昨天剩下的,今天要做新的,讓他拿回去吧。”文義對文水解釋說。
自己家里辦事,自己倒成了局外人,一切都作不了主。文水這么想。
這么想著,文水就拐著腳進了老屋。道士們都休息去了,只有糊靈房的人在忙活。文水看了看母親和文海的靈房,有飛機,有汽車,有銀行,幾個奴仆守在門前,栩栩如生的樣子。母親的照片就擺在靈房前,照片上,母親似笑非笑。文水不敢和母親對視,把目光轉(zhuǎn)移到靈房后面。
紙糊的房子,白花花的錢,這話一點也不錯。一棟紙房子,除了表面上金光閃閃,背后就是一些竹棍藤條支撐著,一張白紙糊上去,遮蓋了廉價和丑陋。就這么徒有其表的紙房子,一棟也得幾千元。
正感嘆著,聽見外面有人低聲談論著什么。順著紙房子的空隙望去,原來是文心、文成和文成媳婦,三人正在交流著什么,情緒十分激動。
“這事先別聲張。”文心說。
“大嫂也許知道的……”文成媳婦說。
文水怔了一會兒,走出了老屋,三個人不再說話了。一時有些尷尬,就從靈房前悄悄走過去,來到天井里。
太陽很大,刺得文水睜不開眼睛。
8
道士的鈴聲一響,嗩吶就跟著吹奏起來,念經(jīng)的聲音嚶嚶嗡嗡,好像誰捅了馬蜂窩。
大嫂從后門閃進來了。看看四下沒人,馬上湊到文水跟前,重復著和文水媳婦沒有談完的話題。
“這不行,禮金收那么多,咱們都吃大虧了。”大嫂說得很急,平穩(wěn)了一下喘息,接著說道,“文成現(xiàn)在手里還有九萬多,花大家的錢,名聲卻是他的。”
“這不是還沒結(jié)束嘛,誰知道還要花多少錢?大嫂,你也不必糾結(jié),不管怎么說,趁著這個機會連大哥的功德也一起做了,你也沒什么遺憾了。如果單獨做,還不得十萬八萬地花?算了,什么才是公平?別聽人家嚼舌頭,有些話,像流水,一淌就沒完沒了。太較真了,就不好看了。”
文水開導著大嫂,也好像在說服自己,勉強接受眼前的事實。
“話是這么說,可一碼歸一碼,咱不能吃這啞巴虧,得找個時間好好跟他們算算……”
大嫂還想說什么,阿三來找文水了。大嫂只好披上孝衣,往靈房那邊去了。
阿三說明天酒席上的酒,他聯(lián)系了一個新品牌,價錢也不貴,一百七十元一瓶。說著,拿出一個酒盒來,放在桌子上。
文水平時喜歡喝兩口,對時下流行的白酒品牌,也略知一些,卻從沒聽說過這款品牌的酒;再看看包裝,也不怎么講究,就有些猶豫。
阿三補充說:“酒喝不完可以退貨,這樣咱們可以省下不少錢。再說了,現(xiàn)在喝酒的人不多,沒必要買什么高檔酒充臉面,能省一點是一點,對不?我這人一是一,二是二,能為主家省錢,就盡量節(jié)省。”
阿三把話說到這份上,文水只好點頭答應了。
“我們相信你。”
“放心吧,錯不了。”
得到文水的許可,阿三滿意地走了。
吃過晚飯,道士們又開始誦經(jīng)了。今天晚上是做功德重要的一環(huán),幾個道士也格外賣力。靈房里的孝男孝女們,都在盡最后一點力氣,努力哭著。當然了,最大的聲音還是那個錄音機。
哭著哭著,文心的臉色突然變了,雙手抓扯著胸部,整個人也抽搐起來了。
文成媳婦就在文心身邊,發(fā)現(xiàn)之后,馬上叫喊跟在道士身后的文成:“快來,快來,快看大姐怎么了……”
文成跑過來,拉住文心的手:“姐,姐,你這是怎么了?”
“不要,不要,我不是,我是……”文心嘴里胡言亂語,不知道在說些什么。
眾人圍在文心身邊,只見文心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大家全都慌了神,趕快報告給主持的老道士。
“趕快把她扶到房間里去。”老道士看過之后吩咐說。
幾個人手忙腳亂地扶著文心,送她到房間里。
這時候,劉城趕過來了,見此情景,不無擔心地說:“你姐心臟本來就不好,怎么還在靈房里哭?”
老道士說:“她是悲傷過度引起的,當然了,也沾了點邪祟。不礙事,等我做做法,讓她喝點符水,馬上就好了。”
聽老道士這么一說,眾人都讓老道士快點作法。老道士就搖著鈴鐺,口中念念有詞,一邊用朱砂筆在一張黃紙上畫了符,然后把那張符燒了,就著一點鹽,十幾顆大米,加了點開水,攪和一下,讓劉城伺候著給文心喝下。
不大一會兒,文心緩過一口氣,蘇醒了,眼睛卻還是有些呆滯。
“天,嚇死我了……”劉城心有余悸地說。
“好好休息吧,她的命理和靈房相沖,今天晚上別去靈房了,明天就好了。”
老道士說著,又畫了一張符,貼在文心房間的門上,這才收了鈴鐺離去。
見文心沒事了,大家也舒了一口氣,各自散去……
第二天一早,文水早早就起床了。今天要進很多菜,而且大部分是海鮮之類的貴重菜品,他必須親自過秤。
稱了一些菜和雞蛋,也收到一些廚房用的調(diào)料,卻沒有收到煙酒,問了,才知道阿三早就簽了單,直接送到房間里去了。
文水等了半天,不見送海鮮的過來上秤,心里狐疑,拐著腳來院子后面水井邊,只見幾個人正在收拾鮑魚。文水正想問個究竟,阿三從井邊走過來說:“這些東西我都驗收過了,讓他們下午過來驗單,收錢。”
“可我還沒有過秤呢……”文水說。
“放心吧,錯不了,都是老熟人。再說,我都稱過了。”
文水還想說什么,又覺得不妥,只好咂咂嘴離開了。
很快就到了中午,親戚朋友蜂擁而至。擺好桌子,眾人開始入席。文水拐著腳細細查看一遍,一共坐了十九桌,連小孩子們都上去了。這樣一來,一下子余了六桌出來。
此時,阿三顯得十分忙碌,正一桌桌地上煙酒和飲料。文水心里納悶,因為阿三說過,酒不必放在桌上,想喝的人,就自己到房間里來拿,這樣才不會浪費,可現(xiàn)在,怎么都擺桌子上了?正想問他,又覺得事情都已經(jīng)這樣了,再問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不一會兒,開始上菜,桌子上的酒,一瓶瓶地打開了。菜香酒香,一下子彌漫在老院子上空。
趁著客人吃飯的空當,文水趕緊整理一些單據(jù)。文成和秀蓮吃過飯,就要回深圳了,他們訂的是下午六點的動車票。
文水進了房間,發(fā)現(xiàn)大嫂也在。
“大嫂,你怎么沒去吃飯?”文水問。
“吃什么飯,沒那個心情……”大嫂說著,低頭劃著手機。
文水走近一看,見大嫂正鼓搗著計算器。一排排數(shù)字,時而隱去,時而出現(xiàn),在手機屏上跳躍著。
“我不止花了一萬,還有一些算不到的。反正我微信中的兩千多元,都沒了。”大嫂一邊劃手機,一邊抱怨。
“你要是記得住,就告訴我,寫個單子,我給你報銷。”文水安慰著大嫂。
“我就是吃了不識字的虧,能寫什么單子?這不是小事。他們拍拍屁股一走,往后的事情,都得我應付了。他們還說什么我們出多少,其余的他們?nèi)恕5昧撕锰庍€賣乖。”大嫂一臉的憤憤不平。
文水知道大嫂的意思,村里的紅白喜事,都是大嫂在應付。大姐和自己都在城里,文成一家在深圳,哪里顧得了村里事兒?就算聽說了,也是鞭長莫及。
“大嫂你也別急,待會兒算賬的時候,我會幫你留意,讓文成留下兩千元給你。至于說以后應付人情的事兒,我也跟大伙說說,我們留點錢給你。”
文水說著,趕緊整理單據(jù)。
大嫂“唉”的一聲,算是勉強認可了文水的意見。
9
正餐用過以后,各路要賬的都來了。租桌椅的,搭鐵棚子的,賣豬肉的……文水和文成媳婦一起,一個對賬,一個付錢,票子流水一般地出去了。
文水一看豬肉單子,竟然一萬六千多元;再有就是送來的海鮮,這是一筆最大的支出,將近三萬元;還有就是煙酒,香煙一共用了一百五十條,酒更不用說了,因為酒瓶蓋上有掃碼兌獎,每個五元,喝不喝的,所有的酒瓶都被打開了……統(tǒng)計一下所有的支出,自母親出殯到功德結(jié)束,一共花了十三萬七千多元。
算好賬,支付了所有款項,時間已是下午四點了。文成和他媳婦收拾好行李,給大嫂留下三千元,匆忙地叫了出租車,趕往高鐵站去了。而文心和劉城,吃過飯也走了,說是家里忙,得回去照應。家里只留下文水兩口和大嫂,準備處理正餐留下來的剩菜。
這時候,阿三來了。
“今天剩下這么多菜,晚上叫那些幫忙的人過來吧,大家聚一聚,算是犒勞他們。反正你們也吃不完,留著倒掉也是浪費。再說了,你們都在外面,平時難得在家,這也算是跟大家聯(lián)絡一下感情,你們說呢?”阿三提議。
“行,你去安排吧。”聽阿三這么一說,文水兩口都表示贊成。
傍晚時分,在阿三的安排下,又擺了五桌。吃喝過后,眾人紛紛散去,順便把一些沒有吃完的剩菜,都端回了自己家里。
大約十點左右,大嫂忙完了,來到客廳里喝茶,看到文水還在鼓搗那些賬單,突然想起什么:“不對呀,不對,我想起來了,原先咱媽有九萬多元的土地補償款,那些錢扣除你大哥去世時的開銷,扣除媽這次住院,應該還有五萬多吧?這些錢可都在文成手里呢。”
聽大嫂這么一說,文水也想起來了。當初修高速公路,占了村里的地,每家都有補償款。母親不識字,這些錢都由文成代管。文水早就分家出來,不好向母親過問此事。如今大嫂把這事提出來了,文水如夢初醒。
文水和大嫂正在激烈討論中,他媳婦也走了進來,也參與了討論。
“還不止這些錢呢,媽活著的時候,咱們逢年過節(jié)給她的錢,媽都沒怎么花,這么多年了,媽這些錢,應該有好幾萬吧?”
媳婦這么一說,文水也醒悟過來了。以前逢年過節(jié)文水給母親紅包時,老人家總說她有錢,你經(jīng)濟條件不好,不用給了。這么說來,母親的錢,一定不少。可母親去世時,身上并沒有發(fā)現(xiàn)一分錢。這些錢哪去了?母親最后的日子,都是大姐文心和姐夫劉城在照顧啊。
“還別說,文心為什么一下子出了那么多錢,還不是咱媽的錢?她倒會做人,用媽的錢,買了自己的面子,又落下好名聲,這可真劃算。村子里誰不知道她出了四萬?”大嫂補充說。
大嫂這么一說,立即得到文水兩口的響應。
“其實,吃虧的就是咱兩家。老人家這場功德,文成幾乎不用花一分錢,還帶了那么多東西回深圳。而大姐作為女兒,老人所有的錢,不是她拿了還能是誰?雖然事情都過去了,都是自家兄弟姐妹,說多了傷感情,可再怎么說,親是親,財帛分,吃虧占便宜說到明處,也不能是一本糊涂賬啊……”文水媳婦憤憤不平。
“人在做,天在看。你看文心,怎么突然間不省人事了?叫我說,這是……”
“大嫂你別說了。”文水趕緊擺手,不讓大嫂說下去。
大嫂“騰”的一下從椅子上跳起來:“為什么不說?他媽的就欺負我這個不識字的,我早就知道這事不地道,文心和文成還要咱兩家出了三萬塊錢,他們倒是賺了不少錢。死了一個媽,什么好處都是他們的。還裝什么好人,像個慈善家那么出手大方。這事不能就這么完了,找時間我得跟他們說道說道。文水你也別沉默了,誰也不想得罪,什么事情都吞進肚子里。這不,吃大虧了吧?”
文水想糾正大嫂,卻不知道說什么好。
大嫂還在憤憤不平,文水媳婦也在附和著大嫂,最后,又把話題轉(zhuǎn)移到母親這場功德上。
“沒想到做一場功德要花那么多錢,聽說有的人家才花七八萬,就很風光了。現(xiàn)在倒好,一下子花了十幾萬。”說到這里,大嫂的聲音小了些,“如今阿三管這事,想省也省不了了。可是,誰家沒有老人?誰家也躲不過這事。就說他自己,也總有死的那一天,就不怕遭報應?總有一天,他那只左眼,也會瞎了……”
“這事不好議論,村里的風俗就是這樣,誰也改變不了。咱們還是少說為好。”
文水不想讓事態(tài)進一步激化,畢竟事情都已經(jīng)過去了,細究起來,難免傷了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不管怎么說,媽的事情算是圓滿了,這是功德圓滿的事兒。至于說誰吃虧誰占了便宜,也沒什么好計較的。天底下沒有一桿公平秤,能足斤足兩稱出誰的良心來。所有的一切,媽知道……”
又對大嫂說了很多感謝的話,說家里的事以后還得靠大嫂照應,長嫂為母,如今母親不在了,大家肯定都會尊重大嫂的。
看看時間不早,文水給媳婦使了個眼色。
媳婦趕緊起身,說累了好幾天,大嫂也早點休息吧。
文水和媳婦從大嫂屋里出來,一抬頭,天上的月亮缺了一塊,夜風吹過,月亮顫抖著,像要掉下來的樣子。一片烏云從遠處移過來,可憐的月亮,像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兒,被悄悄地遮住了臉面。
責任編輯 申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