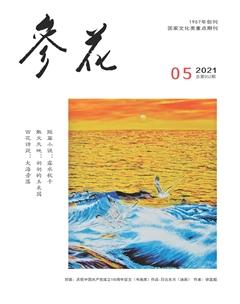紅土地上的詩人
“我用鋤頭在大地上寫下了無數的詩行”,每當我想起這句詩,父親的身影便在眼前了。
二〇一七年春節,我回老家陪父親過節。那天,我站在父親面前,端詳他那被歲月的犁鏵勾勒得蒼老的容顏,想起他經歷的滄桑,走過的人生,我終于無法控制內心的澎湃,淚流滿面。
我常用“紅土地上的詩人”來形容父親,來渲染他對于我在文學創作上的深遠影響。然而,我不得不承認,父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我在孩提時,父親被村里推薦為小學民辦教師。那時教學樓是清一色的泥磚屋。下雨天,晦濕滯氣得叫人難受,大熱天在那里上課卻又烘得人喘不過氣來。父親獨挑“三級”擔子——負責小學一至三年級的課程。每天上完課,父親都口干舌燥,疲憊不堪。母親常勸他:“如果太辛苦,就別干了!”但父親一直無怨無悔。
后來,三弟出生不久,父親就被組織辭退回家務農了。自此以后,每天父親都踏著露珠而出,披星戴月而歸。吃了晚飯后,父親總在燈下讀書,有時讀文學名著,有時讀歷史典故,但大多是讀有關種菜的書籍。還記得有一次,我半夜醒來,看到父親伏在案上寫著他的種田日記。這個晚上,緊皺的眉頭,微白的頭發,舞動的筆頭,成了父親的特寫鏡頭。天道酬勤,父親很快就成了方圓十里的種田能手。父親就這樣靠著一雙長滿老繭的大手操持著我家貧窮的生活,勒緊褲帶供我們四兄妹讀書,父親曾說過:“人的一生要靠奮斗,只有奮斗,才能成功。”這也是父親的真實寫照。我忘不了,多少個晨雞初鳴的時刻,父親悄悄地起床,在暈黃的燈光下掇菜,洗菜,然后裝菜上車,第一個沖破黎明前的黑暗,徑往十幾公里遠的集市;我忘不了,多少個夜幕降臨的時刻,我們兄妹四人站在村邊的小路旁,守候著父親回來的身影,靜待著那熟悉的車鈴聲,盼望著父親從城里帶回來的小吃;我忘不了,多少次莘莘學子回校的時刻,父親帶著殷切的期望送我們去學校念書,從口袋里摸出一疊面值很小的人民幣,臉上顯出轉瞬即逝的一絲尷尬。
父親雖忙,但他從不忘教給我們許多人生哲理;父親話很少,但他說出的話都很有分量。每當夜幕初降的時候,我們全家人都會圍坐在飯桌邊進餐。這個時候,父親就像一位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圣賢。很小的時候,父親無數遍地講“孔融讓梨”的故事,讓我們學會待人接物。再大一點,父親會奉送我們許多名言警句,他還經常給我們講《史記》《資治通鑒》里的歷史故事。在這良好的文化熏陶下,我們兄妹四人如沐春風、如浴春雨般茁壯成長。大哥十七歲就考上了名牌大學,畢業后成為一名高級工程師,而我大學畢業后成為一名人民教師,分配到廉江某中學任教語文,三弟和四妹也分別靠一技之長在社會上站穩了腳跟,這些都得益于父親的教導。如果說父親是一位紅土地上的偉大詩人,那么我們四兄妹應該算是父親用畢生心血抒寫的壯麗詩篇吧!
父親不但教子有方,還心地善良,樂于助人。因此,每個向他請教種菜技術的人,總會滿載而歸。有些人笑我父親太傻,不會“留一手”,父親聽了總會憨厚地笑著。
這些年來,父親就這樣走過,回望六十六年的風雨歷程,父親何嘗不感慨生命之匆匆?!或許,地曠人靜時,父親會抓起一把紅土,默看,兩行濁淚無聲地肆意滑落,滴在他幾十年來用鋤頭抒寫的詩行里。
紅土,依然如昔。
作者簡介:劉偉雄,筆名善道,系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華夏散文》《文學百花苑》《湛江日報》《南方日報》等報刊。
(責任編輯 王瑞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