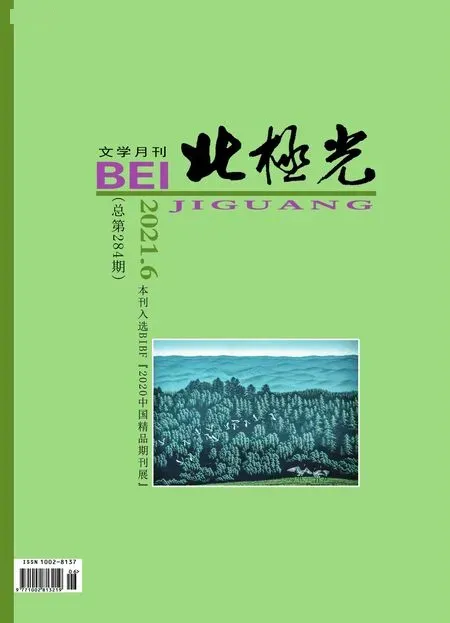幕后故事
□魏春橋 申志遠(yuǎn)
一
記者譚飛是雪城衛(wèi)視的一名普通記者。說(shuō)他普通有時(shí)也冤枉他,上到省里領(lǐng)導(dǎo)下到街道辦事處主任,鄉(xiāng)長(zhǎng)鎮(zhèn)長(zhǎng)他都熟,用咱這一句普通的嗑,那就是“好使”。譚大記者在一般情況下確實(shí)是比較好使的。不過(guò)這也不能就說(shuō)他厲害,這個(gè)地方臺(tái)雖然不大,但像譚大記者這樣的,倒有五六百之多。
這次江岸市的采訪本來(lái)沒(méi)有譚飛什么事情,孫曉剛主任和譚飛的私人關(guān)系不錯(cuò),總在一起洗洗澡喝喝酒什么的,聽譚飛主動(dòng)要求去江岸市采訪,先是一愣,隨即笑嘻嘻地開了句玩笑:“注意身體呀,要不我再給你配上一個(gè)年輕的小姑娘?”
譚飛的嘴在新聞部是出了名的損,一般的人他是絕對(duì)不慣菜的,不過(guò)眼前是孫曉剛,只是輕輕地?zé)o關(guān)痛癢地回?fù)袅艘痪洌洼p手輕腳地離開了。畢竟領(lǐng)導(dǎo)還是領(lǐng)導(dǎo),可以開玩笑,可以喝酒,也可以一起洗澡捏腳,但在人多的時(shí)候,尤其是在人前,面子還是要是給足的。當(dāng)然,小姑娘最終也帶上了,年輕的剛到電視臺(tái)實(shí)習(xí)的記者,帶上就帶上吧,還能幫忙干點(diǎn)活兒。
面子也是記者的特點(diǎn)之一,給別人辦事,或者找別人辦事,都是面子上的事情。比如說(shuō)現(xiàn)在上火車,進(jìn)站,都得有點(diǎn)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進(jìn)站上火車必須要走軟席,車上要進(jìn)軟臥。盡管在實(shí)際生活中真的沒(méi)有任何人能準(zhǔn)確說(shuō)出記者應(yīng)該在什么樣的車廂里乘車。
在軟臥車廂里,譚飛摸出一包大福,遞給攝像小楊一支,“攝像在電視臺(tái)還是比較牛的,好好干吧,以后什么也缺不了。”
攝像小楊是新招聘來(lái)的,“再好也不如譚哥你呀。”小楊陪著笑臉。
“這回讓你拼個(gè)三百五百不成問(wèn)題,和你譚哥出來(lái),干啥都吃不了虧。”譚飛邊說(shuō)話邊悠悠地吐了一口煙,不大的軟席間里馬上充滿了大福香煙的味道。一起來(lái)的實(shí)習(xí)女記者輕輕地咳了兩聲。這兩聲咳嗽提醒了譚飛,從上鋪探出頭去,看了一眼隨行的女記者,眼光重點(diǎn)落在了女記者的胸部,平平的,譚飛不由自主地?fù)u了搖頭。
“譚老師,‘拼’是什么意思?”女記者天真樣地問(wèn)了一句。
“拼縫”也是這個(gè)北方電視臺(tái)專有的名詞,在這個(gè)電視臺(tái),有兩種人被認(rèn)為是有本事的人,一是干活特厲害的,每年都能拿一兩個(gè)國(guó)內(nèi)大獎(jiǎng)的;另一個(gè)就是和“拼縫”這個(gè)詞有關(guān)系的,能拼縫的,掙到大錢的。當(dāng)然,這兩種不是什么人都能達(dá)到的境界。在這個(gè)地方臺(tái)的新聞部一百多號(hào)人之中,這兩種人也沒(méi)幾個(gè)。不過(guò)這番話譚飛并沒(méi)有對(duì)女實(shí)習(xí)生講,有些事情,就得自己去思索琢磨,尤其在電視臺(tái)這種地方。
所以譚飛笑著又搖了搖頭,“慢慢就懂了。”
“是嗎,譚老師?”女記者突然站了起來(lái),譚飛的眼睛也跟著她的胸部移了上來(lái)。
“譚老師,你和我說(shuō)說(shuō)不行嗎?”說(shuō)話時(shí),胸部使勁地往上挺了挺,她這動(dòng)作讓譚飛忽然記起上次在恒道市采訪時(shí),采訪對(duì)象招待他去玩的時(shí)候見到的那個(gè)小姐,譚飛不由得輕笑了一下。
火車很快就過(guò)了油城,譚飛看著窗外飛馳的景物,覺得有點(diǎn)晃眼,又抽出一支大福,點(diǎn)上了。
就在這時(shí),軟席包間的房門突然被人給拉開了,氣勢(shì)洶洶的女列車員沖了進(jìn)來(lái),“把煙掐了,自不自覺,誰(shuí)讓你抽煙了?”
譚飛知道,這不是剛才領(lǐng)他進(jìn)軟席包間的那個(gè)列車員,否則他們對(duì)記者多多少少還是要照顧的。于是譚飛掐滅嘴里叼著的煙,“不要那么兇嗎?”邊說(shuō)話邊探出頭去,計(jì)劃著和這個(gè)列車員開幾句玩笑,然后借機(jī)亮一下自己的身份,既給了別人面子同時(shí)自己又找回了面子,譚飛對(duì)自己做這種事情還是比較有把握的。然而他一探頭卻愣住了,首先一對(duì)大乳房強(qiáng)烈地刺激了他的眼睛,其次,列車員的臉蛋和他上次在恒道市見過(guò)的小姐出奇得相似。
“看什么看。”列車員扯開嗓門又喊了一句,然后一挺胸,兩個(gè)乳房劃過(guò)一道優(yōu)美的弧線,走了。
軟席間的空調(diào)已經(jīng)開得很大了,不過(guò)譚飛仍然感到自己在出汗,肯定是她,錯(cuò)不了,這弧線,他太熟悉了。
那是譚飛的第一次,是他第一次以這種方式來(lái)接觸女人。
那天去恒道市采訪。下車,喝酒,然后就是洗澡。譚飛跟著一個(gè)老記過(guò)去的。當(dāng)時(shí)安排譚飛去洗澡的時(shí)候,譚飛還開了一個(gè)玩笑,“怎么了,恒道市的人這么愛干凈,我們來(lái)了就嫌我們臟,非讓我們洗澡。”
老記只是那種看破了世事的樣子,呵呵一樂(lè)。譚飛現(xiàn)在想起自己當(dāng)時(shí)的狀態(tài),覺得那時(shí)候自己好二,簡(jiǎn)直就是個(gè)傻子。
洗完澡,老記和一起來(lái)的老攝像消失了。譚飛自己一個(gè)人從洗澡間里出來(lái),找不到自己人,看著滿大廳白晃晃的肉、濃妝艷抹的女人,嗅著臭腳丫子和脂粉的混和氣味,譚飛有些頭暈。還好,很快就有服務(wù)員過(guò)來(lái),很熟練地把譚飛帶到了一個(gè)單間。譚飛一邊走一邊問(wèn)剛才一起來(lái)的幾個(gè)人哪里去了,服務(wù)員只是詭異地一笑。進(jìn)了單間,譚飛馬上打開了電視機(jī)。這也是一個(gè)電視記者的習(xí)慣行為,可以不喝酒,不洗澡,但是不看電視是很難想象的。畢竟,這是衣食飯碗,要端好。而且很快就有他喜歡的《新聞?wù){(diào)查》,譚飛覺得這個(gè)節(jié)目特棒,大學(xué)畢業(yè)時(shí)譚飛就想進(jìn)中央電視臺(tái)這個(gè)節(jié)目組,可惜那時(shí)候中央臺(tái)全是招聘的,不想干。
譚飛現(xiàn)在似乎還記得,自己當(dāng)時(shí)對(duì)這個(gè)單間很滿意,洗完澡,能有個(gè)單間休息,舒服多了。但是讓譚飛吃驚的是,就在譚飛脫了睡衣,準(zhǔn)備舒舒服服看電視的時(shí)候,門突然開了,跟著服務(wù)員走進(jìn)來(lái)了一群女人,譚飛懵了,難道這就是平時(shí)他們說(shuō)的那個(gè)?
服務(wù)員讓譚飛選一個(gè)的時(shí)候,譚飛還處在發(fā)蒙的狀態(tài),只聽女人堆里一個(gè)尖聲尖氣的聲音說(shuō)道:“小紅到現(xiàn)在還沒(méi)客人,留給她吧。”
等譚飛再抬頭的時(shí)候,只有一個(gè)女人留了下來(lái),服裝惡俗,但是胸前的兩堆肉很是扎眼。大學(xué)時(shí)候譚飛也見過(guò)女朋友的同一部位,不過(guò)和這個(gè)比較起來(lái),就是桔子和排球了。
二
誰(shuí)都有自己的過(guò)去,列車員李彤同樣也無(wú)法回避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李彤對(duì)自己的第一次記得非常清楚。當(dāng)然不是說(shuō)她第一次和別人上床了。她有過(guò)男朋友,小伙子各方面都不錯(cuò),兩人在一起摸索著把男女之間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小伙子說(shuō)要結(jié)婚,李彤想了很久,就是沒(méi)有同意,別人問(wèn)她為什么?李彤當(dāng)時(shí)說(shuō)不清楚,不過(guò)后來(lái)她想明白了,她其實(shí)是不想重復(fù)過(guò)父母那樣的生活。
李彤的第一次是指她第一次出來(lái)做,在李彤她們那個(gè)群體里面,“做”是一個(gè)很有意思的詞。那天李彤碰到了一個(gè)雛兒,盡管李彤是第一次出來(lái)做,但是那個(gè)人似乎比李彤還緊張。李彤后來(lái)還經(jīng)常回憶起那個(gè)晚上,后來(lái)李彤很快就不再做了,因?yàn)樗吹搅撕芏嗨ε碌臇|西,疾病、警察,而且李彤發(fā)現(xiàn)自己的長(zhǎng)相其實(shí)就是一筆很大的財(cái)富。
但是今天,李彤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動(dòng)。而且還有些喘不過(guò)氣來(lái)。到了列車員車廂后,忙把自己胸衣帶子給解開了,每次喘不過(guò)氣的時(shí)候,李彤都習(xí)慣解胸衣的帶子。
剛才軟席包廂里那個(gè)抽煙的男人,似乎就是自己第一次出來(lái)做遇到的男人。不管怎么說(shuō),那也是自己后來(lái)總會(huì)想起的人。而且李彤有些害怕,這趟列車的乘警長(zhǎng)對(duì)自己已經(jīng)暗示過(guò)很多次了,也給她買了好幾件衣服和皮夾克。可萬(wàn)一,呵呵,想到這里,李彤不禁笑了,覺得自己很有意思,自己不說(shuō),乘警長(zhǎng)永遠(yuǎn)也不會(huì)知道這個(gè)事情,皮夾克也就不會(huì)消失,而且那個(gè)小子看現(xiàn)在的樣子,怕是早已經(jīng)把自己忘了。
李彤馬上覺得呼吸輕松了許多,不知道是胸罩帶的原因,還是自己理順了關(guān)系,而且不由自主地輕輕哼了兩句自己也不知道從哪里學(xué)的歌。乘警長(zhǎng)倒是被歌聲吸引了。人沒(méi)到一股熱氣先到了,隨后就是手過(guò)來(lái)了,一把抓到了李彤胸前的肉,李彤一把打過(guò)去。乘警長(zhǎng)呵呵一樂(lè),小聲嘀咕一句:“怎么是空檔呀?”
李彤這時(shí)忽然覺得乘警長(zhǎng)老陳的那張小臉安在了一個(gè)大大的身子上面很滑稽,和剛才的那個(gè)男人一比簡(jiǎn)直就是個(gè)小丑,不由得笑了一聲。乘警長(zhǎng)老陳似乎是得到暗示似的,又抓了一把,這下李彤不高興了,用力給了老陳的胖手一巴掌,并且迅速起身,向外走去。
列車的軟臥車廂里閑置的空鋪很多。李彤找了個(gè)包廂,拉開了門,李彤可能沒(méi)有注意到里面竟然有人,自己胸前的兩坨子肉正顫顫巍巍地對(duì)著那個(gè)男人的臉。這時(shí)候雖然已經(jīng)到了北方的初秋,可是這幾天的天氣有些怪異,溫度不降反升,這樣的天氣,誰(shuí)也不可能穿的很多,李彤也不例外。
三
乘警這個(gè)職業(yè),假如沒(méi)有這個(gè)“乘”字,那還是個(gè)不錯(cuò)的行當(dāng)。警察嗎,不管是誰(shuí)都要給點(diǎn)兒面子,可是一旦沾上了“乘”,就差多了,明白你身份的,下了火車,根本就不給你面子。
乘警老陳為拿下李彤還真是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地花了不少銀子。只是一件皮夾克就削去了800元,老陳也一直在尋思,回家怎么向老婆交差。剛才老陳在車上逛了好幾圈,看能不能尋摸到想補(bǔ)臥鋪票的人,好把自己手里的兩張票給打發(fā)出去,掙個(gè)百八十的,可惜的是一無(wú)所獲,反倒是看見李彤在發(fā)呆。
李彤對(duì)自己含情脈脈地看了一眼之后,起身扭扭捏捏地朝軟臥車廂走去。老陳對(duì)著李彤列車服里扭來(lái)扭去的屁股尋思了半天,莫不是李彤在暗示自己過(guò)去,不禁呵呵一樂(lè),哼著小曲,起身也往軟臥車廂去了。
剛到一個(gè)車廂門口,忽然聽到李彤大喊:“你這不是耍流氓嗎?!”
老陳怒了。“老子喂了半天的魚讓別人給釣走了。”老陳有些生氣,但是沒(méi)有發(fā)作,老陳輕輕地挪動(dòng)腳步走開了。
恰在這時(shí)候里面的聲音伴著老陳的腳步聲又大了起來(lái),老陳心口有些堵得慌,李彤雖然不是自己的老婆,但畢竟自己喂了這么長(zhǎng)時(shí)間了,那個(gè)小子這不是給我上眼藥嗎?他奶奶的,我就是要看看,究竟是誰(shuí)呀,這么不給我面子!
這個(gè)時(shí)候,老陳做了一個(gè)決定,這個(gè)決定后來(lái)影響了很多人,但老陳當(dāng)時(shí)是絕對(duì)沒(méi)想到的。
打開門,老陳愣住了,李彤的工作服扣子已經(jīng)完全被解開了。男人的手還停留在她的胸前,李彤這個(gè)時(shí)候突然對(duì)老陳大聲叫道:“乘警,這個(gè)人對(duì)我耍流氓!”
老陳的血馬上就涌到了腦門。這個(gè)時(shí)候,列車已經(jīng)駛?cè)肓艘煌麩o(wú)際的草原,油城以北往恒道市方向,有那么一片草場(chǎng),雖然沒(méi)有內(nèi)蒙的草場(chǎng)那樣豐美,但是還是有些草原的調(diào)調(diào)的。老陳小時(shí)候就是長(zhǎng)在這片草原上的,后來(lái)當(dāng)兵去了江岸市,就留在了江岸市的鐵路公安部門。
老陳已經(jīng)很久沒(méi)有用過(guò)手槍了,其實(shí)這一次老陳也沒(méi)必要用槍,但老陳覺得不用槍就不能展現(xiàn)出自己的英雄氣概。
老陳注意到,李彤先是過(guò)來(lái)拉自己的手,可是馬上就趴在自己身上哭了起來(lái),嘴里還喊著:“他耍流氓,讓我怎么活呀。”
兩駝子肉就在老陳的后背上蹭來(lái)蹭去,弄的老陳沒(méi)有辦法,回頭輕輕地拍了拍李彤的腦袋,被槍指住了腦袋的人似乎也緩過(guò)來(lái)了,馬上叫了起來(lái):“你是做什么的!我們?cè)谡剳賽邸!?/p>
或許是老陳的動(dòng)靜太大引來(lái)了很多人圍觀,這個(gè)時(shí)候一個(gè)女孩子怯生生地對(duì)老陳說(shuō):“這是我們單位的譚老師,我們是省電視臺(tái)的,我們老師怎么了?”
“對(duì),我就是省電視臺(tái)的記者譚飛,你這是干嗎?我犯什么罪了,我要找你們領(lǐng)導(dǎo)。”
老陳一聽也有些害怕了,“記者要是和李彤調(diào)個(gè)情,這樣可是麻煩大了,再說(shuō)李彤本身也不是什么好貨!”老陳在自己心里暗暗盤算著厲害關(guān)系,但是李彤的一句話,提醒了老陳,就憑李彤這句話,這個(gè)所謂的記者能夠被判刑。
因?yàn)樵谶@個(gè)時(shí)候,李彤尖叫到:“我根本不認(rèn)識(shí)他,他在調(diào)戲我,我剛進(jìn)來(lái)他就摸我。”
火車這個(gè)時(shí)候已經(jīng)過(guò)了煙筒屯,離恒道市越來(lái)越近了。飄飛的秋葉一片片被呼嘯的火車卷了起來(lái),輕輕地打在玻璃窗上。這個(gè)時(shí)候,多年的警察經(jīng)歷幫助了老陳,老陳決定,不管怎么說(shuō),銬上這個(gè)記者,停車的時(shí)候把他留在恒道市的鐵路公安處,自己則一走了之。日后,即便這個(gè)記者有什么報(bào)復(fù)的招數(shù),也找不到自己頭上。
火車到恒道市,老陳把那個(gè)自稱是省電視臺(tái)的倒霉鬼交給了鐵路公安處。
天漸漸的黑了,老陳自己溜進(jìn)了一間包廂睡覺。這個(gè)時(shí)候李彤進(jìn)來(lái)了,一把抱住了老陳,不過(guò)就在褲子已經(jīng)褪下去半截的時(shí)候,老陳突然問(wèn)了一句“剛才是怎么回事了?”
“沒(méi)怎么,就是他耍流氓!”
“不會(huì)吧。”
“就是!”李彤很堅(jiān)定地說(shuō)!
“那他可能要被判刑的。”
李彤聽到老陳的這句話,似乎沉思了一下,然后語(yǔ)氣堅(jiān)定地說(shuō):“那個(gè)記者就是在耍流氓,還說(shuō)他和我處對(duì)象了,他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處的對(duì)象?”
老陳就沒(méi)有再問(wèn),隨即把褲腰帶上的槍拿了下來(lái),放到了鋪上面。
李彤卻重重地嘆了口氣,把自己放平了,躺在了鋪上。老陳盡管不明白李彤的嘆氣緣何而起,但是李彤這個(gè)動(dòng)作的含意老陳卻是十分明白的。
四
實(shí)習(xí)女記者的電話讓孫曉剛大吃一驚。這時(shí)候?qū)O曉剛正在福成肥牛吃晚飯。福成是孫曉剛比較喜歡的一個(gè)地方,關(guān)鍵原因就是它的汁調(diào)的有味道。總來(lái)這家店,時(shí)間長(zhǎng)了老板也能察覺出孫主任的威風(fēng),人前人后有時(shí)也照顧一下,贈(zèng)個(gè)果盤什么的。
譚飛在新聞部也算是能人,怎么會(huì)被警察抓起來(lái)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詳細(xì)情況這個(gè)實(shí)習(xí)生還說(shuō)不清楚,孫曉剛有些著急了。
放下電話后,孫曉剛先給恒道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老白打了個(gè)電話。恒道市公安局這回因?yàn)榇蚝诘氖虑閼K了,很多領(lǐng)導(dǎo)人人自危,刑警隊(duì)、紀(jì)檢等部門的一些領(lǐng)導(dǎo)還進(jìn)去了。不過(guò)老白平時(shí)就看不慣涉黑的做派,這回他榮升政治部一把了。和老白說(shuō)清楚了情況,孫曉剛又撥了牛臺(tái)長(zhǎng)的電話,想和牛臺(tái)長(zhǎng)匯報(bào)一下,撥完了號(hào)碼,孫曉剛又把手機(jī)合上了,算了,先不說(shuō)為好。
就在這個(gè)時(shí)候,孫曉剛的手機(jī)響了,拿起來(lái)一看,是林雪,譚飛的老婆,原來(lái)電視臺(tái)新聞節(jié)目主持人,后來(lái)辭職走了,自己開了個(gè)廣告公司。電話一接通,林雪的聲音就不客氣地傳了過(guò)來(lái):“他怎么了,出什么問(wèn)題了?”
孫曉剛不敢接林雪的話茬,便岔開話:“我和幾個(gè)朋友在外面吃飯呢,要不你也過(guò)來(lái)。”原先林雪在新聞部的時(shí)候,和孫曉剛有過(guò)那么幾次,后來(lái)離開電視臺(tái)了,關(guān)系也就隨之終結(jié)了。自從和他的下屬譚飛結(jié)婚之后,雖然有幾次單獨(dú)相處的機(jī)會(huì),但是都做出一副柳下惠的樣子,這也是必須的,現(xiàn)在這個(gè)社會(huì),什么事情都得留個(gè)心眼呀,而且孫曉剛眼看著就是電視臺(tái)副臺(tái)長(zhǎng)了,絕不能讓一個(gè)女人輕易毀了自己的前程。
但是林雪根本不理會(huì)孫曉剛甩過(guò)來(lái)的話頭:“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告訴我,要不要我和牛臺(tái)長(zhǎng)說(shuō)一聲?”
孫曉剛聽到這句話有些不高興了。一直有人在傳林雪可能和牛臺(tái)長(zhǎng)有一腿,看樣子,謠傳也不一定都是沒(méi)影的事,但是孫曉剛畢竟是孫曉剛,依舊是一副公事公辦的口吻:“說(shuō)也行,不說(shuō)也行,我們也正準(zhǔn)備去恒道市看看怎么回事。”
街上,華燈處上。雪城最近幾年在搞街道建設(shè),弄得非常漂亮。車?yán)铮瑢O曉剛想了想,決定還是明天早上去恒道市,突然手機(jī)響了,一看是牛臺(tái)長(zhǎng)的號(hào)碼,牛臺(tái)長(zhǎng)則是一副非常隨意的口吻,好像只是無(wú)意中聽說(shuō)譚飛的事情,孫曉剛只好把自己了解的情況說(shuō)了一遍。
車快到家門口的時(shí)候,孫曉剛品出來(lái)牛臺(tái)長(zhǎng)電話的意思了,就是要孫曉剛馬上把這個(gè)事情處理完。譚飛決定現(xiàn)在就去恒道市。心里盤算了一下,誰(shuí)和恒道市以及鐵路的人熟悉,想好了人選,孫曉剛給辦公室去了一個(gè)電話,準(zhǔn)備連夜出發(fā)。
就在這時(shí)候,恒道市公安局老白的電話也打過(guò)來(lái)了。譚飛現(xiàn)在被扣在了恒道市鐵路公安處。扣押的原因是企圖強(qiáng)奸列車員,孫曉剛一聽這個(gè)說(shuō)法當(dāng)時(shí)就樂(lè)了。他手下的人和強(qiáng)奸絕對(duì)是扯不上邊的。老白在說(shuō)的時(shí)候語(yǔ)氣中也帶著笑意,告訴孫曉剛,他已經(jīng)和鐵路公安處的人打好了招呼,沒(méi)人會(huì)動(dòng)譚飛一下子。
不過(guò)老白接著告訴孫曉剛,因?yàn)樽T飛是涉嫌刑事犯罪被押進(jìn)來(lái)的,想要馬上出來(lái),怕得孫曉剛親自去一趟了。孫曉剛接過(guò)話茬告訴老白,他現(xiàn)在正在準(zhǔn)備連夜動(dòng)身了。
在鐵鋒區(qū)建華街的恒道市鐵路公安處辦公室,孫曉剛見到了譚飛,頭發(fā)蓬亂不堪,胡子也長(zhǎng)出來(lái)了,完全沒(méi)有平時(shí)那股瀟灑勁頭了。這副樣子,孫曉剛心里竟然有一絲絲的快意,孫曉剛馬上察覺出自己的不該,又一想為什么了?因?yàn)榱盅?/p>
“孫主任,我真是莫名其妙。在火車上我就和乘務(wù)員隨便說(shuō)了幾句話,結(jié)果就被抓起來(lái)了。”
“你別著急,我去和鐵路公安處的領(lǐng)導(dǎo)研究一下,看怎么辦。”孫曉剛這個(gè)時(shí)候也只能這么安慰譚飛。
這時(shí)老白已經(jīng)和公安處的領(lǐng)導(dǎo)老林溝通好了,決定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對(duì)公開耍流氓的省電視臺(tái)記者譚飛處以5000元的罰款。
孫曉剛和老林握了握手,然后說(shuō)了一句:“中午我在白鶴安排了一桌,一起去。”白鶴是恒道市鐵路這一片有名的一家飯店。
回雪城的車上,孫曉剛還比較清醒。譚飛雖然有些酒量,可能是由于頭一晚的驚嚇,狀態(tài)一直不好。孫曉剛問(wèn)起原因時(shí)候,譚飛依然還是那番話。孫曉剛也不想再追問(wèn)下去了。當(dāng)領(lǐng)導(dǎo),有的時(shí)候,你就得學(xué)會(huì)裝糊涂。
五
站在鏡子前發(fā)了半天呆。衣服穿上了一套看了看,不滿意又脫下了,再找出另外一套,想了想,又脫了。
鏡子中的女人只穿了一套內(nèi)衣。林雪不由得想起自己大學(xué)時(shí)候也經(jīng)常這樣穿著內(nèi)衣在宿舍里走來(lái)走去,那時(shí)候往來(lái)的女生沒(méi)有不羨慕自己身材的。
譚飛打電話回來(lái)說(shuō),他已經(jīng)從恒道市開始往雪城趕,估計(jì)晚上7點(diǎn)到家,譚飛讓林雪準(zhǔn)備一下,晚上給新聞部的幾個(gè)同事接風(fēng),而且譚飛疲憊的話語(yǔ)中略帶著一絲感激的腔調(diào)說(shuō),孫曉剛也要參加。
多年來(lái),林雪一直在刻意回避孫曉剛,這也是林雪離開電視臺(tái)的最大原因。
明月酒樓前面車滿為患,一個(gè)肥頭大耳的男人正把頭探出奔馳車的窗外,厲聲呵斥給他找車位的保安。林雪看這個(gè)人似乎很面熟,忽然想起來(lái)了,這不就是以前電視臺(tái)臺(tái)長(zhǎng)張永峰的兒子張望朝嗎,林雪在電視臺(tái)上班的時(shí)候,張望朝雖然只是總編室的一個(gè)司機(jī),但是車?yán)锏拿琅畢s是隔三差五就要換一個(gè)。林雪也坐過(guò)張望朝的別克車,不過(guò)一次酒后,張望朝把林雪帶到江邊的融府康年酒店,在房間里林雪半是玩笑半認(rèn)真地告訴張望朝,她的好朋友是牛臺(tái)長(zhǎng)。牛臺(tái)長(zhǎng)那時(shí)候還是常務(wù)副臺(tái)長(zhǎng),但是張永峰要退休牛臺(tái)長(zhǎng)要接班的風(fēng)聲早已在全臺(tái)彌漫開來(lái)。也不知道是林雪的話起了作用還是張望朝良心發(fā)現(xiàn),那次盡管林雪喝多了,卻仍然是全身而退,而且以后張望朝再也沒(méi)有用他的車?yán)^(guò)林雪。
順著電梯上了五樓,酒店的包房里空無(wú)一人。譚飛和孫曉剛他們還沒(méi)有到,林雪先去了洗手間。從洗手間出來(lái)突然有人叫林雪的名字,林雪一愣,聽聲音似乎是牛臺(tái)長(zhǎng)。
“小林呀,譚飛回來(lái)了嗎?”牛臺(tái)長(zhǎng)一邊說(shuō)話一邊把手伸了出來(lái)要和林雪握手。
“哦,牛臺(tái)長(zhǎng),還沒(méi)有,一會(huì)兒到。”
兩只手握在了一起,林雪感覺到牛臺(tái)長(zhǎng)的手依舊是那么溫?zé)幔盅┧南驴戳丝矗唤f(shuō)了句;“我要是不給你打電話,你是不是永遠(yuǎn)不會(huì)給我打電話?”
牛臺(tái)長(zhǎng)沒(méi)有接話茬:“只是自顧自地說(shuō),我今天宴請(qǐng)我們的老領(lǐng)導(dǎo)張永峰臺(tái)長(zhǎng),過(guò)兩天他就要去美國(guó)了。”突然放了林雪的手對(duì)著林雪的身后接著說(shuō):“來(lái)來(lái),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張臺(tái)。”
“哈哈,林雪你就不用介紹了,我們臺(tái)的當(dāng)家花旦,全雪城人民都認(rèn)識(shí)。”
林雪忙把手伸了過(guò)去。
“多好的人才呀,我要是還在電視臺(tái),就不能讓她走,老牛,這就是你的不對(duì)了。”張永峰握住林雪的手但卻把臉沖向牛臺(tái)長(zhǎng)。
吃飯的時(shí)候譚飛似乎又恢復(fù)了一點(diǎn)往日風(fēng)采。至于為何在恒道市被抓起來(lái),只字不提,飯桌上也沒(méi)有不識(shí)相的人多問(wèn)一句。結(jié)賬的時(shí)候,林雪順便把牛臺(tái)長(zhǎng)那桌的單也買了。回家路上,林雪感覺到自己手機(jī)突然震了一下,明白是短信,但是林雪沒(méi)有立刻看,這也是林雪幾年來(lái)能夠和譚飛相處得平安無(wú)事的主要原因,不露一點(diǎn)破綻。
回家,在衛(wèi)生間里,林雪打開手機(jī)一看:“今晚在老地方等我。”林雪有些為難了,想了半天,出了衛(wèi)生間先換上了睡衣,和譚飛溫存了一下,突然,一副猛然省悟的樣子:“糟了,我的標(biāo)書還在王翻譯那里,我得去看看。”
林雪的生意做得越來(lái)越大,這個(gè)開發(fā)區(qū)最好地段的房子也是林雪買來(lái)的,所以譚飛對(duì)林雪生意上的事情一向非常支持。下樓林雪坐進(jìn)了車?yán)飼r(shí)候,突然覺得有些過(guò)意不去,譚飛畢竟從恒道市才回來(lái),怎么能這樣?但是林雪想到即將開始的電視臺(tái)黃金廣告時(shí)段的招標(biāo),咬了咬牙,發(fā)動(dòng)了車。
白色的本田雅閣慢慢駛出了小區(qū)的大門,直奔太平而去,那里有一所房子,是牛臺(tái)長(zhǎng)的,也是牛臺(tái)長(zhǎng)常說(shuō)的老地方。林雪沒(méi)有把車停在樓下,而是遠(yuǎn)遠(yuǎn)地停在一個(gè)飯店門口,然后走了過(guò)去。
進(jìn)門之前,林雪先關(guān)了手機(jī)……
林雪是被早上的太陽(yáng)給曬醒的,滿身是汗,決定先去洗個(gè)澡,然后回家。這個(gè)牛臺(tái)長(zhǎng),也不知道昨天吃了什么藥,一晚上竟然折騰了三次。
洗澡之前,林雪打開了手機(jī),手機(jī)關(guān)了,有時(shí)候甚至覺得失魂落魄的,好像少了什么東西似的。剛開沒(méi)有五分鐘,手機(jī)突然唱起歌來(lái)。林雪在浴室里沒(méi)有接,然而手機(jī)卻非常執(zhí)著地在唱著歌,簡(jiǎn)單地在身上裹了一個(gè)浴巾出來(lái),電話號(hào)碼有些熟悉,林雪懶得去想。拿起電話,里面的人問(wèn)道:“是林雪嗎?你老公今天早上被江岸市公安局來(lái)的一伙人給抓走了。”
“什么?”林雪有些愣住了,“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們也不知道,反正譚記者他被江岸市的警察抓走了。”
六
譚飛被銬在餐車?yán)锏臅r(shí)候,李彤連餐車的邊都沒(méi)敢沾。
但是譚飛在恒道市被押下火車的時(shí)候,李彤真的有些心酸,盡管李彤說(shuō)不清楚什么叫愛情,李彤總在幻想自己的愛情,愛情里的男主人公有很多次就是剛才被銬著雙手帶下火車的譚飛。
車長(zhǎng)特殊照顧,作為受害人的李彤不必再繼續(xù)值班,這也給了老陳機(jī)會(huì)。和老陳在軟臥車廂翻云覆雨的當(dāng)間,李彤總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了缺德事了。老陳雖然人長(zhǎng)的高高大大,但是有些事情卻十分不靈光。李彤還沒(méi)明白怎么回事,老陳就草草收兵了。
“你說(shuō)他會(huì)怎么樣?”李彤在老陳穿褲子的時(shí)候問(wèn)。
老陳以為李彤張嘴可能又是買什么衣服之類的,哪知道沒(méi)頭沒(méi)尾的甩出這樣一句話,“什么怎么樣?”
“就是剛才的那個(gè)戴眼鏡的記者。”
“假如強(qiáng)奸成立,判刑是肯定的了。”老陳把手伸到上鋪一邊摸槍一邊接著說(shuō):“不過(guò)你還要到恒道市作證,到時(shí)候我找臺(tái)車,送你過(guò)來(lái)。”
“哦,這樣。”李彤忽然覺得有些不舒服。
這時(shí)候火車已經(jīng)駛進(jìn)了濃濃的黑夜,看著窗外飛馳而過(guò)的燈火,李彤的心情一點(diǎn)點(diǎn)好起來(lái)。李彤就是這樣的一個(gè)人,很多事情很容易就忘記了。
從職工通道出站后,老陳一直跟在李彤后面。李彤拎著包,低著頭一直向前走。
“六哥,你怎么過(guò)來(lái)了。”老陳的大嗓門突然嚇了李彤一大跳。
李彤抬頭一看,原來(lái)是江岸市公安局刑警支隊(duì)的聯(lián)防隊(duì)員大六子。
“我媳婦回來(lái)了,我接她來(lái)了。”說(shuō)著,大六子上去一把摟住了李彤,“想我不?來(lái),親下!”
大六子原先是江岸市有名的社會(huì)混混,由于多次打架斗毆被抓進(jìn)公安局,結(jié)果一來(lái)二去時(shí)間一長(zhǎng),和公安局的人混熟了,反而成了聯(lián)防隊(duì)員,買了一個(gè)破吉普車,然后自作主張噴上了藍(lán)白道,掛上了警燈,儼然是一個(gè)警察模樣了。
李彤本來(lái)挺討厭大六子,但是由于老陳在后面跟著,反而覺得大六子有幾分可愛了,伸手在大六子的臉上輕輕打了一下,模仿電視臺(tái)的女主持人腔調(diào)說(shuō):“六哥,我餓了!”
“接你就是為了喝酒的,今天劉隊(duì)請(qǐng)客,讓我一定帶上你。”兩個(gè)人說(shuō)話時(shí),老陳有些手足無(wú)措,準(zhǔn)備要走,突然大六子對(duì)老陳說(shuō):“你也和我們一起喝酒去。”
老陳剛要推辭,大六子有些急了:“你這是什么警察,不敢喝酒。”
江岸市最近新開了不少啤酒廣場(chǎng),據(jù)說(shuō),這些都是從廣州學(xué)過(guò)來(lái)的,廣州那里老早就有這個(gè)東西了。李彤他們江岸鐵路分局最遠(yuǎn)的火車只能到北京,至于廣州的事情,李彤一點(diǎn)兒也不知道,所以不敢言語(yǔ)。
大六子、老陳、劉隊(duì)還有劉隊(duì)的司機(jī)小賈四個(gè)男人脫光了上身,每人手把一瓶酒,很快,一箱啤酒下去了。
李彤雖然只喝了兩瓶,可是難受異常,便起身要去廁所,大六子這個(gè)時(shí)候咋咋乎乎地喊道:“怎么了,媳婦,這點(diǎn)兒就不行了。”
“誰(shuí)是你媳婦,睜開狗眼瞧清楚了。”李彤也是有些喝多了,平時(shí)她還是比較害怕大六子的,倒不是大六子在社會(huì)上有多大的能耐,關(guān)鍵是大六子在她身上肯花錢。
啤酒廣場(chǎng)雖然十分嘈雜,但是李彤的一句話引來(lái)了周圍人的目光。李彤起身往廁所走時(shí),大六子一把拉住了李彤:“小娘們,給鼻子上臉。”
老陳忙過(guò)來(lái)勸架,老陳的酒量也是一般,舌頭已經(jīng)捋不直溜了,說(shuō):“別怪她,六哥,李彤在車上攤了一個(gè)案子。”
李彤雖然喝了一點(diǎn)兒酒,但是神志還清醒,一聽這話,心里“咯噔”一下,感覺有些不妙,連忙掙脫了大六子的手,說(shuō)了句:“我要去廁所。”
回來(lái)桌子上的氣氛就有些不對(duì)了。劉隊(duì)正在打電話,大六子和老陳在抽煙,李彤悄聲問(wèn)了句:“怎么了?”
大六子說(shuō):“怎么了!你讓人給辦了,結(jié)果那個(gè)小子讓恒道鐵路公安處給放了。”
老陳說(shuō):“他不是記者嗎,放了就放了吧,咱們喝酒。”
“我的女人!這樣就讓那小子走了,劉哥,你說(shuō)咋辦?”
劉隊(duì)放下電話慢條斯理地說(shuō):“我剛才向張力支隊(duì)長(zhǎng)匯報(bào)了,這個(gè)事情不能便宜那個(gè)小子。這是刑事案件,我們可以辦理。”
“他不是記者嗎?”老陳又嘀咕了一句,這次聲音有些小,但是仍舊走進(jìn)了大六子的耳朵。
“記者,記者怎么了。”大六子開始打電話聯(lián)系車了。
李彤的心情這個(gè)時(shí)候又開始低落起來(lái)。
“媳婦,你和我們一起去,要不我不認(rèn)識(shí)他,這樣的人怎么能說(shuō)放就放了。這是刑事案,要判刑的。”大六子仍舊在忿忿不平。
“對(duì),一起走,車一來(lái)我們就走。李彤也去。”劉隊(duì)跟著補(bǔ)充說(shuō)道。
李彤這個(gè)時(shí)候恍惚覺得自己還是不希望那個(gè)記者有什么事情發(fā)生,說(shuō)了句:“那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住呀?”
哈哈哈,除了老陳之外,三個(gè)男人同時(shí)笑了起來(lái)。
七
門鈴響的時(shí)候,譚飛正在生林雪的氣,自己剛剛虎口脫險(xiǎn),她就一夜未歸,實(shí)在不像話。本來(lái)準(zhǔn)備不管的,隨便它響去吧,但是這回門鈴異常執(zhí)著,譚飛有些厭煩,這個(gè)女人總是忘帶鑰匙,隨便裹了毯子就下了床,可視對(duì)講門鈴里面顯露出來(lái)的卻不是林雪那張臉,而是一個(gè)男人,由于離門太近的原因,有些變形,十分猙獰。
“誰(shuí)呀。”譚飛沒(méi)有好氣地問(wèn)。
“我,保安小呂,飛哥,電話局的人說(shuō)要檢查一下你家的線路。”
“我家電話沒(méi)有問(wèn)題,不用了。”
“不是,飛哥,就是檢查一下,您給開下門吧。”
譚飛雖然不樂(lè)意,還是按下了開門的鎖,順手把防盜門門閂也拉開了,然后甩掉毯子,找出了一件舊牛仔褲,運(yùn)動(dòng)服,套到了身上。
譚飛拉開門,門口除了小呂之外還有三個(gè)人,一女兩男。女的譚飛覺得十分面熟,一下子想不起來(lái),就在這時(shí),一個(gè)男人突然掏出槍,火車上的一幕重演了,黑洞洞的槍口對(duì)著譚飛,小呂則帶著一點(diǎn)驚慌和歉意躲在了邊上。譚飛的心猛地一下子沉到了底,壞了,有強(qiáng)盜,不過(guò)就在譚飛的目光落到了起伏不已的兩團(tuán)肉上的時(shí)候,譚飛想起來(lái)了,這不是那個(gè)列車員嗎,這是怎么回事。
“別動(dòng),我們是警察!”
“我的事不是完了嗎?”譚飛有些不解,不過(guò)這個(gè)時(shí)候譚飛倒不是十分害怕了。
“別說(shuō)話。”高個(gè)子男人給了譚飛一記響亮的耳光。
這時(shí)候,兩團(tuán)肉的主人叫了起來(lái):“六子,你干嘛?”
“別廢話,銬上,帶走。”高個(gè)子男人似乎是個(gè)領(lǐng)導(dǎo)。
4500吉普車飛速向江北駛?cè)ァWT飛被銬在車的后排坐上。從窗子看過(guò)去,譚飛覺得車是在走雪江公路,似乎是奔江岸方向去的。
譚飛動(dòng)了下身子,小心地說(shuō)了句:“同志,您是哪個(gè)單位的,您看,您是不是搞錯(cuò)了?”
“沒(méi)錯(cuò),你犯罪了,知道不!”大六子摸著譚飛的腦袋說(shuō)。動(dòng)作一開始十分輕柔,突然之間加力,把譚飛的腦袋向后一拉,譚飛只好面沖著車頂棚。大六子把臉貼上來(lái),酸臭味直沖譚飛的口腔噴來(lái):“我們抓的就是你。”
“大六子。”這時(shí)候劉隊(duì)喊了一句,大六子有些悻悻地放了譚飛。
這是譚飛24小時(shí)之內(nèi)第二次走進(jìn)了公安局的大門,以前譚飛也走進(jìn)去過(guò),但是當(dāng)時(shí)都是作為上賓被請(qǐng)進(jìn)去的。這兩次卻是大大不同,尤其是這回,一進(jìn)了江岸市公安局刑警隊(duì),就被鎖在了一個(gè)大鐵椅上。
江岸的氣溫本來(lái)就要比雪城低很多。尤其是到了北方的秋天,晚上已經(jīng)開始下霜了,可憐的譚飛被從雪城帶到這里之后,就一直被銬在這個(gè)鐵椅子上,吃喝根本沒(méi)有,要是大小便什么的,必須要等到有人來(lái)了,然后由別人帶著去廁所。盡管譚飛一直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了,但是他隱隱約約的感覺到,還是和那個(gè)做過(guò)小姐的列車員有關(guān)。
6個(gè)小時(shí)過(guò)去了,譚飛一直企盼警察能過(guò)來(lái),他好說(shuō)明問(wèn)題,而且譚飛也更是十分盼著能夠見到江岸市公安局的李少周局長(zhǎng),譚飛以前采訪過(guò)他,當(dāng)時(shí)還一起喝了酒。
8小時(shí)過(guò)去了,天黑了。
12個(gè)小時(shí)過(guò)去了,譚飛就這樣在這個(gè)鐵椅子上沉沉睡去了。
天再亮的時(shí)候,譚飛全身已經(jīng)麻木了,這時(shí)候他除了想離開這個(gè)鐵椅子之外一點(diǎn)別的想法都沒(méi)有。
有人過(guò)來(lái)了,是把譚飛從雪城帶過(guò)來(lái)的劉隊(duì)。劉隊(duì)和顏悅色的和譚飛說(shuō):“我們就是想和你聊聊,問(wèn)你幾個(gè)問(wèn)題。”
譚飛突然之間受到這種待遇有點(diǎn)受寵若驚,忙說(shuō):“您說(shuō)。”
“你是怎么強(qiáng)奸列車員的?”
譚飛一下子愣住了。
劉隊(duì)點(diǎn)起一支煙,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吐出煙氣,說(shuō)了一句:“希望你能配合我,別給我們添麻煩,有些人不聽話,我們是要用些手段的。”
譚飛身上的汗下來(lái)了。
八
孫曉剛在上班路上接到牛臺(tái)長(zhǎng)的電話,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沒(méi)有起來(lái)。孫曉剛以為牛臺(tái)長(zhǎng)還要關(guān)心一下譚飛的情況,馬上匯報(bào)說(shuō):“我和小譚說(shuō)了,今天讓他在家休息,不用上班。”
“休息個(gè)屁,你連這個(gè)事情都辦不好,我看你的新聞部主任再做下去就沒(méi)什么意思了。”老頭子莫名其妙地發(fā)起火來(lái),一下子讓這位新聞部的一把手有些摸不著頭腦。而且就這么說(shuō)了兩句就把電話掛了。
孫曉剛一想,是不是和譚飛有什么關(guān)系?是不是林雪那個(gè)小婊子在牛臺(tái)長(zhǎng)枕頭邊吹什么風(fēng)了。譚飛的手機(jī)沒(méi)有人接,怎么回事?打給林雪,林雪倒是接了電話,不過(guò)態(tài)度很冷,孫曉剛小心翼翼地問(wèn):“譚飛好嗎?”
“好個(gè)屁。”林雪似乎也怒了:“讓人給抓走了。”
孫曉剛一下子就明白了,牛臺(tái)長(zhǎng)肯定是有什么把柄握在了林雪這個(gè)女人手里,這個(gè)世道讓人說(shuō)什么好了,一個(gè)新聞部的主任還比不上一個(gè)女人輕飄飄的一句話,孫曉剛這時(shí)候有些悲涼。
孫曉剛有些不解,為什么再一次把譚飛抓起來(lái)。
怎么辦?直接找江岸要人,是不是有難度?到了辦公室之后,孫曉剛還在琢磨這件事情。這時(shí)候牛臺(tái)長(zhǎng)來(lái)電話了,孫曉剛接起,牛臺(tái)長(zhǎng)冷冷地說(shuō):“你記個(gè)號(hào)碼,公安廳刑警總隊(duì)王中的電話。”王中是刑警總隊(duì)的總隊(duì)長(zhǎng),有他出面這個(gè)事情可能好辦很多。
放下牛臺(tái)長(zhǎng)的電話?cǎi)R上就給王中打電話。王總隊(duì)長(zhǎng)只是不冷不熱地說(shuō):“我叫我們小孟和你們一起去江岸看看,小孟原來(lái)是江岸市的人,那里他比我還熟悉。但真的違反原則的事情,我們也沒(méi)有辦法。”
孫曉剛明白,盡管王中話這么說(shuō),但是這個(gè)事情還是給辦了。
車到江岸,已經(jīng)太陽(yáng)落山的時(shí)候。江岸和俄羅斯一江之隔,由于今年天旱少雨,中俄交界的江岸河已經(jīng)顯示一副疲態(tài)。但是落日的余暉撒在江面上,依然美麗異常,這樣的景色在雪城的松花江是見不到的。孫曉剛以前多次來(lái)過(guò)江岸,每次都喜歡在江邊走一走。
這次帶到江岸的人不多,除了林雪和新聞部辦公室的老李之外就是警察小孟了。小孟說(shuō)他先回家看看,然后再找市局刑警隊(duì)以前的幾個(gè)好朋友探聽下情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孫曉剛覺得小孟有些小題大做,但是沒(méi)有說(shuō)什么,只是說(shuō):“要花錢什么的,和我吱聲。”
找到賓館先住下了。孫曉剛自己一個(gè)房間,林雪一個(gè)房間,司機(jī)和辦公室的老李一個(gè)房間。安頓好之后,孫曉剛想了想,還是先找宣傳部的于部長(zhǎng)吧。畢竟自己和他有數(shù)面之交。電話里匆匆把事情說(shuō)了之后,于部長(zhǎng)沒(méi)有表態(tài),但是二十分鐘后,于部長(zhǎng)給孫曉剛打來(lái)電話了,說(shuō)約到了市局局長(zhǎng)還有刑警隊(duì)的張力支隊(duì)長(zhǎng)一起吃飯。孫曉剛有些得意了,看樣子有些事情并沒(méi)有我們想的那么難。
晚飯安排在離公安局不遠(yuǎn)的滿漢樓吃。市局局長(zhǎng)和支隊(duì)長(zhǎng)張力很豪爽。孫曉剛幾次說(shuō)到了譚飛的事情,兩個(gè)人都說(shuō),調(diào)查一下沒(méi)事兒,就把他給放了。林雪當(dāng)時(shí)馬上露出一副非產(chǎn)感激的樣子,不停地敬酒,孫曉剛心里暗暗嘀咕,這個(gè)女人啊。
突然,孫曉剛的電話響了。孫曉剛拿起電話,電話那頭的人問(wèn):“是不是在和市局局長(zhǎng)還有支隊(duì)長(zhǎng)吃飯?”
孫曉剛心里一驚,忙說(shuō)是,同時(shí)起身就往外走。孫曉剛聽出來(lái)了,是小孟。
“孫主任,你還在這里吃飯,那邊開始審了。剛才于部長(zhǎng)打電話給公安局之后,公安局的人就開始審譚記者了。這個(gè)時(shí)候怕都交代了,這是刑事案件,一旦有了筆錄,就很難辦了。”小孟沒(méi)有多解釋,一口氣把話說(shuō)完了。
孫曉剛還有些半信半疑:“不會(huì)吧。”
“千真萬(wàn)確。”小孟加重了語(yǔ)氣:“他們?cè)谶@里吃飯就是為了穩(wěn)住你們。”
孫曉剛這時(shí)候有些懵,回到包間,局長(zhǎng)正在一邊碰杯一邊對(duì)林雪說(shuō):“只要你老公確實(shí)沒(méi)事,我們馬上就放人。”
孫曉剛一下子就明白了剛才這兩個(gè)人說(shuō)的沒(méi)事就放人的真正含意了。進(jìn)了公安局,誰(shuí)敢說(shuō)自己沒(méi)事。可能也是酒勁上來(lái)了,孫曉剛插上去問(wèn):“局長(zhǎng),我們小譚會(huì)不會(huì)有事了?”
“這個(gè),他自己最清楚了,一會(huì)兒我們可以去看看嗎。”刑警支隊(duì)長(zhǎng)張力發(fā)話了。聽到這里,孫曉剛明白了他們的意思。
孫曉剛這下子真的是沒(méi)有辦法控制自己了,拿起酒杯用力往桌子上一摔:“你們給我說(shuō),現(xiàn)在是不是正在審譚飛?”
市局局長(zhǎng)和支隊(duì)長(zhǎng)張力頭也不回地走了。
林雪明白了事情的全部經(jīng)過(guò)后,眼淚當(dāng)時(shí)就下來(lái)了,孫曉剛只是拍了拍林雪的后背,說(shuō)了聲:“這個(gè)世道呀。”
兩個(gè)小時(shí)后,牛臺(tái)長(zhǎng)電話打過(guò)來(lái),這次沒(méi)有一點(diǎn)埋怨的意思,只是說(shuō),休息一下吧,第二天再回來(lái)。
三天之后,譚飛被保釋出獄,但是交了5萬(wàn)塊的保釋金。
尾聲
譚飛回到雪城之后,再也沒(méi)有上班,一周之后,被單位開除,因?yàn)橛羞^(guò)犯罪記錄的人員是不能從事新聞工作的。
林雪的生意依舊紅火。
李彤還依舊在跑車,一次譚飛在商場(chǎng)附近吃肯德雞時(shí)還遇到了她,但是當(dāng)時(shí)兩人都沒(méi)有說(shuō)話。
其實(shí)譚飛不知道,他現(xiàn)在天天在家,胖得厲害,李彤見了根本認(rèn)不出他來(lá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