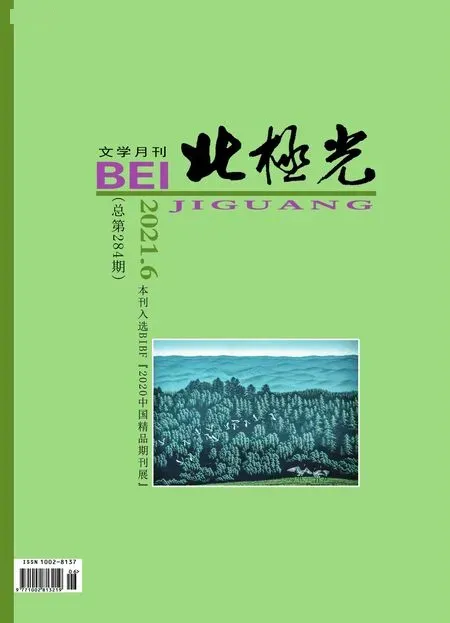長安詩酒胡姬花
□英子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天寶年間,白馬白衫的李白跨進長安城時,他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這座城池的法地象天的帝王氣度,而是一雙揮舞著的綿軟素手。城里的街道上,從世界各地涌來的商賈學子藝人僧侶縷縷行行,車水馬龍,人口最多時已超過一百萬。開放而寬容的、多民族混居的長安城,遂成了一個胡風滾滾、胡塵漫漫、胡樂飄飄的所在,在胡服、胡食、胡俗、胡歌之中,妖冶的胡姬伴著盛唐的詩酒歡歌,以狂野精怪喧囂著長安城內的一百零八坊,此時,這位金發碧眼、腰肢纖軟的胡姬的召喚正和著一縷縷春風,鼓蕩著李白精致的綢衫,也鼓蕩著李白狂放多情的心。
漢文古籍中所說的“胡”原意所指甚泛,幾乎涵蓋了所有華夏域外的異族。但據向達先生所著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考證,當時古籍中記載的流寓長安、擅長經商的“胡人”,主要是指波斯人和粟特人等。高鼻深目、曾書寫過楔形文字的波斯人性喜飲酒,美酒與美色是波斯人生活的重要內容;粟特人祖居于茫茫蔥嶺以西,通過歸附、人質、使節、技藝、商賈等多種渠道,粟特人的血脈之溪,沿著古雍州古涼州的河西走廊,數百年里一直無畏而堅定地向著長安、洛陽這些中華民族的主干城市滲透,至盛唐時,波斯人與栗特人早已成為長安城里重要的遷徙民族。
這些人數雖多、但仍被長安民眾輕蔑地稱之為“胡人”的商賈,多以販賣絲綢與美酒為生,他們販賣的酒類是高昌之“葡萄酒”、波斯之“三勒漿”、烏弋山離國的“龍膏酒”。“蒲桃”就是“葡萄”,據說,“唐太宗平定高昌后,收馬乳蒲桃實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損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緹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這種源自于高昌國,又經唐太宗御手欽制的、酒性酷烈的“葡萄美酒”,成了豪華的李唐皇宴的標志性飲品。暗紅色的美酒與碧綠色夜光杯色澤絕配,烈香徹骨,透過王昌齡“葡萄美酒夜光杯”給后人留下了精妙的遐想;“三勒漿”同“蒲桃酒”一樣的皇家珍品,可能酒性不如“蒲桃酒”那般清冽,清代陳元龍的《格致鏡原》這樣記載:“唐代宗以“三勒漿”賜太學諸生,其光灼灼,如蒲桃桂釀,味則溫馨甘滑”;“龍膏酒”既然稱之為“膏”,外觀一定粘膩似膏,唐代武功縣的進士蘇鶚一定是喝過這種美酒的,他在《杜陽雜編》里稱“龍膏酒”為“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杜陽雜編》卷二又記云:上(指唐憲宗)因好神仙不老之術,一個名叫“玄解”的“氣息高潔”的處士被密召入宮禁:“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龍膏酒色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至多,亦大國也”的“烏弋山離國”是班超打通的西域諸國之一,當指今之阿富汗的赫拉特一帶。如此看來,蒲桃酒、三勒漿、龍膏酒等不僅是酒類,更兼是唐代的珍貴滋補品。時至今日,四川成都的三勒漿藥業集團的廣告單上仍然寫著:“唐代的一本名叫《國史補》的古書上首次記載了一種神奇的配方,名為三勒漿。后來,三勒漿的主要藥材均收入歷代本草著作,包括《唐本草》《本草拾遺》《海藥本草》《藥性論》和《本草綱目》等”。
這些帶著西域詭譎香氣的美酒一入長安,便引發了滿城嘩然的喧囂。初唐詩人、生性貪酒的王績肯定是最早的一批酒客,因手中常無沽酒之資,王績只得賒酒而飲,后來干脆作《題酒店壁五首》以充酒錢:
有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的長道貰,慚愧酒家胡。
竹葉連糟翠,葡萄帶曲紅。相逢不令盡,別后為誰空?
比西域名酒更讓男人們驚艷的,是開酒店的胡人帶來的粉嫩如花的“胡姬”。胡姬是指來自中亞、西亞、甚至是歐洲一帶的女性,從詩人們夸贊她們“數錢憐皓腕”“胡姬招素手”的句子來看,她們應當是印歐人種的白種人,很可能源出中亞的索格底亞那地區。是被波斯或粟特的商人販賣到長安的女奴。《新唐書·西域傳》中“蔥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的記載,說明西域一直存在著買賣女奴的“女肆”。長安地處于絲綢之路的起點,是西域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各地商人在販賣絲綢美酒的同時,也輕車熟路地在長安做起了胡姬的買賣。纖腰胡姬身著廣袖合歡襖,腳踩繡花絲靴,貓一般綿軟地游走,她們碧綠發光的貓眼瞬間萬變,她們的頭發也如貓兒一樣黃里透金。還說,她們擺動腰肢、踮起足尖的胡旋舞,疾如旋風,輕如飛雪,在聲聲驚心的羯鼓聲里,高挑細削的胡姬那酥胸含雪環佩叮當的裝束,那完全不同于漢族女子的熱辣眼風,個個都是“胡姬醉舞筋骨柔”。于是,那頭發蓬亂、身披漁陽戰塵的驃騎男兒,是怎樣在錚錚鼗鼓聲中,摘下他腰間從沙場上帶回的大秦珠,換得一壇美酒的啊!那策馬而來、頭簪紅花的輕狂少年,是怎樣卸下了他的玉勒雕鞍,買得胡姬的一宿春醉啊!那身著仙袂般軟白的綢衫、常在酒肆中爛醉如泥的詩品般的李白,又是在怎樣的寸寸結結之中,寫下了“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的啊: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
為官清廉、卻也時常參與詩友的風花雪月之會的楊巨源,又是在哪一處“綠柳才黃半未勻”的二月清風里,朦朧的醉眼里飄忽著十五歲的嬌羞,才寫下了這首絲絲縷縷的“胡姬詞”的啊:妍艷照江頭,春風好客留。當壚知妾慣,送酒為郎羞。
“青綺門”即長安的春明門,在正東,興慶坊與道政坊之間。開元十六年,唐玄宗移入興慶宮聽政,興慶宮遂成為開元天寶年間的政治中心。唐代著名的宮殿南熏殿、大同殿、勤政務本樓、花萼相輝樓和沉香亭等建筑物都在興慶宮里,按照唐玄宗的授意,東郭墻內建造了“夾城”,供唐玄宗與皇親們秘密通行。夾城的南北起點就在春明門,淡掃娥眉身著男裝的虢國夫人,正拂開絲絲細柳,以天子之姨的華貴與慵懶,穿行于春明門的夾道之間呢。面白無須卻得意弄權的高力士,說不定就扶輦于夾城中,匆匆接回在寧王宅第爛醉的李翰林,說皇上和貴妃娘娘正在牡丹亭等著他的新詩呢。而日日笙歌的教坊里,紫玉笛吹出的清平調和霓裳羽衣曲,正順著春明門的夾城,傳入勤政樓上唐玄宗的耳中。這聲聲召喚,引得酷愛絲竹的唐玄宗放下了手中的朱筆,偷偷撫摸著藏在龍袍里的玉笛,心思又飄忽到昨夜的新曲譜上了。
“江頭”指的是曲江邊,在東南角,“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的暮春,大唐的新科進士鑼鼓喧天地在此擺下“聞喜宴”。這種連皇上都要“御紫云樓,垂簾觀焉”的盛況,豪華的教坊樂隊絲竹高亢,樂師雷海青的錚錚琵琶驚濤裂岸,宮伎第一女歌手念奴的高音破空而下,被玄宗譽為“每執行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二十五人吹管也蓋不過其歌喉”。王定保《唐摭言》有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填塞,莫可殫述”。所以,那高舉著皇上賞賜的四百酒錢的青年才俊,今日不僅暢飲美酒,還會一日看盡長安花呢。
如此的富貴麗景之下,在鋪著紅氈地毯、擺滿波斯風格的金銀杯壺的酒肆內,胡地廚師精心烹制出的羊饌、膾鯉、胡炮肉、駝峰炙、駝蹄羹、鵝鴨炙、羊皮花絲已盛滿高足銀盤,三勒漿閃著華彩,已在夜光杯中層層蕩漾。清越胡琴奏出的《樂世娘》絲絲入扣,俯在客人肩頭輕搖小扇的妖媚胡姬,薄薄青衫中透出“胡姬若擬邀他宿”的暗香,怎不讓多情公子意亂神迷啊。
花錢買得與胡姬春風一度,是當時的長安少年最得意、最樂意的事情。但令人不解的是,這個推動了長安酒文化的女性群體,這些傳播過西域歌舞的草根藝術家們,在長安的大街小巷鮮艷了數百年后卻真真的“風吹芳蘭折”了。今天,除了在詩人粉艷的詩箋上和斑駁的壁畫上能看到她們妖冶的背影之外,史書里竟然沒有關于她們的只言片語。
時至現代,卻有許多現代的學者們開始研究胡姬的生活,甚至有學者認為留下一整本傳奇戲文《西廂記》的崔鶯鶯就是一位胡姬。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大學者陳寅恪。陳先生在《讀鶯鶯傳》中推測說,崔鶯鶯原型是中亞粟特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并推出崔的原名為“曹九九”。近年來,《文物》主編葛承雍教授通過對《西廂記》故事的發生地山西永濟唐代蒲州普救寺的一系列考察,非常肯定地斷定崔鶯鶯的原型就是中亞“胡姬”。現將葛承雍教授發表于《北京青年報》上的文章摘錄于后,并致謝忱:
“一代學術大師陳寅恪先生非常善于從實錄筆法的小說中發現有根有據的歷史,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寫有《讀鶯鶯傳》一文,推測元稹塑造的崔鶯鶯原型是中亞粟特種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他參照胡姓、胡名和胡俗三項標準立說,首先,設想崔鶯鶯原名為曹九九,因為唐代中亞粟特人入居中原的很多,其中位于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北古布丹(G u b d a n)‘曹’國人,不僅在唐朝拜相做官,而且善彈琵琶,入居中國者很多,鶯鶯姓‘曹’而不姓‘崔’。極有可能,鶯鶯與古音‘九九’相近,雙文復字在唐代女子取名中常見,故崔鶯鶯諧音曹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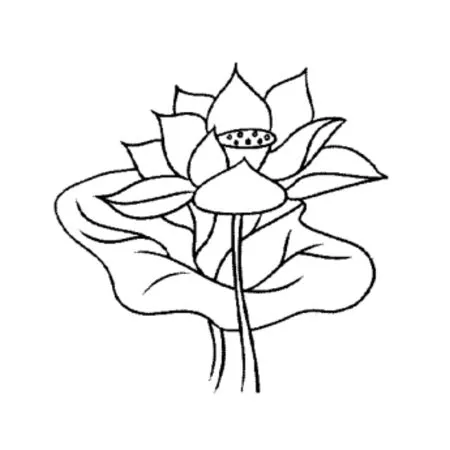
如今,隔著風隔著沙,長安城詩酒中的胡姬御風而去,竟無半點遺跡可尋。連年征戰的大漠邊關,裹在腐銹鐵衣中的狼族枯骨,再不能帶來半點異鄉的消息。如果,崔鶯鶯真是一位胡姬的話,那遙遠的邊城,會不會有一位同樣高鼻深目的少年,吹著羌笛,遙遙地寄來一份思念呢?這畫卷般令人心碎的一幕,卻早已出現在精靈詭譎的李賀的“龍夜吟”中:
卷發胡兒眼睛綠,高樓夜盡吹橫竹。
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