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壯歌
朱杰 全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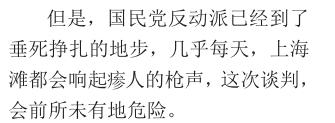
在位于國江路停車場 “公交三烈士”廣場內,聳立著一座白色雕像,蒼松翠柏見證著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1949年2月17日傍晚6時,國民黨當局派出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地將鐘泉周、王元、顧伯康三人押赴刑場實行槍決。凜冽的寒風中,三位烈士邁著堅定的步伐,面對敵人毫不畏懼……
暗夜明燈
1947年的一天夜晚,在上海西寶興路的一間房子里,燈火通明,外面,卻看不到窗子上的一點光亮,因為窗戶上罩了毛毯。
房子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學者正在黑板上畫一幅草圖。畫完,他清晰有力的語聲響了起來:“這個圖就是車輪上的軸承。軸承的英語怎么說呢?”
一位名叫王元的漢子回答:“白擰。”這話頓時引起一片哄笑。一個俊秀的年輕人笑著糾正:“是bearing。”
這位學者,是從重慶來到上海的機電專家,章名濤教授。俊秀年輕人,是章教授在西南聯大時教的學生,名叫鐘泉周。這師生二人,奉黨組織之命,由重慶秘密來到上海,配合中共地下黨的工作,為解放上海做準備。
在章教授的幫助下,鐘泉周進入上海公用局電車公司的汽車修理保養場,擔任技術員。師生開辦了個夜校,幫助工友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還傳播進步思想。
夜校的地點就選擇在鐘泉周的家里。這也得到他的妻子胡馥英的支持:“咱們有兩間房,一里一外,外間就做課堂。這樣,就不怕告密了。”
職工夜校就這樣開課了,章名濤教授講解汽車零部件知識,鐘泉周講述革命形勢。夜校很快得到了工友們的認可。
由于汽車零部件基本要靠進口,附帶的說明書都是英文,所以章教授附帶著教起了英文。工友們平時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全,面對拗口的英文,覺得難如天書。工友顧伯康就說:“章教授,我們都是貧苦人出身。拿我來說吧,從小在木器行里當伙計,后來當了國民黨汽車團的駕駛兵,因為看不慣他們發動內戰打自己人,才開起了公交汽車。我底子太薄,不學英文行嗎?”
王元也說:“我一天書都沒念過,不像鐘老師,上了那么多學,我學這個太難了。”
鐘泉周一直坐在角落里聽著,這時候他站了起來:“那我也說說自己吧。我家里也窮,小學沒念完就回家了,后來在一家書店打雜,可我一有空就看書,后來才靠自學考上了西南聯大。你們有章教授這樣的好老師,比我可強多了。”
這話一說,工友們的心穩定下來。鐘泉周趁機說:“我們學習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將來建立了新中國,上海的公交汽車由我們自己當家作主,再也不用受國民黨特務和黑心老板欺壓。”接著,他就向大家講起了革命形勢,聽得工友們眼睛里都閃閃發亮。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叫賣聲:“香煙、香煙、老刀牌香煙!”這是在外面放哨的工友發出的緊急信號,有特務來了!鐘泉周當即打開后門,掩護工友們火速離開。當章教授也要出去時,前門被踢開,一幫窮兇極惡的特務闖了進來。
化險為夷
鐘泉周這房子,是里外兩間,外間是客廳,里間是臥室。特務們一腳踢開了前門,一看外間,空無一人,又氣勢洶洶沖進里間,只見里面有三個人。
床上,一位不停咳嗽的年輕女人正伸出胳膊,請一位中年人診脈。特務們一闖進來,三個人六只眼,都驚愕地看過來。
領頭的特務,是臭名昭著的軍統特務丁慰堂。他盯著三人,惡狠狠地說:“我們接到密報,有很多可疑人進你這個屋子了。說,他們去哪里了?”
病人丈夫,也就是鐘泉周說:“哪有什么可疑人,我這是請了醫生給我太太看病。她病情嚴重,去不了診所。”
原來,后門開在臥室衣柜那里,當章教授正要出后門的時候,特務已經在外間破門而入,如果繼續出去,一定會被發現后門的。于是,章教授果斷退了回來。這時,胡馥英靈機一動,躺在床上裝病人,章教授和鐘泉周立刻配合,合演了一出戲。
丁慰堂仔細打量臥室,發現只有衣柜能藏人,就過去檢查,但衣柜里空空如也。他又讓小特務搬開衣柜,檢查后墻,也沒有暗門。難道密報有誤?丁慰堂小眼睛一掃,發現窗戶上遮擋著毛毯,不由疑心大起:“就現在這天氣,遮窗戶干什么?是不是心里有鬼?”
鐘泉周鎮定回答:“我太太這病,見不得風,又怕光,所以,唉——”他還故意嘆了口氣。
丁慰堂看向章教授:“你說,她得的是什么病?”
章教授不慌不忙地說:“結合病人的脈象看,應該是肺癆。這病要當心傳染。”
一聽這話,丁慰堂和他手下的小特務都嚇了一跳,急忙后退。但丁慰堂還不死心,又追問一句:“那這個病怎么治呢?”說完,他的兩只小眼珠緊緊盯著章教授。
章教授還是那副不緊不慢的樣子:“這是肺陰虧損型,該用的中藥有:沙參、麥冬、天冬、生地、百部,等等,我還是開方子吧。”說著筆走龍蛇,真的寫起了方子。原來章教授年輕的時候,還真學過中醫,這時候派上了大用場。
丁慰堂見挑不出什么毛病,正想垂頭喪氣地回去,忽然,他的小眼睛又盯上了衣柜,又走了過去:“我總覺得這個衣柜可疑!”
就在這時,就聽“哇——”的一聲,胡馥英吐出一口血來。章教授急忙說:“都后退,這血傳染性極強!”丁慰堂暗叫一聲倒霉,帶著手下人匆匆走了。
聽著腳步聲漸漸遠去,鐘泉周與章教授相視一笑。原來,后門沒在后墻上,而是衣柜上方天花板上的一個開口,這時用和天花板同樣顏色的木板擋著,不注意根本看不出來。忽然,鐘泉周又擔心地問妻子:“你怎么會吐血呢?”胡馥英一張嘴,里面竟然是鮮紅一片:“我把自己舌頭咬破了,不然,還真騙不過這幫狗特務。”鐘泉周心疼之下,一把抱住了妻子。
這件事一發生,說明特務已經盯上了這里,夜校是不能開了,人也會有危險。第二天,中共地下黨員吳兆森找到章教授和鐘泉周,讓他們去北平。兩人都不愿意走,鐘泉周說:“黎明前是最黑暗的,這里最需要我,我不能離開。”鐘教授也不愿意走,鐘泉周反倒勸起自己的老師來:“您是中國首屈一指的電機工程專家,未來的新中國百廢待興,您應該到建設國家更需要的地方去……”一番肺腑之言打動了他,于是,章名濤教授在地下黨的安排下,登船離開了上海。
再說鐘泉周,在開夜校時,他發現工友王元和顧伯康兩位思想覺悟高、為人可靠,就注意培養,當時機成熟后,帶領兩人去見吳兆森,介紹他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鐘泉周身邊又多了兩位最可靠的戰友。
罷工風潮
1948年的上海,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就連鐘泉周所在的電車公司,工友們的生活也出現了困難。
這天,王元和顧伯康闖進了鐘泉周家里。王元呼哧呼哧直喘:“泉周,今天公司找司機和售票員開會,要解雇125名售票員,還有76名司機!”

“怎么,你們兩個被解雇了?”鐘泉周不安地問。
顧伯康說:“那倒沒有。可是被解雇的那些工友怎么生活啊?”
三人商量對策,王元提出要去社會局請愿。鐘泉周思考了一下,搖搖頭,又點點頭:“不能去社會局,我們要去更大的地方,兵分兩路。”說著,他就在兩個戰友耳邊低聲說起來。
1948年7月7日,鐘泉周、王元帶領公交職工們分別坐上44輛公交車,來到江西中路包圍了市政府進行請愿,要求當局不得解雇工人。另一路,由顧伯康帶領工人來到公司所在的公平路大禮堂,用粉筆在墻上書寫“我們要吃飯”,張貼“我們要工作”“反對無理解雇”等標語,號召更多的工人加入罷工隊伍。
國民黨市政府派出公司員工福利會的頭頭,來安撫工人們。為首的,竟然就是那個特務丁慰堂。原來,在軍統,他就負責這一區。見了鐘泉周,丁慰堂立刻認了出來:“又是你?說,你是不是受共產黨指使的?”

鐘泉周回答:“我是受被解雇的工人指使的,倒是你們員工福利會,為什么總是替資本家說話?”
丁慰堂無言以對,員工福利會的人開始假惺惺地勸慰工人們,說什么汽油價格大漲,經營困難云云。
鐘泉周向王元使個眼色,王元立刻大喊:“你們都是黑心資本家的狗腿子,要你們干什么?”說著,帶領工人們沖過去。員工福利會的人狼狽逃竄。
這場罷工持續了兩天,大規模的游行、輿論的壓力以及交通癱瘓,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不得不同意在外灘水上飯店與新工人代表談判。鐘泉周、王元、顧伯康作為工人代表,迫使電車公司答應不再解雇人員,而是改為留職停薪。鐘泉周又特別提出,原有的員工福利會,已經代表不了工人利益,立即解散,由工友們民主推舉新一屆員工福利會。原來,鐘泉周早已想到,要把工人們團結起來和敵人作斗爭,必須有一個公開的組織,這個員工福利會一定要由工人自己來管理。所以,他才特意安排王元,讓工友們看清員工福利會的真面目。
兩個月后,第三屆電車公司員工福利會召開選舉會,工人代表們一致選舉鐘泉周擔任福利會理事長,王元、顧伯康當選為司機常務理事和理事。一場公交史上反解雇的罷工斗爭,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取得全面勝利。
英勇就義
1949年春寒料峭,還是那么刺骨的冷。在大會議室里,員工福利會正在召開理事會議。這個會的氣氛很不尋常,起因,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渡江,國民黨反動政府準備南遷廣州,臨時給南京的公教人員發了一筆“應變費”。電車公司的司機也是公教人員,卻沒有兌現,工友們紛紛找上員工福利會,要他們出面和當局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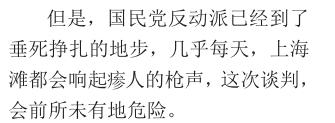
頓了頓,鐘泉周說話了:“我們會去和他們談判,不過,要講究策略,不能蠻干。”
鐘泉周告訴王元和顧伯康:“解決工友生活問題,只是其一。我想的是,上海解放在即,要嚴防敵人破壞公交設施,我們要借機讓工友看清國民黨的真面目,保護電車公司,完好交到黨的手中。”
談判現場,鐘泉周遇上了一個“老熟人”——特務丁慰堂。丁慰堂皮笑肉不笑地說:“鐘先生,現時不同往日,我可沒什么耐心。”潛臺詞是,他隨時可以下毒手!
鐘泉周才不怕他呢,針鋒相對:“巧了,我也沒什么耐心。政府答應工友,發給工友們每人六石米的‘應變費,說到就該做到,不然,我們將罷工示威。”
丁慰堂都要氣瘋了,上次的大罷工,他被上司一頓臭罵,差一點被撤職,這次是萬萬不能再罷工了。他揮舞著雙手說:“你再提罷工,我現在就槍斃你!”
手下的十多個小特務紛紛亮出短槍,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鐘泉周和眾工友。王元和顧伯康一看,立刻招呼工友們操板凳自衛。
流血犧牲一觸即發,反倒是鐘泉周先說話了:“這樣吧,給你們三天時間,如果我們還是拿不到應變米,那么……”
丁慰堂有了臺階下,悻悻地說:“大家應該體諒政府難處,三天后肯定發的。”然后狼狽逃竄了。
鐘泉周這么做,是因為他知道,這幫家伙狗急了會跳墻,真的會開槍,現場工友人數太少,沒必要做無謂犧牲。三天后,如他所料,一粒米都沒有發下來,他才找來王元和顧伯康,全市公交車大罷工!
2月16日清晨,由顧伯康所在楓林橋營業所率先進行停車罷工,接著各公交線路工人陸續響應。丁慰堂聞訊后,急忙帶著一大幫特務趕到現場同工人們談判。
顧伯康說:“還是原來的要求,每人發應變費6石米!”周圍工友們也陸續圍攏過來,大聲呵斥當局的無賴嘴臉,人越聚越多。這可不是前幾天的談判場,面對這么多人,丁慰堂可不敢動槍了,聲稱回去向上峰請示,盡量替大家爭取應變米,然后溜回了警局。不過,他可不是去要米的,是要軍隊鎮壓罷工潮!
當晚,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派出大批軍警,包圍了楓林橋保養場,從職工宿舍內抓了顧伯康。消息很快被中共地下黨員曹淼獲知,火速趕往鐘泉周家,通知他馬上轉移。
妻子胡馥英匆忙收拾了一下,要和丈夫一起走,鐘泉周不放心:“黨的一些機密文件,還有一些來往信件,我還沒銷毀完。你先走,我隨后到。”胡馥英只好先走一步。
可是,他剛剛燒完最后一封信,警局大隊人馬就闖了進來。幾乎同時,包括王元在內的九位職工同時被捕。
2月17日凌晨,鐘泉周被解到警備司令部受審。丁慰堂聞訊趕來,他對鐘泉周恨得直咬牙,陰森地說:“老朋友,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說,你的上司是誰?”
鐘泉周一口吐沫吐到他臉上:“誰跟你是老朋友?我的上司就是廣大工友,我是全體職工選出來的理事長,為職工謀福利有什么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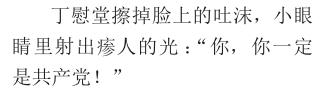
鐘泉周哈哈一笑:“我還真不是,我要是就好了!”原來,他在西南聯大參加的是中國民主青年同盟,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后來他多次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上考慮“民青”這個身份更適合展開地下工作,就沒有批準,現在,竟然成了鐘泉周的一個遺憾。
丁慰堂一時間理屈詞窮,臨走拋下一句:“實話跟你說,上峰給了我六個字,‘借人頭,平工潮,招不招都一樣,反正你們都是要槍斃的。”鐘泉周只是輕蔑地一笑。
幾乎在同一時刻,另外的審判室里,王元、顧伯康等人也是大義凜然,無所畏懼。當審訊人員脅迫他們交代誰是共產黨、主謀是誰時,顧伯康激昂地說:“向你們要6石應變米是我先提出的,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審訊從凌晨2點一直到清晨6點,敵人都一無所獲。
丁慰堂黔驢技窮了,竟然將鐘泉周懷孕的妻子胡馥英抓入大牢,讓她好好勸勸“頑固不化”的鐘泉周。但沒想到,這對革命夫妻竟然互相鼓勵起來,讓鐘泉周更為堅定。
胡馥英臨走時,鐘泉周遞給她一件舊衣服,說讓她回家洗洗,等他出獄再穿。胡馥英到家后,拆開衣服內側,竟發現了丈夫的遺書:我今天被公司陷誣關在滬淞警備(司令)部,或須冤枉要死,希你照看小孩,能夠在家鄉再(更)好。否則就決定改嫁,免得吃苦……
她后來才知道,就在那天,1949年2月17日傍晚6時,鐘泉周、王元、顧伯康三人被秘密槍決。
解放后,時任上海市長陳毅為三烈士舉行殉難一周年追悼大會,并題寫悼詞:為中國人民事業而犧牲,永遠為人民所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