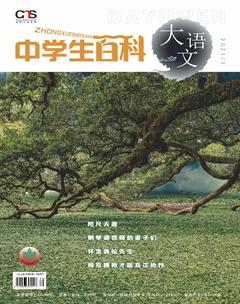鋼琴調(diào)音師的妻子們
[愛(ài)爾蘭]威廉·特雷弗

維奧萊特嫁給他的時(shí)候,鋼琴調(diào)音師還是個(gè)小伙子。貝爾嫁給他的時(shí)候,他已經(jīng)老了。
還不只這些,要知道選擇維奧萊特為妻的時(shí)候,鋼琴調(diào)音師已經(jīng)拒絕了貝爾,宣告第二次婚禮的時(shí)候,大伙兒還記得這事。“哎,不管怎么說(shuō),她算是得到了殘余的他。”鄰居中有個(gè)農(nóng)夫這樣評(píng)說(shuō),這么說(shuō)并無(wú)根據(jù),只不過(guò)是在陳述他的觀點(diǎn)而已。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會(huì)有另外一種說(shuō)法。
鋼琴調(diào)音師一頭白發(fā),隨著一個(gè)一個(gè)潮濕的冬天過(guò)去,他一只膝蓋的關(guān)節(jié)炎也越發(fā)嚴(yán)重了。曾經(jīng)的溫文爾雅如今已不見(jiàn),比起同維奧萊特結(jié)婚那天——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一個(gè)星期四——他也更瞎了。較之一九五一年那會(huì)兒,如今,他生活中的陰影也愈發(fā)模糊稀疏了。
“我愿意。”在小小的圣科爾曼新教教堂里,他應(yīng)道,他所站立的地方幾乎就是許多年前的那個(gè)下午他曾經(jīng)站立過(guò)的位置。五十九歲的貝爾呢,則和她從前的情敵一樣,站在同一個(gè)圣壇前,將維奧萊特說(shuō)過(guò)的話重復(fù)了一遍。這段空當(dāng)間隔得恰到好處;教堂里的人憶起維奧萊特沒(méi)有不心懷敬意的,對(duì)于她的離世也沒(méi)有不痛心緬懷的。“……并將我所有世俗財(cái)產(chǎn),盡獻(xiàn)于你。”鋼琴調(diào)音師說(shuō)道,他的新任妻子在想,她更愿意穿著白紗而不是這身合宜的酒紅色站在他身旁。她沒(méi)有參加那第一次婚禮,盡管她受到了邀請(qǐng)。那天她讓自己忙乎了一天,粉刷雞棚,但即便如此,她還是哭了。不管有沒(méi)有哭,她都來(lái)得更漂亮——差不多要比那個(gè)如此清晰地占據(jù)著她頭腦,令她用嫉妒同之搏斗的新娘年輕五歲。然而,他選擇了維奧萊特——或者說(shuō)選擇了自己的房子有朝一日會(huì)歸于她名下的前景,貝爾站在雞棚里苦澀地告訴自己,還有那一丁點(diǎn)兒錢,對(duì)于一個(gè)瞎子的生活來(lái)說(shuō)多少可以喘口氣。后來(lái),每當(dāng)她看到維奧萊特領(lǐng)著他走路,每當(dāng)她想到維奧萊特為他打理一切,給予他生活,她便覺(jué)得這一切也是可以理解的。哎,換了她也能做到。
人們離開(kāi)教堂的時(shí)候,有人在用管風(fēng)琴?gòu)椬喟秃盏那樱D鞘撬墓ぷ鳌H藗冊(cè)谛⌒〉慕烫媚沟乩锶宄扇海瑝災(zāi)沽阈巧⒉荚谶@幢小小的灰色建筑周圍,鋼琴調(diào)音師的父母親,還有他父親這邊的好幾代祖先都埋葬于此。參加婚禮的客人要是愿意到兩英里之外的家里去,將會(huì)有茶點(diǎn)招待他們,不過(guò)一些人向新人獻(xiàn)上祝福,就此告辭了。鋼琴調(diào)音師握著這一雙雙熟悉的手,想象著這一張張他的第一個(gè)妻子曾向他描述過(guò)的面孔。正是盛夏,同一九五一年那會(huì)兒一樣,陽(yáng)光熱烘烘地照在他的前額兩頰,還透過(guò)那厚重的結(jié)婚禮服照在他身上。這個(gè)墓地他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一輩子了,小時(shí)候,他就摸索著石頭上的字母,對(duì)他母親拼出父親家族的一個(gè)個(gè)名字。他和維奧萊特沒(méi)有孩子,有的話他們會(huì)很喜歡。有那么一種說(shuō)法,他就是她的孩子,每當(dāng)貝爾聽(tīng)到這句話,就會(huì)覺(jué)得是一種刺激。她本可以給他生孩子的,這一點(diǎn)她很有把握。
“我預(yù)備下個(gè)月去拜訪您。”年邁的新郎提醒一位仍握著他手的婦人,她有一架斯坦威鋼琴,那是他調(diào)過(guò)的鋼琴里唯一一架斯坦威。她彈得好極了。他詢問(wèn)何時(shí)上門(mén)去調(diào)音,并再三表示,聆聽(tīng)她的彈奏就足以支付報(bào)酬了。但她從來(lái)不短他的酬金。
“第三個(gè)星期一,我想。”
“好的,朱莉亞。”
她叫她德羅姆古爾德先生:他有他的處事風(fēng)格,不喜同人親昵。人們說(shuō)起他,常用鋼琴調(diào)音師來(lái)稱呼,對(duì)他職業(yè)的提示顯示出人們對(duì)一位頗具才華者的敬意。他的全名叫歐文·弗朗西斯·德羅姆古爾德。
“哦,天氣真好,安排在今天,”教區(qū)新來(lái)的年輕牧師說(shuō)道,“天氣預(yù)報(bào)說(shuō)可能會(huì)有陣雨,但他們肯定弄錯(cuò)了。”
“天空——”
“哦,無(wú)云,德羅姆古爾德先生,無(wú)云。”
“哎,真好。那您愿意光臨寒舍吧,我想?”
“他肯定會(huì)來(lái)的,當(dāng)然了。”貝爾催促著,匆匆穿過(guò)墓地里的人群,并一再向大家發(fā)出邀請(qǐng),她一定要舉行一場(chǎng)派對(duì)。
過(guò)了一段時(shí)間,當(dāng)這場(chǎng)新的婚姻進(jìn)入日常生活后,人們想知道鋼琴調(diào)音師是不是有退休的打算。一只膝蓋不好,看不見(jiàn),又上了歲數(shù),在他發(fā)揮才干的時(shí)候,那些私宅、修道院、學(xué)校里的人都對(duì)他寬容有加。他閑不下來(lái),歲月流逝,他也沒(méi)交到多少好運(yùn)。但是,偶爾有饒舌的人或是包打聽(tīng)將這個(gè)問(wèn)題擺在他前面的時(shí)候,他否認(rèn)自己有過(guò)這種念頭,他也不認(rèn)為只有死神的召喚才會(huì)終結(jié)這一切。事實(shí)是,要是不工作,不到處轉(zhuǎn)悠,長(zhǎng)久以來(lái)不是每半年左右就要跑到一個(gè)個(gè)小鎮(zhèn)上為人服務(wù),他就會(huì)不知所措。不,不會(huì)的,他承諾,他們還會(huì)看到那輛白色的沃克斯豪爾車轉(zhuǎn)進(jìn)某個(gè)農(nóng)場(chǎng)的大門(mén)口,或是在某個(gè)修道院的大院子里停上半小時(shí),或是停在路邊,而他則咀嚼著他的午飯三明治,喝著妻子給他裝在保溫瓶里的茶。

這項(xiàng)業(yè)務(wù)主要是維奧萊特開(kāi)發(fā)出來(lái)的。兩人結(jié)婚那會(huì)兒他還同母親住在巴納高姆大宅的門(mén)房里。之前他已經(jīng)開(kāi)始給鋼琴調(diào)音了——兩架在巴納高姆大宅,一架在巴納高姆鎮(zhèn)上,還有一架在一家農(nóng)戶里,他要走上四英里。那時(shí)候人們都可憐他是個(gè)瞎子,所以他時(shí)不時(shí)被叫去修理馬桶或是椅子的海草坐墊,這也是他學(xué)來(lái)的本事,或者在某個(gè)重要場(chǎng)合拉奏小時(shí)候他母親給買的那把小提琴。婚后,維奧萊特改變了他的生活。她住進(jìn)了那間門(mén)房,她跟他母親也不是一直都處得好,但好歹還是過(guò)下來(lái)了。她有輛車,這便意味著只要她在哪兒發(fā)現(xiàn)一架長(zhǎng)期疏于照料的鋼琴,她就可以開(kāi)著車帶他去。她駕車去那些人家里,最遠(yuǎn)的在四十英里外呢。她算上車子的油耗和損耗,確定了他的收費(fèi)。她備了個(gè)地址簿,還在日記里記下每家下次調(diào)音的日期,這些都很管用。她記下一筆筆可觀的收入增長(zhǎng),發(fā)現(xiàn)迄今為止最賺錢的還屬拉小提琴:在寂寥的酒館里那些鄉(xiāng)村與西部音樂(lè)的晚會(huì)上拉奏,夏天里,在十字路口搭起的舞臺(tái)上為舞會(huì)拉奏——一項(xiàng)在一九五一年間還沒(méi)有完全絕跡的活動(dòng)。歐文·德羅姆古爾德喜歡小提琴,在哪兒都愿意拉,不管有沒(méi)有錢,不過(guò)維奧萊特看中的是錢。
于是,這第一段婚姻就這樣忙忙乎乎地發(fā)展著,后來(lái),維奧萊特繼承了她父親的房子,便把丈夫接去同住。它曾是一座農(nóng)臺(tái),但因?yàn)榧依飵状硕际染迫缑艳r(nóng)場(chǎng)的地都喝沒(méi)了。不過(guò),還好維奧萊特沒(méi)有沾染上這一困擾著她家的惡習(xí)。
“好了,告訴我那兒有什么。”早些年她丈夫經(jīng)常這么問(wèn),維奧萊特便把這所她帶著他人住的房子的情況告訴他,房子坐落在偏僻的山腳下,這些山有時(shí)候看上去是藍(lán)色的,房子就在一條巷子拐彎處靠后一點(diǎn)的地方。她描述著屋子里的角角落落,當(dāng)東邊吹來(lái)的風(fēng)形成的氣流影響到那間過(guò)去被叫做客廳的屋子里的爐火時(shí),他可以聽(tīng)到她拉啟和閂上木百葉窗的聲音。她描述著鋪在屋里僅有的那段樓梯上的地毯的花紋,廚房碗柜上那藍(lán)白相間的瓷把手,還有那扇從不曾開(kāi)啟的前門(mén)。他聽(tīng)得津津有味。他的母親,從來(lái)沒(méi)有遷就過(guò)兒子的苦惱,當(dāng)初可沒(méi)有這么耐心。他父親過(guò)去在巴納高姆大宅當(dāng)馬夫,跌了一跤后死了,他對(duì)父親一無(wú)所知。“瘦得跟條獵狗似的。”維奧萊特這樣描述他父親留下的一張照片。
她讓巴納高姆大宅那寬敞、冰涼的大廳歷歷在目。“通往樓梯的這一路上我們繞著走的是一張桌子,上面擺了只孔雀。這是一只銀色的大鳥(niǎo),張開(kāi)的尾翼間點(diǎn)綴著一小片一小片的彩色玻璃,代表它五顏六色的羽毛。綠的和藍(lán)的。”他問(wèn)起顏色時(shí)她說(shuō)道,哦,還有,她確信那不過(guò)是用玻璃做的,不是什么珠寶,因?yàn)橛幸淮危谒σ愿皩?duì)付客廳那架破得不成樣子的大鋼琴的時(shí)候,有人告訴過(guò)她。樓梯是弧形的,因?yàn)榻?jīng)常跑上跑下修理育嬰室那架夏貝爾鋼琴,所以他知道。第一層的樓梯過(guò)道黑得跟隧道似的,維奧萊特說(shuō),有兩張沙發(fā),兩頭各一張,墻上還黑魆魆地掛著幾排面無(wú)笑容的畫(huà)像。
“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過(guò)的是杜西加油站,”維奧萊特會(huì)說(shuō),“菲利神父在泵那兒加油呢。”

杜西加油站售的是埃索汽油,他知道這個(gè)詞怎么寫(xiě),因?yàn)樗麊?wèn)過(guò)別人。標(biāo)識(shí)用的是兩種顏色;那個(gè)圖形與他感覺(jué)得到的形狀做過(guò)比較。借助維奧萊特的眼睛,他看見(jiàn)了奧格希爾郊區(qū)麥克科迪大宅那荒涼的外墻。他看見(jiàn)了基勒思那個(gè)文具商沒(méi)有血色的臉。他看見(jiàn)了他母親永遠(yuǎn)地閉上了眼睛,雙手交叉在胸前。他看見(jiàn)了群山,有時(shí)是藍(lán)的,有時(shí)霧散去又變灰了。“報(bào)春花沒(méi)那么鮮艷,”維奧萊特說(shuō),“更像是稻草或者是鄉(xiāng)村黃袖的顏色,中間有一點(diǎn)顏色。”他就會(huì)點(diǎn)點(diǎn)頭,知道了。淡藍(lán)色的,就跟煙一樣,她描述著山巒,中間那塊不是紅色,更像是橙色。對(duì)于煙,他知道的也并不比她告訴他的多,但是,他能分辨那些聲音。他堅(jiān)持認(rèn)為他知道紅色是什么,因?yàn)樗?tīng)得出它的聲音,也知道橙色,因?yàn)閲L得出來(lái)。他看得見(jiàn)埃索招牌上的紅色,還有報(bào)春花里的那點(diǎn)橙色。說(shuō)“稻草”和“鄉(xiāng)村黃袖”他就明白了,維奧萊特說(shuō)惠騰先生脾氣古怪也就夠了。有個(gè)院長(zhǎng)嬤嬤看上去很嚴(yán)肅。安娜·克雷吉喜歡異想天開(kāi)。鋸木廠的托馬斯是個(gè)邋遢的家伙。巴特·康倫的前額長(zhǎng)得像梅里克家的那條獵犬,每次看到梅里克家的布羅伍德,就要摸摸它。
在前妻去世尚未續(xù)弦的這段日子里,鋼琴調(diào)音師獨(dú)自一人也就這么過(guò)來(lái)了,那些有鋼琴的人家得開(kāi)著車接送他,買東西、家務(wù)活也需要有人幫忙。他感覺(jué)自己成了他人的累贅,心知這可不是維奧萊特所希望的。她也不會(huì)希望她為他一手建立起來(lái)的事業(yè)因?yàn)樗碾x去而被荒廢。他在圣科爾曼教堂演奏管風(fēng)琴令她驕傲。“永遠(yuǎn)也別放棄。”在輕聲說(shuō)出臨終幾句話之前,她就輕聲說(shuō)過(guò)這話,于是,他獨(dú)自去教堂。在差不多過(guò)去兩年后的一個(gè)星期天,他與貝爾再續(xù)前緣。
當(dāng)年貝爾被拒絕之后,一直不能擺脫嫉妒之情,她氣不過(guò)維奧萊特貌不如己,令她痛苦的是,在她看來(lái),似乎失明這一懲罰也像是加在她頭上的。除了懲罰,你還能管眼前一抹黑叫什么呢?除了懲罰,還有什么能將黑暗置于她的美貌之上?然而,并沒(méi)有什么罪孽可懲罰,他倆原本應(yīng)該是稱心的一對(duì),她和歐文·德羅姆古爾德,她把美貌給予了一個(gè)并不知曉美貌的男人,那應(yīng)該是一種德行。
因?yàn)椴恍覠o(wú)休止地折磨著她,貝爾一直未婚。她起先是幫父親,后來(lái)是幫她哥哥看家里開(kāi)的這個(gè)店,給留在店里等著修理的鐘表寫(xiě)寫(xiě)標(biāo)簽,記錄一下體育獎(jiǎng)杯上要雕刻的文字。她在店里唯一一張柜臺(tái)后頭給顧客服務(wù),圣誕節(jié)期間她最忙,玻璃制品和氣象指示器是最受歡迎的結(jié)婚禮物,打火機(jī)和廉價(jià)首飾買的人少些。有的時(shí)候鐘表不過(guò)是需要裝個(gè)電池,于是禮品這部分的生意就擴(kuò)大了。不過(guò)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鎮(zhèn)上始終沒(méi)有出現(xiàn)一個(gè)男人能比得上那個(gè)被人從她身邊奪走的人。
貝爾出生時(shí)還沒(méi)這個(gè)店呢,等到房子和店鋪都?xì)w她哥哥所有的時(shí)候,她依舊住在那里。她哥哥有了孩子之后,她在家里還是有地方可住,她在鋪?zhàn)永锏奈恢靡矡o(wú)人篡奪。她在屋后養(yǎng)了一群雞,從十歲生日那天起她就開(kāi)始養(yǎng)雞:這同樣持續(xù)到現(xiàn)在。她懷著失落生活著,很久以前這就成了她的一部分,侄子、侄女眼里的她就是這副樣子。有人注意到,她眼里的愁苦反倒令她更顯嫵媚。當(dāng)她與曾經(jīng)拒絕過(guò)她的那個(gè)人再續(xù)前緣時(shí),兄嫂都覺(jué)得她在犯傻,但嘴上并不說(shuō),只是笑著問(wèn)她是不是打算把那群雞一起帶走。
那個(gè)星期天,等幾個(gè)教區(qū)居民走了,他倆就站在教堂墓地里說(shuō)話。“來(lái),我?guī)憧纯茨切┠埂!彼f(shuō)著便走在前頭,對(duì)自己要去的地方一清二楚,他踏上草地,用手指觸摸第一塊墓碑。這是他奶奶,他說(shuō),他父親的媽媽,有那么一會(huì)兒,貝爾真想親手感覺(jué)下那些刻在上面的字母,而不是看著它們。他倆走在墓碑間,兩人都知道,那些已經(jīng)回家去的教區(qū)居民對(duì)落在后頭的這一對(duì)兒知根知底。維奧萊特死后,每個(gè)星期天他都會(huì)在家和墓地之間往返,除非下雨。真要碰上下雨,開(kāi)車送珀蒂爾老太太去教堂的那個(gè)人也會(huì)捎他回家。“你想散散步嗎,貝爾?”介紹完家族墓碑,他問(wèn)道。她說(shuō)她想。
貝爾出嫁的時(shí)候并沒(méi)有帶上她的雞。她說(shuō)養(yǎng)雞已經(jīng)養(yǎng)夠了。后來(lái)她有些后悔,因?yàn)樵谀莻€(gè)屬于維奧萊特的家里,她無(wú)論做什么事,都覺(jué)得這事過(guò)去維奧萊特做過(guò)。當(dāng)她切肉準(zhǔn)備做燉肉時(shí),她站在那里,陽(yáng)光照在維奧萊特用過(guò)的砧板、道具上,她感覺(jué)自己就像個(gè)模仿者。她把胡蘿卜切成丁,相信維奧萊特也這么切過(guò)。她買來(lái)新的木勺,因?yàn)榫S奧萊特的那些都不好使了。她粉刷了樓梯扶手的豎欄桿,她還粉刷了那扇從不開(kāi)啟的前門(mén)里頭的一面。她把那一堆堆婦女雜志處理掉了,那是她在樓上―個(gè)小櫥里找到的,很有些年頭了。她扔了一個(gè)油炸鍋,因?yàn)樗X(jué)得那玩意兒不干凈。她訂購(gòu)了新的廚房塑料地板。她定期給屋后的花壇鋤草,免得有人上門(mén)來(lái)說(shuō)她把這個(gè)地方搞得了無(wú)生氣。
事情一直就是這樣一分為二:什么要保留,什么要改變。當(dāng)她照料花壇的時(shí)候,她是在向維奧萊特讓步嗎?當(dāng)她扔掉一個(gè)油炸鍋和三把木勺的時(shí)候,她是在向瑣事屈服嗎?無(wú)論做了什么,事后貝爾總會(huì)懷疑自己。維奧萊特矮矮胖胖,一頭灰發(fā)就跟臨終時(shí)一樣,肉鼓鼓的臉把眼睛擠得小小的,仿佛要令人生氣地發(fā)號(hào)施令。而那位她們共有的盲人丈夫,不是在這間就是在那間屋子里輕柔地拉著小提琴,何曾知道他的第一個(gè)妻子衣著難看,身材走樣,邋里邋遢,臟兮兮地下著廚。活著的是貝爾,她享受著一個(gè)男人所有的愛(ài),她占有了他前一個(gè)女人的財(cái)產(chǎn),住著她的房間,開(kāi)著她的車,這還不夠嗎。事情應(yīng)該就是如此了,可是,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這些對(duì)于貝爾來(lái)說(shuō),似乎根本不算什么。他在那段將近四十年的婚姻里一成不變,由著自己,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樣子:一直都是如此。
結(jié)婚一年后的某天中飯時(shí)間,貝爾將車開(kāi)到一片田地的通道處,夫婦倆坐在車子里,他說(shuō):
“告訴我,你是不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什么,歐文?”
“開(kāi)著車在那里奔來(lái)跑去。送我去又接我回來(lái)。無(wú)奈地坐著聽(tīng)我嘮叨。”
“沒(méi)什么受不了的。”
“你可真有好性子。”
“我覺(jué)得自己一點(diǎn)也不好。”
“那個(gè)星期天我知道你在教堂里,我聞得出你身上的香水味。哪怕坐在風(fēng)琴那兒我也聞得到。”
“我永遠(yuǎn)也不會(huì)忘記那個(gè)星期天。”
“你允許我給你介紹那些墓碑的時(shí)候,我愛(ài)上了你,那之前我就愛(ài)你了。”
“我不想讓你太累,調(diào)完那些鋼琴后還要東游西蕩的。我可以放棄的,你知道。”

他愿意為她那么做,他說(shuō)的時(shí)候,她想。對(duì)于一個(gè)女人來(lái)說(shuō),他算不了什么,過(guò)去他說(shuō)過(guò)這話:不過(guò)是一個(gè)來(lái)日無(wú)多的瞎子。他坦承,在他起念要娶她的時(shí)候,他憋了兩個(gè)多月沒(méi)有向她開(kāi)口,因?yàn)樗人宄偃缢f(shuō)愿意,她將為此付出什么。“那個(gè)貝爾最近看上去怎么樣啊?”幾年前他問(wèn)過(guò)維奧萊特,維奧萊特起先沒(méi)吭聲,接著,她說(shuō)的似乎是:“貝爾看上去還跟個(gè)姑娘似的。”
“我可不想你不工作,永遠(yuǎn)也不,歐文。”
“你是我的心肝,親愛(ài)的。別說(shuō)自己不好。”
“這也能讓我四處走走,你知道。比我過(guò)去去過(guò)的地方要多得多了。在通往那些陌生人家里的大道上開(kāi)著車。去那些我從來(lái)沒(méi)去過(guò)的鎮(zhèn)子。認(rèn)識(shí)一些我從不認(rèn)識(shí)的人。以前我的生活圈子多么狹小。”
狹小這個(gè)字是無(wú)意說(shuō)出來(lái)的,可也沒(méi)什么。他沒(méi)有回應(yīng)說(shuō)他理解那種狹小,因?yàn)檫@么說(shuō)不是他的風(fēng)格。自教堂的那個(gè)星期天之后,他們逐漸熟知起來(lái),他說(shuō)他經(jīng)常想起她在她哥哥的首飾店給顧客買的東西打包的情形,有一年她也為他買給維奧萊特作生日禮物的手表打過(guò)包。他還想象她晚間放下櫥窗的格柵,鎖上店門(mén),上樓與哥哥一家坐在一起的情形。婚后她對(duì)他說(shuō)了好多事:她的大半輩子都是怎么過(guò)來(lái)的,唯有那群雞是屬于她的。“穿得很漂亮。”在說(shuō)到這個(gè)被他拒絕的女人還跟個(gè)姑娘似的時(shí)候,維奧萊特加了一句。
沒(méi)有什么蜜月,但是幾個(gè)月之后,他尋思這樣跑東跑西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是不是太累了,于是他把她帶到一個(gè)海濱勝地,這地方他和維奧萊特來(lái)過(guò)好多次,一待就是一星期。他們住在同一個(gè)家庭旅館——桑·蘇西,漫步于長(zhǎng)長(zhǎng)的、空蕩蕩的海濱大道,漫步于云雀在倒掛金鐘間竄來(lái)竄去的巷子,還有那些懸崖。他們?cè)隈R雷的酒館里喝酒。他們躺在秋日陽(yáng)光下的沙丘上。
“你真好,還想得到這個(gè)。”貝爾朝他微笑,很高興,因?yàn)樗M鞓?lè)。
“為這個(gè)冬天養(yǎng)精蓄銳,貝爾。”

她明白,這對(duì)于他來(lái)說(shuō)不容易。他們來(lái)這兒是因?yàn)樗徽J(rèn)識(shí)別的地方,出發(fā)前他就知道到了這里以后他會(huì)有一場(chǎng)情緒的波動(dòng)。她已經(jīng)從他的臉上看出來(lái)了,那是為了她的一種堅(jiān)忍。私下里,他被大海和海草的氣息所觸動(dòng),背負(fù)著背叛的內(nèi)疚。家庭旅館里的那些聲響是維奧萊特也聽(tīng)到過(guò)的。對(duì)于維奧萊特而言,那杜鵑花的香味同樣也綿延到十月。是維奧萊特第一個(gè)說(shuō)起沐浴―個(gè)星期的秋日陽(yáng)光會(huì)讓他們?yōu)檫@個(gè)冬天養(yǎng)精蓄銳:在他說(shuō)出這句話的片刻,可以在他臉上看出這一點(diǎn)。
“我要告訴你咱們的計(jì)劃,”他說(shuō),“回去以后,要給你買臺(tái)電視機(jī),貝爾。”
“哦,可你——”
“反正你會(huì)說(shuō)給我聽(tīng)的。”
說(shuō)這話的時(shí)候,他們正走在岬上的燈塔附近。他應(yīng)該跟維奧萊特說(shuō)過(guò)給她買電視機(jī)的,但維奧萊特準(zhǔn)是說(shuō)她可不想要這玩意兒。永遠(yuǎn)也不會(huì)打開(kāi)的,她多半是這么辯解的;不管怎樣,那玩意兒只會(huì)讓你變傻。
“你對(duì)我真好。”這是貝爾說(shuō)的話。
“啊不,不。”
他們快到燈塔的時(shí)候,他叫了一聲,一個(gè)男人從窗戶那兒應(yīng)了一句。“稍等。”那人說(shuō)道,他打開(kāi)門(mén)的時(shí)候,一定猜到他認(rèn)識(shí)的那位妻子已經(jīng)去世了。他們進(jìn)了屋,說(shuō)到故人與再婚,他提議道:“來(lái)一杯怎么樣?”主人倒上威士忌,三只玻璃杯舉起來(lái)致意的時(shí)候,貝爾感覺(jué)這是在向她致敬,雖然沒(méi)有人這么說(shuō)。回家庭旅館的路上下起了雨,假期的最后一晚了。
“冬天很合適,”第二天她冒雨駕著車,雨就沒(méi)停過(guò),他說(shuō)道,“電視機(jī)。”
電視機(jī)買來(lái)了,放在廚房隔壁那間原來(lái)被叫做起居室的小房間里。他們大多時(shí)候就坐在這里,收音機(jī)也在這里。電視機(jī)買來(lái)兩個(gè)星期后,貝爾弄來(lái)一條小小的黑色牧羊犬,那是一個(gè)農(nóng)夫不想要了的,因?yàn)樗卵颉_@條狗就成了她的,而且一直就被叫做“她的”。她喂它食,照顧它。她把它放在車?yán)铮瑤е教幾摺K€給它取了個(gè)新名字“瑪吉”,一叫它就會(huì)答應(yīng)。
即便有了狗和電視機(jī),家里添置也扔了一些東西,丈夫這么真誠(chéng)地愛(ài)她,告訴她她很好,對(duì)于貝爾來(lái)說(shuō),一切依然如舊。那個(gè)挽著她丈夫胳膊那么久的女人,那個(gè)帶著他走家串戶,讓他小心擺弄鋼琴,讓鋼琴起死回生的女人依然宣告著她的存在。她不像一個(gè)討厭的幽靈,讓無(wú)情的幻覺(jué)似有似無(wú),而是將她的一部分附在了她所愛(ài)的這個(gè)男人身上。
歐文·德羅姆古爾德敏感的地方是別人沒(méi)有的,他仍舊覺(jué)察出他第二個(gè)妻子的不自在。她知道他感覺(jué)得出來(lái)。這便是為什么他提出不再工作,為什么他要帶她去維奧萊特也去過(guò)的海濱,忍受著背叛的內(nèi)疚,為什么如今會(huì)有一臺(tái)電視機(jī),還有一條牧羊犬。他已經(jīng)猜到她為何要重漆廚房那扇門(mén)。他懷著驕傲,與一個(gè)認(rèn)識(shí)維奧萊特的男人一起,對(duì)她高高舉起酒杯。他懷著驕傲,與她一起坐在家庭旅館的餐廳還有馬雷酒館里。
貝爾叫自己記住這一切。她叫自己回想在燈塔里的小廚里拿出的那瓶John Jameson,回憶著家庭旅館里的聲響。他知道,他竭盡全力地寬慰她;他的愛(ài)無(wú)微不至。可是,維奧萊特會(huì)告訴他哪些葉子在變顏色。維奧萊特會(huì)向他報(bào)告潮水是漲了還是退了,貝爾意識(shí)到這一切已經(jīng)太晚。維奧萊特就是瞎子丈夫的眼睛。維奧萊特沒(méi)有給她留下透氣的余地。
一天,他們正駛離他們?nèi)ミ^(guò)的最遠(yuǎn)的一戶人家,那地方貝爾還是頭一次去,他說(shuō):
“你以前見(jiàn)過(guò)那樣一間陰沉沉的屋子嗎?是不是掛著圣像的關(guān)系呢?”
貝爾倒好車,筆直開(kāi),緩緩地通過(guò)那道三十年來(lái)不曾加寬的大門(mén)。
“陰沉沉?”她將車開(kāi)到一條像是河床的窄路上,盡量繞著路上的凹坑迂回前進(jìn)。
“以前我們懷疑,會(huì)不會(huì)是因?yàn)樗麄儾幌胗孟駢埬菢硬噬臇|西,以免對(duì)那些圣像有失敬意。”
貝爾不置一詞。她把沃克斯豪爾汽車安然開(kāi)上柏油路,又默不作聲地開(kāi)過(guò)一大片泥塘。格雷納罕太太家放鋼琴的那間屋子里的圣像仿佛歷歷在目。壁爐架和拐角一個(gè)書(shū)架上擺著些雕塑。格雷納罕太太把茶水和點(diǎn)心端進(jìn)那間憂郁的小屋,聲音壓得低低的,仿佛圣人們要求她那樣。

“什么像?”貝爾頭也沒(méi)回地問(wèn)道,盡管她可以回一下頭,因?yàn)榍胺郊葲](méi)有其他車輛也沒(méi)有泥塘。
“那些畫(huà)不再掛在那里了嗎?那屋子不是掛滿了圣像嗎?”
“他們一定是取下來(lái)了。”
“那現(xiàn)在那兒掛的是什么?”
貝爾略微加快了車速。她說(shuō)不知打哪兒竄出一只狐貍,穿過(guò)馬路跑到左邊去了。現(xiàn)在還站在那里呢,她說(shuō),狐貍都那樣。
“你是不是想停下車去看看,貝爾?”
“不,不,它現(xiàn)在跑了。那架鋼琴以前是格雷納罕太太的女兒在彈嗎?”
“哦,是的。她有好些年沒(méi)見(jiàn)著女兒了。過(guò)去我們說(shuō)是那些個(gè)圣像把她嚇走的。現(xiàn)在墻上是什么樣子?”
“條紋墻紙。”貝爾又加了一句,“壁爐架上有一張她女兒的照片。”
過(guò)了些日子,有一天,他說(shuō)起米納的修道院里有個(gè)修女,紅紅的兩腮就跟熟透的蘋(píng)果似的,貝爾卻說(shuō),最近那修女臉色白得像粉筆,面孔病懨懨的,都凹下去了。“這么說(shuō),她是病了。”他說(shuō)。
突然間,貝爾壯了膽子,也不管別人會(huì)怎么想,將維奧萊特種在屋后花壇里的植物拔了個(gè)精光,全都種上草。她告訴丈夫杜西加油站里的變化:德士古取代了埃索。她描述著德士古的標(biāo)識(shí),那顆大大的紅星還有組成這個(gè)詞的幾個(gè)字母都是怎么排列的。她避免在杜西加油站停車,以免發(fā)生攀談聊天,省得他問(wèn)杜西是不是賣埃索汽油讓他虧本了,或者別的什么。“哦,不,實(shí)際上,我想那不是銀的,”貝爾說(shuō)的是巴納高姆大宅大廳里的那只孔雀,“要是他們把它擦干凈了,我敢說(shuō)那底下是銅的。”樓上兩頭的那兩張沙發(fā)松垮垮地套上了新的罩子,上面是一束束五顏六色的菊花。“哦,不,不瘦,我覺(jué)得他不瘦,”貝爾拿著她丈夫父親的照片說(shuō)道,“一張壯實(shí)的臉,我想說(shuō)。”那個(gè)牙齒曾被形容為一陣大風(fēng)似的學(xué)校老師,如今差不多是一口假牙,笑起來(lái)很莊重。麥克科迪家亮白色的外墻飽經(jīng)風(fēng)霜,差不多都可以說(shuō)是灰色的了。“是勿忘我那樣的藍(lán),”有天貝爾說(shuō)到山的顏色,那天的天氣將群山襯得很藍(lán),“你簡(jiǎn)直難以置信。”從此,鋼琴調(diào)音師家里不再管山的藍(lán)色叫煙一樣的淡藍(lán)。
歐文·德羅姆古爾德的手指在樹(shù)皮上飛快地掠過(guò)。他分辨得出那些形態(tài)各異的葉子;他分辨得出荊豆與黑莓的刺。他根據(jù)鳴叫分辨鳥(niǎo)兒,聽(tīng)著吠叫分辨狗兒,還能根據(jù)腿間的觸碰分辨那些貓兒。他知道墓碑上的那些字,管風(fēng)琴上的那些音栓,還有他小提琴上的按弦。他知道什么是紅色,認(rèn)識(shí)冬青樹(shù)和栒子樹(shù)上的漿果。他還聞得出薰衣草和百里香的氣味。
這一切,從他身上是奪不走的。要是一夜間廚房門(mén)把手的紅漆掉落了,那沒(méi)有什么要緊。要是廚房里傳來(lái)他過(guò)去不曾聽(tīng)到的瓷燈罩打碎的聲響,那也沒(méi)什么要緊,要緊的是某種如同夢(mèng)一樣脆弱的東西受到了傷害。

他選擇的第一個(gè)妻子衣著邋遢:從沉默和變化的語(yǔ)調(diào)中——不僅僅是從話語(yǔ)間——他現(xiàn)在知道了。她的灰發(fā)亂糟糟地散在肩膀上,背還有點(diǎn)駝。他戳戳點(diǎn)點(diǎn)地走路,這一對(duì)沉浸在永恒幸福中的老兩口,一路走來(lái),看上去比實(shí)際要老。她連只蒼蠅也不會(huì)打,她不是那種會(huì)叫人嫉妒的人,當(dāng)然,老是擺脫不了昔日那幸福的陰影,老是要跟昔日的那種純樸較勁,對(duì)于一個(gè)新任的妻子來(lái)說(shuō)也著實(shí)是折磨。他把自己交給了兩個(gè)女人;他還沒(méi)有從第一個(gè)那里抽離出來(lái),也沒(méi)有從第二個(gè)這里離開(kāi)。
每個(gè)有鋼琴的人家都跟過(guò)去大相徑庭了。珀蒂爾太太戴的珍珠項(xiàng)鏈?zhǔn)堑鞍资模账寄莻€(gè)文具商蒼白的皮膚上長(zhǎng)滿了雀斑。奧基山上那兩排橡樹(shù)真的是山毛櫸嗎?“當(dāng)然了,當(dāng)然了。”歐文·德羅姆古爾德同意了,因?yàn)樗挥羞@樣做才公平。不能責(zé)怪貝爾提出自己的主張,要不是受到了傷害與破壞,這些主張也不會(huì)提出來(lái)。貝爾贏得了結(jié)局,因?yàn)樯呖偸勤A家。而這似乎也是公平的,因?yàn)榫S奧萊特贏了開(kāi)局,并且度過(guò)了更為美好的歲月。
賞析
威廉·特雷弗被譽(yù)為愛(ài)爾蘭的契訶夫,不僅是上世紀(jì)成就斐然的愛(ài)爾蘭小說(shuō)家,也常常被稱為當(dāng)代最偉大的英語(yǔ)小說(shuō)家。雖然年近不惑才開(kāi)始全職寫(xiě)作,但他在人生的后四十年中,創(chuàng)作了大量?jī)?yōu)美、傷感、富含詩(shī)意的長(zhǎng)短篇小說(shuō)。如同契訶夫一般,特雷弗的作品也往往關(guān)注生活中的配角人物:年長(zhǎng)者,大齡單身男女,或婚姻不幸福的人群。在這篇《鋼琴調(diào)音師的妻子們》中,特雷弗選擇了一位失明的調(diào)音師與他的先后兩任妻子作為主角。雖然近兩年出現(xiàn)了大熱電影《調(diào)音師》,但通常情況下一位年長(zhǎng)體弱的盲人調(diào)音師大概難以成為故事的主角。更別提他與兩任妻子都可算是循規(guī)蹈矩,沒(méi)做過(guò)任何令人大吃一驚或引人非議的事情。既不是值得紀(jì)念的好人,也沒(méi)有敗壞道德,他們不過(guò)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但在特雷弗的筆下,普通人也有了存在的意義,普通人的內(nèi)心同樣千回百轉(zhuǎn),普通人對(duì)周遭世界的感知同樣敏銳。看似無(wú)關(guān)痛癢的微小細(xì)節(jié)被特雷弗仔細(xì)分解,讓讀者見(jiàn)到普通人隱秘而豐富的內(nèi)心,同時(shí)進(jìn)一步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
特雷弗在敘事過(guò)程中,不斷切換視角,穿插描寫(xiě)過(guò)去與現(xiàn)在,這種手法營(yíng)造出一種略微混亂的美感。如同一段回憶、一場(chǎng)對(duì)話或者一個(gè)夢(mèng)境,總是有點(diǎn)沒(méi)頭沒(méi)尾、次序顛倒。因?yàn)橹鹘鞘敲と耍谑翘乩赘ゼ尤肓嗽S多對(duì)顏色、聲音、質(zhì)地的描寫(xiě),加深了小說(shuō)的夢(mèng)幻色彩。對(duì)于旁觀者來(lái)說(shuō),盲人與他的妻子們無(wú)外乎是相互協(xié)作的團(tuán)隊(duì)伙伴,她照顧他的起居,他為她提供居所。但對(duì)于局內(nèi)人,他們的協(xié)作有更深刻的內(nèi)涵。調(diào)音師的妻子便是他的雙眼,而妻子從調(diào)音師處得到的是全身心的愛(ài)與信任。他借由妻子的眼睛和描述來(lái)得知眼前的風(fēng)景,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他的熟人。
當(dāng)?shù)谝蝗纹拮尤ナ溃诙纹拮咏庸芩纳睿{(diào)音師所熟悉的畫(huà)面和人物突然之間全都變了。山巒不再是“煙一樣的淡藍(lán)”,而是變成了“勿忘我那樣的藍(lán)”。銀孔雀變成了銅孔雀,面頰紅潤(rùn)的修女變成了病懨懨的樣子,就連他自己的父親也從瘦子變成了壯漢……調(diào)音師無(wú)法自行分辨孰是孰非,卻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遠(yuǎn)離與第一任妻子共同塑造的世界。第二任妻子的不滿也從細(xì)節(jié)中體現(xiàn)出來(lái),她照顧好前妻留下的花草,最后又把它們連根拔起。調(diào)音師的傷感與第二任妻子的矛盾心理被特雷弗巧妙地捕捉。哪怕是作為普通人的我們,無(wú)力影響世界的進(jìn)程,但仍能擁有屬于自己的主觀世界,同樣細(xì)膩多彩。
文/ Vicky
——為鋼琴獨(dú)奏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