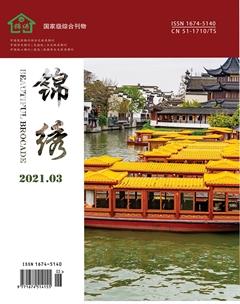降低環境侵權責任“入圍底線”的兩種途徑
楊明華 王致民
摘要:環境侵權的特殊性使得處于弱勢方的被害人因舉證能力有限,通常得不到完整的救濟。實踐中,處于資源優勢的加害人,往往以其排污達到當地的排污標準證明其行為不具有違法性,進而推卸環境侵權責任。降低環境侵權責任的“入圍底線”已經成為國際環境侵權救濟趨勢。本文擬通過明確排污達標與否與行為是否違法的無關性以及明確違法性并不是環境侵權責任構成的必要要件兩種途徑,降低環境侵權責任的“入圍底線”,為更大程度上實現被害人權利救濟及污染防治提供理論支持。
關鍵詞:排污標準;違法性;環境侵權;責任構成
一、問題之提出——以排污為切入
排污是否達標所依據的排污標準的性質是什么?排污標準是否可以成為違法性判斷的標準?環境侵權較之一般侵權的有哪些特殊性?違法性是否是環境侵權責任構成的必要要件?這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環境侵權責任“入圍底線”的問題,換言之,如何在現有法律體系內降低環境侵權責任“入圍底線”就成為實現對公眾利益保障的當務之急。
筆者認為,降低環境侵權責任“入圍底線”途徑有二,符合其中任何一條都應該認定施害方的環境侵權責任,以下將詳述之。
二、途徑一:排污標準與行為違法性的非必要聯系
(一)排污標準的地位界定
排污標準,就規范意義而言,屬于行政規范范疇,是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決定排污單位是否需要繳納排污費和進行環境管理的依據,其制定目的在于為行政執法提供依據,限制行政機關的活動范圍,確立行為人的行政責任。排污標準本身不屬于法,與法規和規章在制定程序、內容構成和編排體例以及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不同。
首先,排污標準是按照《環境標準管理辦法》規定的程序而不是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其次,排污標準的內容構成和編排體例采用了類似于“行政規范性文件”的體例風格,并不同于成文法的卷、編、章、節、條、款、項、目。再次,排污標準沒有法律規范的完整結構,也無獨立的法律意義,只有當其被環境立法中的準用性法律規范援引時,排污標準與援引的準用性環境法律規范相結合才能構成完整的環境法律規范,此時排污標準通過環境立法的援引而被賦予相應的法律效力。1
(二)排污達標與否不能成為行為違法與否的判定標準
在環境侵權案件的司法實踐中,致害企業往往依據地方環保部門制定的排污標準以及企業對排放物的檢驗鑒定結果提出反證,企圖以此證明行為并未違法,試圖逃避法律追究。不僅是實踐中,理論上我們很容易把環境標準誤認為是法律的一種,把它也視為環境法的淵源,進而把排污標準視做判定環境行為是否合法的準則。其實,排污標準的非法律屬性以及制定的局限性決定排污達標不能成為行為違法與否判定標準。
第一:排污標準的非法律性是其不能成為行為違法與否判定標準的本質因素。如上所述,排污標準是它只是屬于有權制定行政規章的行政主體制定的不屬于法規和規章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其本身并不具有法律屬性,而違法性是法學術語,認定也需要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規范,行政規范性文件無權對違法性做出判定。只有當其被環境立法中的準用性法律規范援引時,排污標準與援引的準用性環境法律規范相結合才能構成完整的環境法律規范,此時排污標準通過環境立法的援引而被賦予相應的法律效力,才能和援引的準用性環境法律規范相結合判定環境行為是否合法。
第二:排污標準制定的局限性是其不能成為行為違法與否判定標準的現實因素。首先,排污標準的制定要受到科技發展水平的制約。環境污染往往具有復雜性、滯后性和科學上的不確定性等特征,而排污標準的制定是基于當時的科技水平。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新的環境污染問題就會呈現,之前制定的排污標準就失去了科學性。第二,排污標準的制定還要受到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排污標準不能不顧此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現狀,而制訂高于經濟基礎可以承受排污標準,否則要么嚴重阻礙當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么是這樣的標準根本得不到切實的實施和遵守。
第三:排污標準雖然是考慮區域差異性由地方制定并用于地方,但在地區仍然具有普遍性,必須是一個地區平均化的標準,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缺乏靈活性和針對性。相比較之下,違法性是客觀層面的概念,除了法律的規范以外,不應該受其他因素左右,而排污標準是由人制定的,由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標準本身可能會錯誤,符合標準的也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危險,同時,排污標準的制定并非純粹的科學判斷過程,而是摻雜了諸多考量因素的評估過程,也不能準確反映排污時的具體情形。以排污達標作為違法性判定標準,勢必會導致認定結果不統一。
三、途徑二:違法性并不是環境侵權責任構成的必要要件
(一)環境侵權的特殊性
環境污染侵權行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權行為的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有別于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環境污染侵權行為的特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主體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環境污染侵權行為中當事人雙方力懸殊巨大,受害害人多為欠缺規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農民、漁民或市民,無論在專業技能、經濟實力還是社會動員力上都與作為公司、企業集團甚至跨國公司的加害人相差懸殊。
(二)侵害過程的間接性、復合性
環境侵害的結果往往是“由于重金屬、化學物質、煙塵等物質長期微量排出,經由大氣、水體等環境介質發生擴散、遷移、轉化、積累、富集等復雜的物理、化學、生物或生物化學變化” 2而形成,加害人的加害行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財產之上,而是通過“環境”這一中介物,對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損害,其過程表現出極為明顯的間接性和復合型。
(三)損害結果的持續性、潛伏性
污染物的不斷排放,其損害后果也將持續出現,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損害也不會立即消失,而會在環境中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尤其是疾病,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時發現,常常要潛伏很長時間,即使發現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
總之,環境污染本身具有間接性、積累性、潛伏性、長期性、滯后性的特點,導致其侵害主體眾多、侵害范圍廣、證據難以收集、侵害過程難以發覺。正是由于科技的飛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環境問題的危機,加之環境侵權的特點,決定了環境侵權作為特殊侵權需要加大排污企業的責任,降低受害人的舉證責任等標準,如上文所討論,達標排污作為致害企業訴稱其合法最常見的抗辯理由,因其不是違法性與否的判定標準已經被否決。
(二)違法性與環境侵權責任構成
依據侵權法理論,一般侵權責任由行為的違法性、損害結果、違法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主觀上具有過錯四個要件構成。如上文所述,環境污染侵權作為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因加害主體的不特定性、原因多樣性、因果關系復雜性等特點,其構成要件具有特殊性。環境污染侵權實行無過錯原則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救濟環境污染受害者,懲治污染者,達到防治污染保護環境的社會效果,已經被立法所明確和學者所共識。問題是,違法性是否是環境侵權責任構成的必要要件,還有很大的爭議。
1、立法的模糊性
環境污染責任的成立,是否須以污染環境的行為具有違法性為要件,法律上所涉及這一問題的規定有三處:其一,《民法通則》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其二,《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其三,《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2、學者的違法性要件之爭
由于立法的重復性和模糊性,現關于違法性是否是環境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學者存在三種學說:其一,違法性要件不要說。該說從《環境保護法》第41條以及《侵權責任法》第65條的規定出發,主張違法性不應作環境污染責任的構成要件,即使污染環境的行為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造成了他人損害,也應當承當賠償責任。3。其二,違法性要件必要說。該說又分為狹義違法性要件說和廣義違法性要件說兩種。其中,狹義違法性要件說主張污染環境的行為沒有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即不具有違法性,不承擔環境污染責任 。4廣義違法性要件說則主張,環境污染責任應當以具有違法性為要件,但是對何為違法性,又有不同理解,一種觀點( 結果違法說) 認為,排污行為違反了保護他人生命健康權的法律規定,產生了侵害他人人身權 財產權的結果,就意味著此種排污行為具有違法性;5還有一種觀點( 實質違法說) 認為,違法性中的“ 法”既包括法律規范,也包括民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但并非具體的某項排污標準。6其三,區別對待說。該說認為環境污染責任有時具有違法性,有時又不具有違法性,即污染環境的行為一般情況下是違反法律規定的,但是特殊情況下即使沒有違反法律規定也應當要求加害人承擔責任。7就目前的環境危機以及環境侵權救濟的情況而言,筆者的觀點是違法性不應該是環境侵權的責任構成要件。
3、違法性不應該是環境侵權的責任構成要件
環境侵權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其責任構成只需具備存在環境污染的致害行為、 環境污染造成損害、結果環境污染的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不考慮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和行為的違法性。具體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危險責任是違法性不應該成為環境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理論基礎。環境污染責任并非一般的過錯責任,而是一種危險責任。危險責任的宗旨并不是禁止危險活動的存在,也不是懲罰加害人,而是基于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的觀念,將伴隨一定危險但對社會有益的活動所生的損害,令危險的創造者或危險源的支配者負擔,從而將不幸損害予以合理分配。因此,危險責任的成立并不以違法性為要件,這些危險活動為社會允許,自始非屬違法性判斷的客體,也不得因事后發生損害結果而認定危險活動具有違法性。
第二,《侵權責任法》第65條是違法性不應該成為環境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法律基礎。《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從字面以及立法者的目的來看,立法只考慮了造成損害發生,并沒有將違法性作為環境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雖然,在《民法通則》以及《環境保護法》有不同的規定,但結合該條文義及我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如果《侵權責任法》和其他法律就同一事項都有規定,則按“新法優于舊法”的規則適用《侵權責任法》;如果其他法律就不同事項作了規定而《侵權責任法》沒有規定,則按“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規則,適用其他法律。因此,就環境污染責任的構成,《侵權責任法》和《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環境特別法都有規定,但規定不同,則應依“新舊優于舊法”的規則而適用《侵權責任法》。
第三,環境侵權救濟現狀是違法性不應該成為環境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實踐基礎。環境污染是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不可避免的衍生品,隨著社會和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日益嚴重。環境侵權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的侵權方式,而在司法實踐中,對被害人的救濟還遠遠不夠。原因之一是,環境污染本身具有間接性、積累性、潛伏性、長期性、滯后性的特點,加之原告沒有足夠的舉證責任能力,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承擔著更大的敗訴風險。原因之二是我國現行的法律對環境民事侵權訴訟采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舉證責任倒置并不意味著原告無需承擔舉證義務,其仍需就致害方存在環境污染的致害行為以及環境污染造成損害結果承擔舉證責任,并且原告完成舉證責任是舉證負擔向被告轉移的前提,此項舉證義務仍然位于原告企及的范圍之外。鑒于此,增加環境加害人的義務,降低受害人的責任已經成為為國際趨勢。同樣的,降低環境侵權的“入圍底線”,即行為的違法性不作為環境侵權責任的必要構成要件也是增加環境加害人的義務,降低受害人的責任的一種方式。此舉,對警示企業的環保意識、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降低被害人的救濟標準,更大利益的救濟被害人、懲治環境污染者,達到防治污染保護環境的社會效果均有重要意義。
四、結語
降低環境侵權責任的“入圍底線”已經成為國際環境侵權救濟趨勢。通過明確排污達標與否與行為是否違法的無關性以及明確違法性并不是環境侵權責任構成的必要要件兩種途徑,降低環境侵權責任的“入圍底線”,更大利益的救濟被害人、懲治環境污染者,達到防治污染、保護環境的社會效果。
參考文獻
[1]楊朝霞.達標排污也要承擔法律責任么?[J].環境教育,2010(7):45.
[2]李彩虹.環境污染訴訟:原告無法完成的舉證[J].法學雜志,2010(10):133-135.
[3]金瑞林,汪勁.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94.
[4]王家福.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515.
[5]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55.
[6]曹明德.環境侵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66—169.
[7]劉士國.現代侵權損害賠償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09—213.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上海?20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