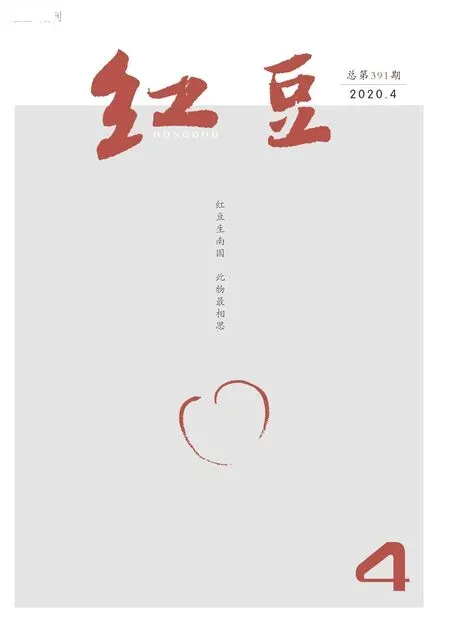色里逃禪
昨夜雨
昨夜雨,我讀《十七帖》。江淮之間的夏天又濕又熱,也漫長,人仿佛久在蒸籠之中,易煩悶、焦躁,元神也容易耗散。幸好有梅雨。雨以梅為名,既是寫實,也足見古人風致。每年吾鄉黃梅子熟時,黃梅雨必如約而來,或落或歇,或密或疏,或晨昏或日中或夜半,有時太陽雨,有時東邊日出西邊雨,有時雨夾著冰雹,小性子捉摸不定如林黛玉。孩子們出門,大人每每叮囑要帶把傘,但孩子們都是孫悟空轉世,更愿意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常常淋一頭一身的雨,雖然如此,眉眼里卻有叛逆得逞的快樂。
梅雨可以殺山中毛蟲、田中稻虱,可以澆灌田園,當然更可以消暑。雨意淋漓,又挾涼風,山中氣溫二十八度上下,是很安逸的。此季草木肥綠狂野,我的父母在院墻外的枸骨冬青旁邊種了十幾株番茄,幾日不見,青果已然累累杯蓋大,似乎是偷著長的。我曾在浙江常山吃過青番茄炒臘肉,顏色嬌美味道清芬,所以我建議母親試一試,她愕然如同聽說石頭生子。在她的傳統觀念里,青番茄酸得令人淌尿,斷不可食,更不能與肉同炒,番茄必待紅透了,切片放蛋花和蔥葉做湯才是正宗。鄉人篤厚,老實得過分,于做菜也可見一斑。祖宗傳下來的菜譜就像祖宗的牌位,輕易是動不得的。
我心也蔥蘢如草木,自覺元氣如綠液充盈于體內,可以讀幾頁古書,也可以寫一點文章。古書有石硯的靜氣、宣紙的溫軟,入眼即生清涼,即可以進入莊子所謂的虛室。人間多擾擾,也多是無事生非庸人自擾,書可以寧心靜神,令人坐忘而自得。這些年,無論如何忙碌、如何心躁,泡一杯茶,點一支煙,打開一本書,我瞬間就能進入槁木之境,心間簡素清白。《度人經》說“神風靜默,山海藏云,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以為人在書中,境界近似之。
書隨時可以讀,文章卻不是隨時可以寫的,得精力充沛、元氣飽滿,下筆才有氣象風云,否則虛弱干癟得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憎。寫文章真是有定數的,如同壽夭福禍,所以要惜福,精神狀態好時不可荒廢。前些天在九華山下,與幾個作家朋友夜里聊天,說起當代一些名家,自己埋頭苦寫,動輒捧出幾十萬、上百萬字的大部頭,卻屢屢誠懇勸誡年輕人要少寫,不知道是幾個意思。那晚大家笑得意味深長。我想起秋天的植物,哪怕是卑微如野草,也拼命借助風力和鳥獸,把它們的種子播撒四方。少寫,寫出絕妙好詞,固然是至理;多寫,于勤奮中悟道,卻是必由的路徑。古人習字,從未聽說要少寫的,只聽說王羲之讓兒子王獻之把十八口大缸里的水寫完。
回到《十七帖》。王右軍寫信給老友周撫:“頃與足下別廿六年,于今雖時書問,以解闊懷。省足下先后二書,但增嘆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帖中九百余字,所談大致如此,都是碎語閑言,也是碎玉屑金。相比《蘭亭集序》的風云際會、文采風流和死生興感,《十七帖》純然山家老翁語,有家常的親切和樸直,有衣飯氣息和美好的人間情味。憶起數年前在紹興蘭渚山下,當年書圣與諸賢曲水流觴處,與眾友持蟹鰲浮黃酒,醉夢中想見古人風采,以為前賢只飲山陰道上風月,不食人間煙火。讀《十七帖》,方知書圣也是肉體凡胎,喜生畏死,有常人的歡樂悲愁,有人生破綻。有一些破綻并非壞事,只要不是破綻百出,就像《蘭亭集序》里被涂改的字,后世寫字的人也奉為圭臬日夜摹仿。
古人傳世碑帖,自然都是神妙之品。大體上,碑如皇帝詔令,如祖宗家法,如廟宇中如來佛的金身塑像,法相莊嚴;帖如小橋流水,如蜂蝶亂飛,如番茄蛋湯,有溫度、有情義,有寒暖、溫涼、離聚、死生的人間細節。
色里逃禪
京郊有荒古氣息,像舊碑刻。陽光荒古,月色荒古,湖藍色的天空荒古,土地河流荒古,竹木鳥鳴荒古,薄薄的一層冬雪覆蓋在草野上,像竇線娘穿的那件白綾征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初,我在京郊順義縣后沙峪鎮小住數日,聽課、翹課、飲酒、喝茶、讀詩、寫作、做白日夢,或者在住所周邊閑逛,與三五人談文章世事,如手捏一根隱身草,得幾天世外逍遙。日覺一團混茫元氣在身體里摶轉,上沖天靈下撞涌泉,貫之于筆墨,得文章數千字。自以為文章有膽也有氣,如有鬼助神襄。
有飯、有茶、有閑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可以寫文章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鎮子離京城不過二十公里,卻偏僻,人家遙遠,燈火也稀疏,冷清得好,讓人不起一絲邪念。望不到邊際的原野,草蛇灰線,像無頭無尾綿延鋪展的史書,寓豐贍于簡淡,平實得好,也幽隱得好。夜間氣溫零下五六攝氏度,風很干也很大,割人的耳朵,月亮如一枚鋒利的指甲,也割人的耳朵。
如果待在酒店里不外出,暖氣吹人如春嵐,是很舒服的。不像在南方,那種無處可逃的濕寒,刺人肉、熬人骨。但每天早中晚,我都出門走走,雖然酒店周圍除了一群光禿禿的樹,一點殘雪,一面結著冰的小湖和湖里破冰游泳的白鵝、黑鴨,其實并無甚可看。好看的東西并不都在眼里,就像天天見到的人不一定是想見的人。
南方早就下過雪了,但我住在城里,并沒有見到雪。來北京的那天,恰好遇見北方下第一場雪,虛虛的一層白,像畫在古宣上,望過去有些古怪,不覺得清寒;就像北方的冷,奇怪的干冷,其實并不冷,只存一點冬天的意思;也像住在后沙峪的這些日子,遠離營營廛囂,卻并不覺得孤單。
昨天進城,去了國家典籍博物館看古書。殷商甲骨、敦煌遺書、金石拓片、古圖古畫、譜牒輿書,隔著厚厚的玻璃一個窗子接一個窗子細細地看。像我這樣嗜古籍成癖的人,眼放精光,心間花花綠綠,一如江洋大盜窺見黃金白銀、鳳冠冕旒,如登徒子闖見睡鄉里的絕代佳人。
在館中看見幾冊印譜,《錦囊印林四卷》,清代乾隆年間安徽歙縣人汪啟淑所輯,汪氏香雪亭刻鈐印本,白棉紙質,霜墓一樣的古氣奪人魂魄。打開的那一面,有四幀印文,一為“香雪亭”,一為“人之情也”,一為“休拘束”,一為“色里逃禪”。揣摩久之,以為可以這樣連著讀:“香雪亭色里逃禪,休拘束,人之情也。”人之初,性情本如飛鳥、淵魚、草蟲、木石,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尤喜“色里逃禪”四字,以為得大歡樂,差可比擬孫悟空在釋迦牟尼手掌中撒一泡猴尿,也遠比先賢所云“逃禪歸儒”有意味得多,也曠達得多。他年當請篆刻名家照樣刻一方印,出新書時蓋在上面送人。再刻一方初唐王績原創的“閑田牧豬”,或者“閑田騎豬”。
京郊多土地,閑田可牧豬也。人生多茍茍,色里可逃禪。
露水起
露水起了,夜已微涼,我趁著酒意臥在山溪邊濃密的草毯上,看曠野里螢火蟲明明滅滅,看天上遠古星辰幽幽冷冷。一鉤淡月躲在大山后面,像剛剛開臉的小媳婦,像山的白眉。耳邊只有流水,只有草蟲喓喓、嚶嚶、呤呤、唧唧。天地若絲桐,若笙簧,若石磬,若曾侯乙編鐘,若舞榭歌臺,若戲園子,若柳堤上唐虞時代的戀人相偎呢喃。急管繁弦,低吟淺唱;繁弦急管,淺唱低吟。良夜如良人,如斯,宜譜曲填詞,宜作世外之想,也宜走神念遠。
住在山中有山、山外有山的大別山里,混跡于草木昆蟲奔獸流水之間,日與日的變化極其細微,歲月溫吞光陰綿綿,又兼皮已厚肉已糙,我常常忘記人間易老。前夜讀唐人《化度寺碑》,見“泡電同奔”四字,心中一凜。比少年時初見《金剛經》中“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比弱冠時初聽蘇子說“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更加有所觸動。但是一夜春秋大夢之后,心間那一點驚悚消失得無影無蹤,日子依舊貌似轟轟然實則寂寂然地向前,我也早已習慣現世安穩。心理學有選擇性記憶一說,甚有道理,人的潛意識里的確有一道防御墻,自動遮蔽掉一些不愿意記起的事物。想起舊時鄉間的茅廁,門口掛著的那一條破麻袋。
月光與水流泄于石上,小蟲嘶語于草葉中,塵世的燈光近在一里之遙,又遠在天邊。疏離、安靜,天地有大美而蟲言之。夜色迷離而美好,仿佛是一件隱身衣,一身銅鎧甲。如果我愿意,可以脫得一絲不掛,到溪里游泳;可以在青草河堤上像原始人一樣披頭散發狂野地舞蹈;也可以想象自己變成了一只蟲子,豆丹、椿象、七星瓢蟲或者金鈴子,在草叢中蟄伏、嘶鳴、蹦跶、餐風飲露。想起來真叫人泄氣:人的肉身太重,人間的規矩又太多,人無論如何也做不了自由自在的蟲子,勉強算蟲子,也是科幻片中那類恐怖血腥的害人蟲。
有兩三年我耽于蟲子。夏秋兩季下班后,經常在單位后面的山谷中靜坐,或者輕手輕腳地閑走,只為了聽滿山谷的蟲鳴。那座山也叫花果山,雖然既無花也無果,但老松蔚茂、茅草披離,山谷中藏著萬千只蟲子,自下午至第二天清晨一直彈唱不休。有時獨奏,東隅一聲,西隅一聲,嘀嘀咕咕;有時對唱情歌,雄一言,雌一語,如《上邪》之誓;有時多聲部交響,疑是在大劇院的音樂廳里聽門德爾松。我尤其愛聽金鈴子,滴玲玲,滴玲玲,倏然破空而來,干凈清越如古謠曲,如萬串風鈴迎風脆響。那段時間,我為蟲子寫過二十來篇文章,名之為《昆蟲小語》,后來收入第一本文集。舊作雖不悔,大多可以棄,這些有草木氣、有生靈氣的文字,卻寶愛至今。
前些天與三五人小聚,席間聽人說,他特別討厭聽到蟬叫,因為太吵。回家翻出從前的文章,關于蟬我是這樣寫的:一只蟬就是一個哲學家。它住在高高的樹上,一幅天下云煙盡收眼底、萬千機變了然于胸的樣子,很是有些哲學的意味。沉默時,它紋絲不動,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唱歌時,它左一個“知了”右一個“知了”,仿佛世間事它無所不知。就連遭遇捕捉時,它撒一泡尿就走的從容姿態,也很是高蹈,近似兵法中的“走為上”。
想一想,舊時文章中有意氣、有生氣,也有逸氣,不似今日枯澀。
忽然念起王祥夫先生的工筆草蟲。王師是小說大匠,也是畫壇高手,性慷慨,酒量與度量并洪,酒后面色潮紅意氣風發,妙語似珠穿。我在筆會中見過兩次,敬其文章與畫藝,尤其傾慕其風采和為人。仲夏同游九華,在蓮花佛國下的青陽,酒兵之間,他和我說,他認識的姓儲的作家,一個是江蘇的儲福金,一個是安徽的儲勁松。我說,還有一個唐代的儲光羲。王師大樂,耳語云:酒后別走,有筆會,我給你寫字。果然有。王師贈我“聽松”二字,逸筆草草。仍然不滿足。其筆下的枇杷、青蛙、菖蒲、蓮藕、竹筍、蘑菇、草蟲、小鳥、凍秋梨,點染之間纖毫畢現,得風致、得神韻、得生意、得自然,我向往之久矣。師無奈,耳語云:酒后字畫都是狗屁。笑罷仍為我畫一魚,游弋紙上,骨骼歷歷,落款“珊瑚堂”。
昨日在微信上見王師畫枇杷小蟲,題曰:買畫者對予說,藤黃不貴哦,不像洋紅那樣貴,就多多畫幾個枇杷果給我哦。我說是的是的,藤黃不貴。便欣然命筆大畫枇杷,并奉送小蜜蜂一只。一時主客皆大歡喜。管它豬肉漲價幾何。
王師食葷茹素,言談亦葷亦素。葷素里有風情,有風概,有風月。以為他是草蟲幻化,一舉足一落筆,就到了宋元。
還是覺得他欠我一只蟲子。
責任編輯? ?韋毓泉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