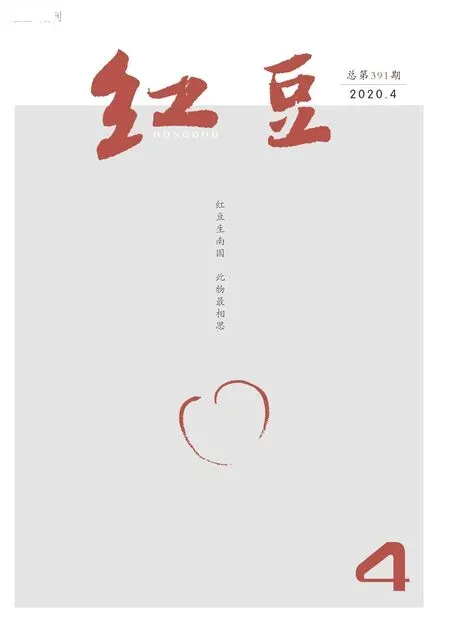吃粉
寧炳南
“粉”字,古已有之。《說文解字》說:“粉,所以傅面者也。從米、分聲。方吻切。”“粉”從米、從分,分亦聲。本義:米細(xì)末,亦指谷類、豆類作物子實(shí)的細(xì)末。現(xiàn)在我們有關(guān)“粉”的詞語大多來自它的本意。
我今天要說的“粉”是指廣西的“粉”。說到廣西,就不能不提“粉”;說到吃粉,就免不了要提廣西。粉,儼然成為廣西的一個(gè)標(biāo)識(shí)性的名片。因?yàn)樯裰荽蟮厣蠜]有哪個(gè)地方能像廣西這樣,有那么多種類、那么多口味的粉;也沒有哪片區(qū)域的人能像廣西人這樣,一天乃至數(shù)天,頓頓都能以粉為餐食;更沒有哪個(gè)地方的人能像廣西人這樣,愛吃粉,愛到魔怔的地步。
作為一名地道的廣西人,我當(dāng)然也是愛吃粉的。
人生中第一次吃粉的經(jīng)歷,要追溯到我的童年時(shí)代,那時(shí)應(yīng)該是五六歲的時(shí)候,印象中能吃到的粉的種類也僅三四種而已。一種是普通的水煮粉,一種是炒粉,另一種則是凍粉(俚語)。那個(gè)時(shí)候能吃上一頓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你得起得夠早。每天清晨,商販們騎著自行車?yán)洀拇孱^吆喝到村尾,五六點(diǎn)鐘一趟,十一二點(diǎn)鐘一趟,要是趕不上趟,就算你有錢,那也吃不上粉的。當(dāng)然了,這起早趕趟的事,是輪不到我們這些小屁孩操心的,自有早起的老一輩人來操持。故而就有人開始動(dòng)起了腦筋,既然今天買不到了,那就跟商販提前預(yù)定明天的,這樣村里人既能買到想買的,商販也能多掙錢,兩全其美。如果要是真的想吃,村里又買不到,那就只能到鎮(zhèn)上趕集去買了。
小的時(shí)候到鎮(zhèn)上趕集,最高興的事莫過于買上一件漂亮的衣服、一雙時(shí)髦的鞋子和吃上一碗鎮(zhèn)上的凍粉。鎮(zhèn)上的凍粉跟其他地方的粉還是有區(qū)別的。粉是用石磨將米碾磨成粉之后,加入店家的秘方,調(diào)制成米漿,再攤成薄如蟬翼、晶瑩剔透的粉皮,上籠蒸制,待蒸熟后取出攤涼,一片片細(xì)膩光滑的凍粉皮就制作成了。取一片凍粉皮切成條狀,大碗盛裝,淋上精心熬制的鹵汁、扣肉汁、牛肉汁混合而成的三汁,鋪上加入各種香料和配料熬制而成的扣肉或者牛肉,再點(diǎn)綴上時(shí)令蔬菜,一碗美味的凍粉就擺在了眼前。吸收了加入香料和配料熬制而成的扣肉肥而不膩,牛肉鮮嫩爽滑,真真讓人垂涎欲滴。這種味道畢生難忘,以致今天待在城市里還念念不忘小時(shí)候的味道,隔三岔五地就要找來吃。人們都說味蕾是有記憶的,看來還真的是沒說錯(cuò)。
一個(gè)人對(duì)一種食物的喜愛,除了靈魂深處的一種溫暖記憶的味蕾之外,還有一種是帶有沖擊感的精神上的刺激。這種精神上的刺激在我看來莫過于辣了。說起辣來,就不得不提螺螄粉了。
辣椒對(duì)中國來說是舶來品,最早關(guān)于辣椒的記載是明末高濂撰寫的《遵生八箋》,其中寫道:“番椒叢生,白花,果儼似禿筆頭,味辣色紅,甚可觀。”因此一般認(rèn)為,辣椒是在明末從美洲傳入中國的,起初只是作為觀賞植物和藥物,進(jìn)入中國菜譜的時(shí)間并不算太長(zhǎng)。而融入辣椒的螺螄粉最早出現(xiàn)在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末。二〇〇八年,柳州螺螄粉手工制作技藝才入選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第二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二〇二〇年,才被列入國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單。可以說歷史并不算長(zhǎng)。雖說其歷史不長(zhǎng),但其影響力卻非比尋常。隨著新冠肺炎疫情來襲,螺螄粉的國內(nèi)外的需求更是大漲,海外亞超更是“一粉難求”,真的是手快有手慢無。
說起我第一次吃螺螄粉,還是在大學(xué)期間。我從小就不吃辣,但這不吃辣的節(jié)奏在吃上螺螄粉之后就被徹底打破,甚至還在吃辣的道路上越走越遠(yuǎn),猶如游戲中升級(jí)打妖怪一樣,一路狂升不止。從不辣到微辣,從微辣到中辣,從中辣到加辣,再從加辣到變態(tài)辣,以致現(xiàn)在是到了無辣不歡的地步。二〇二〇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封閉家中,因?yàn)榧胰硕汲圆坏美保趪L遍了“平淡無味”的美食之后,精神上的刺激和味蕾上的誘引竟讓我自己煮起了螺螄粉來。如果沒有疫情,還真不知道對(duì)于螺螄粉,我居然有著近乎“癮君子”的習(xí)性。故而在吃螺螄粉這件事上,其帶來的精神上的沖擊感的刺激竟讓我無法言表。
當(dāng)然,除了螺螄粉之外,廣西還有老友粉、干撈粉、生料粉、生榨粉、鹵菜粉、牛巴粉、豬腳粉、酸辣粉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粉,不一而足。因?yàn)闊o論是在故土還是他鄉(xiāng),總會(huì)有一種記憶中的味道慰藉著我們的腸胃和心靈,可以讓味蕾記住我們所在的城市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
“粉”,從米、從分,看來我對(duì)“粉”這種美食是再也無法分開了。
責(zé)任編輯? ?謝? ?蓉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