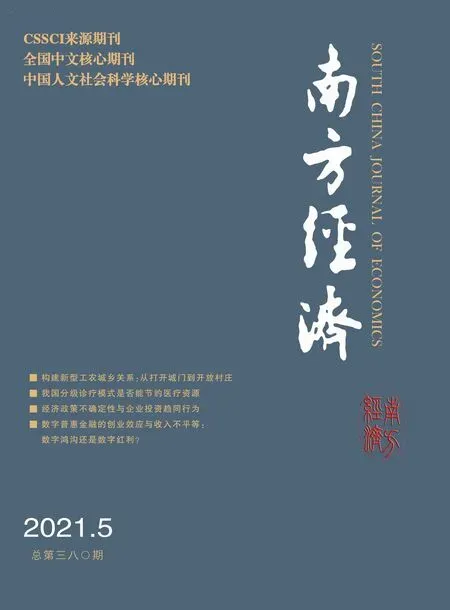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
——基于世界銀行對143個國家企業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
李 殷 劉 忠
關鍵字:微腐敗 生產率 內生性
一、引言
腐敗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世界銀行,2002)。腐敗作為一種全球性現象,世界各國一直致力于反腐敗斗爭。然而,根據透明國際組織最新發布的2020年全球腐敗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1)腐敗感知指數在2012年之前取值介于0至10之間,2012年起由于調整測算方法,取值變更為0至100之間。分數越高表示該國越清廉。,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超過三分之二國家的腐敗感知指數得分低于50分,屬于腐敗較嚴重的國家。以中國為例,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閉幕之后,中國發動了一場建國以來最嚴厲的反腐敗運動并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伴隨著一大批高官的落馬,大肆行賄、索賄等腐敗現象顯著減少,理論上中國的腐敗感知指數自2012年后應當逐年提升。然而,根據透明國際組織披露的中國腐敗感知指數發現,盡管2013年得分較2012年增加1分(即由39分上升為40分),但2014年相較2013年卻下降4分(即36分),到2020年中國的腐敗感知指數僅為42分,與阿根廷、科威特等四個國家并列排名第78位,仍屬于嚴重腐敗的國家,本文認為產生這一差異的原因可能與腐敗的大小相關。
世界銀行在將腐敗定義為政府官員“為牟取私利而濫用公共權力或權威的行為”的同時,還指出腐敗存在大小之分,即大腐敗(grand corruption)與微腐敗(petty corruption)(世界銀行,1997)。兩種腐敗存在著本質區別。根據定義,大腐敗參與主體通常是較高級別的政府官員、國際機構等,涉及的交易或金額龐大,通常會觸犯一國法律,是各國反腐敗斗爭的主要對象(Jain,2001;Mashali,2012;Jancsics,2013;Habiyaremye and Raymond,2013);而微腐敗,主要發生在企業或公眾與低級公職人員之間,涉及的金錢或交易規模小,發生范圍廣,通常游離于法律約束之外,在各國的反腐敗斗爭中往往被忽略(Djawadi and Fahr,2013;Jancsics,2013;Nguyen et al.,2016)。
微腐敗有多種表現形式,最典型的表現為企業或公眾為了好辦事而與低級別政府官員進行的金錢交易。這些好辦事包括納稅申報、免除監管、許可要求、基礎服務(如電話、天然氣、水、電等)、申請政府福利(如貸款、補貼等)或批準特權(如新公司注冊、工人安全、安全建筑標準、環境危害等)等多個方面(Kochanek,1993;Ariane et al.,2007;Clarke,2011;Mashali,2012)。與微腐敗概念相近的是亞腐敗,它同樣是一種介于廉潔和腐敗狀態之間的游離于法律邊緣的行為,如日常辦事過程中的請客送禮,打著人情禮儀幌子借婚喪嫁娶、添丁增歲收送節禮,公款揮霍浪費等現象都屬此列。但根據定義以及表現形式可知,無論是微腐敗還是亞腐敗,其本質都是一種權力尋租,即低級別的政府公職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身謀利益。因此,結合所使用的樣本數據特征,本文選擇從微腐敗的角度展開論述,并將微腐敗定義為較低級別的政府公職或公用事業單位人員通過主動向企業索取禮物或費用來牟取自身利益的行為。
不難發現,微腐敗滲透到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之其涉及利益微小,往往使社會公眾難以覺察。微腐敗的這種隱秘性,在很大程度上與特定的文化習俗有關。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關系型社會,“辦事找關系”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默認準則(李四海等,2015)。因此,從某種程度而言,一方面特定的文化習俗成為微腐敗的溫床;另一方面,部分微腐敗形式也是從某些文化習俗物化、異化而來的,如部分投機人利用節假日、紅白喜事等特殊時節給所求的公職人員送禮送錢等(李海濤,2020)。正因為與文化習俗的這種共生性,使得社會公眾形成了錯誤的認知,認為微腐敗并不違反法律,反而給自身帶來便利,從而默許并進一步效仿這種行為以“方便”行事。這些錯誤認知均在無形中助長了微腐敗的歪風邪氣。如果放任這種錯誤認知不加制止,微腐敗可能會發生質變成為大腐敗,最終對社會造成巨大危害。正如習總書記在中共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它損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
當前,在未區分大腐敗與微腐敗情形下,國內外學者已針對腐敗展開了豐富的研究。但Lambsdorf(2006)在總結腐敗產生的原因及后果后指出,區分微腐敗和大腐敗進行研究非常重要。由于微腐敗的度量不易,當前探究微腐敗經濟后果的實證研究較少。僅有的關于微腐敗經濟后果的研究結論還存在分歧(Habiyaremye and Raymond,2013;Vorley and Williams,2016;Nguyen et al.,2016)。并且,鮮有文獻探討微腐敗影響企業的路徑機制。基于此,本文利用包括中國在內的143個國家2002-2014年的企業層面的獨立混合截面數據(independently pooled cross section data),重點探究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微腐敗會顯著抑制企業生產率,這支持了微腐敗不利于企業的觀點。同時,在探尋影響機制過程中,本文發現微腐敗可通過抑制企業創新對企業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分子樣本討論時發現,私營企業、服務行業、位于腐敗程度高地區以及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企業的生產率受微腐敗的負面影響更大。
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有兩方面:一是現有文獻在探究腐敗及其影響時,鮮少區分大腐敗與微腐敗,但根據定義,這兩種腐敗存在本質區別。微腐敗由于涉及金額微小,往往使人忽略其可能產生的危害。本文借助世界銀行調查問卷構建衡量微腐敗的指標,然后在控制內生性問題條件下,基于工具變量方法證實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負面影響。二是已有研究腐敗經濟后果的文獻,較少探究其中的影響機制,本文首次嘗試從企業創新角度,探討微腐敗損害企業生產率的可能機制,這是對以往文獻的重要補充。
本文剩余結構安排如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說;第三章重點介紹數據來源、變量定義以及模型設定;第四章為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最后一章為結論與不足。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說
(一)微腐敗與企業生產率
鑒于圍繞微腐敗影響的實證研究較少,本文主要從腐敗的角度綜述現有關于腐敗影響企業的相關研究,從而為構建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的研究假說提供文獻支撐。目前,關于腐敗對企業經濟影響的研究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腐敗是“潤滑之手”(grease the wheels),有助于企業規避無效率的政府管制,從而提高其經濟效率。如Wang and You(2012)、Gander(2014)以及張璇等(2016)的研究發現腐敗可以促進企業成長;Dreher and Gassebner(2013)指出腐敗能顯著地提高企業家的創業活動,加速企業進入市場;Krammer(2013)認為腐敗是將創新產品引入市場的一種有效手段;黃玖立、李坤望(2013)指出,企業招待費支出越多,企業獲得的政府訂單和國有企業訂單越多。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腐敗是“掠奪之手”(sand the wheels),會扭曲企業的資源配置,阻礙企業效率的提升。如De Waldemar(2012)發現腐敗對企業產品的創新存在顯著負效應;Vu et al.(2018)基于越南企業的分析表明,腐敗會顯著降低企業的資產回報率;Bbaale and Okumu(2018)使用26個國家的世界銀行企業調查問卷的研究顯示,腐敗能夠降低企業勞動生產率;Cai et al.(2011)、De Rosa et al.(2015)的研究均發現,腐敗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存在顯著負效應;聶輝華等(2014)認為腐敗與企業TFP之間存在一種非單調關系。
參照以上論述,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產生何種影響將取決于“潤滑之手”與“掠奪之手”的程度,從而可能表現出正反兩種效果。然而,腐敗“潤滑之手”的觀點在理論與經驗上都遭到了一定批判。如Kaufmann and Wei(1999)發現行政官員出于謀求利益的動機可能會故意增加官僚程序,因此,腐敗并不能幫助企業減少應對官僚程序的時間。De Rosa et al.(2015)的研究顯示,“賄賂稅”(賄賂行政官員的支出)和“時間稅”(與行政官員打交道的時間)之間并不存在替代關系,賄賂并不能幫助企業規避繁瑣的監管規定從而得到次優效率。并且,在僅存的幾篇研究微腐敗對企業影響的實證文獻中,盡管Nguyen et al.(2016)基于越南企業的調查數據的研究結果發現,微腐敗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企業的創新;但Habiyaremye and Raymond(2013)利用世界銀行調查的東歐以及中、西亞30個轉型國家12000家企業的研究結果則顯示,無論是大腐敗還是微腐敗,均不利于東道國的企業創新;Vorley and Williams(2016)通過對保加利亞以及羅馬尼亞兩個國家部分企業家的訪談結果得出結論,微腐敗會顯著抑制企業家的積極性。此外,根據本文對微腐敗的定義,微腐敗是較低級別的政府公職或公用事業單位人員為謀取自身利益而向企業索取的好處,這本質是一種設租(rent creation)行為。設租會導致企業不得不支出相應的尋租成本。基于此,本文認為微腐敗將更多發揮“掠奪之手”來影響企業生產率,從而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微腐敗會降低企業生產率。
(二)微腐敗、研發創新與企業生產率
Baumol(1990)將企業家活動分為生產性、非生產性以及破壞性活動三類。其中,生產性(productive)活動主要指企業家日常的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還包括企業的研發創新等活動,是一種創造利潤的過程;而非生產性(unproductive)活動主要涉及多種尋求租金(rent-seeking)的活動,如公關、招待、游說等,是一種財富再分配過程。企業家活動配置是指在約束條件下,企業家如何將有限的資源(比如時間和金錢)在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活動之間進行分配的過程(何軒等,2016)。一個理性的企業家會將自己有限的時間精力分配到能夠給其帶來最大收益的活動中去。因此,本文認為微腐敗可能基于以下原因促使企業決策者從事更多的非生產性經營活動,從而造成對企業研發創新等生產性經營活動的擠出,最終負面影響企業生產率。
一方面,微腐敗的產生往往與市場制度不完善密切相關。市場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各級政府公職人員在不同程度上擁有重新分配資源和自由裁量的權力,從而為這些公職人員牟取私利提供了便利。當公職人員主動設租時,企業為了好辦事將“積極”與這些公職人員打交道,進行公關、招待以及賄賂等非生產性活動,進而擠壓其對生產性經營活動的投入(何軒等,2016)。此外,根據定義,微腐敗僅涉及小額交易,對于參與微腐敗的企業而言,微腐敗的支出可能只占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支出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企業可能通過微腐敗與各類公職人員建立聯系,從而獲得諸如加速許可證的審批流程或者減少稅收監管等好處。因此,參與微腐敗行為的低成本性,相對于其它能夠帶給企業收益但需要較高投入成本的生產性活動而言,企業決策者可能更愿意通過低成本的微腐敗來獲取相應的利益,從而造成對生產性經營活動的擠出。已有研究證實了上述推測,黨力等(2016)在研究中國反腐敗與企業創新關系時指出,造成中國企業創新能力較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企業進行腐敗的成本較低,企業可通過與政府建立特殊的政治關聯來獲取利潤,而不愿意通過企業創新獲得發展,最終導致企業整體創新能力較低。何軒等(2016)在探究腐敗與私營企業創新關系的過程中同樣發現,腐敗會抑制企業家對研發創新等生產性活動投入的意愿,提升企業家對非生產性活動投入(即尋租等)的偏好,造成企業家活動配置的扭曲。Vorley and Williams(2016)指出,微腐敗會降低企業家的野心,限制以創新增長為導向的企業家精神,并且誘發企業家進行更多的微腐敗活動。
研發創新等生產性活動均存在投入高、風險大、周期長的特點,充裕的資金是企業開展這類活動的必要前提。對于企業而言,研發創新是提升企業生產率的重要決定因素(Aw et al.,2011;Mohnen and Hall,2013)。當面臨著低成本的微腐敗這類非生產性活動以及投入高、風險大、收益不確定的研發創新這類生產性活動時,企業決策者將更偏好將有限的時間精力投入到微腐敗行為,從而造成對生產性的研發創新活動的“擠出效應”,最終導致企業生產率的降低。基于此,本文將從企業創新入手,提出如下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機制的假說:
假說2:微腐敗會抑制企業創新進而降低企業生產率。
三、數據來源、變量及模型設定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的樣本數據來自世界銀行2002-2014年對全球六大洲143個國家企業的調查數據。其中,48個國家只參與過一年的企業調查;45個國家參與過兩年的企業調查;24個國家參與過三年的企業調查;18個國家參與過四年的企業調查,剩余8個國家參與過五年的企業調查。由于世界銀行每年進行調查的國家以及企業都是隨機選擇的,即使樣本中大部分國家參與過兩年及以上的企業調查,但是年份并不連續,出現同一個國家連續兩年被調查的樣本僅占全部樣本的6.29%。而且,同一個國家連續兩年被調查的企業也并不是同一批企業,因此,本文樣本是由這143個國家被調查企業組成的獨立混合截面數據。
調查問卷包括企業的一般信息、基礎設施與服務、銷售與供應、競爭與創新、土地、犯罪、政企關系、融資、勞動力、生產率等幾大方面。問卷的巧妙設計不僅可以獲取關于這些企業詳細的特征信息以及財務信息等,還提供了企業在申請供水、供電、通訊連接、進口許可證、經營許可證、建筑許可證以及稅收監管過程中是否被要求支付一些非正式費用的信息,使得本文能夠采用此問卷來研究微腐敗行為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關于國家層面的特征信息,如人均GDP、人口密度等數據也來自世界銀行,由作者手動搜集整理。
本文對原始數據的主要處理如下:剔除成立時間在1900年前的企業;剔除銷售收入、雇員人數小于0的企業;剔除農業部門的樣本;剔除所有制屬性為其他的樣本;刪除行業信息缺失的樣本等。經過這一系列處理,本文的最終樣本為117245條記錄。
(二)主要指標的度量
1.被解釋變量
衡量企業生產率的指標最常見有兩種:一種是勞動生產率,另一種是TFP,由于后者可以度量除了勞動、資本變化以外的技術變化,因而成為最常用的指標。但限于計算TFP所需各個企業的資本及中間投入數據的大量缺失,本文主要使用對數化的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作為被解釋變量(llabor)。具體而言,用問卷中經過指數調整的“當年總銷售收入”與“該企業當年擁有多少長期全職的員工數”的比值進行衡量。由于無法收集各國各行業的出廠價格指數,本文利用各國消費者價格指數調整“當年總銷售收入”(以美元為計量單位),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2.解釋變量
腐敗是一種隱蔽且非法的行為,導致難以獲得關于腐敗的真實數據,當前所有衡量腐敗的指標僅僅是對真實腐敗的不完美代理(Rohwer,2009)。微腐敗由于其交易金額小,滲透到生活各個方面,使得微腐敗的衡量更加困難。世界銀行在對各國企業進行問卷調查時涉及較多與腐敗相關的問題,為國內外學者研究腐敗的相關內容提供了重要信息。根據匯總,世界銀行調查問卷中關于腐敗的相關問題可歸納為四類:第一類是詢問管理者平均每周花費多長時間用于與政府相關部門打交道;第二類是詢問“企業在申請供水、供電、通訊連接、進口、經營、建筑許可證或者稅收監管等過程中是否被要求支付非正式的禮物或費用(informal gift or payment)”;第三類是詢問企業為了“將事辦成(get things done)”每年支付給政府行政人員非正式的禮物或費用占企業銷售收入的份額;第四類是要求被調查者針對腐敗的感知來對腐敗是否阻礙企業生產經營進行排序,通常分為五個等級,分別為沒有障礙、次要障礙、中等障礙、主要障礙、嚴重障礙,依次取值0-4。
進一步分析問卷發現,前三類腐敗問題提及的政府相關部門或者行政人員主要是指許可證、基礎服務、稅收以及海關等部門及其工作人員。通常認為,這幾類部門的工作人員均屬于行政級別較低的公職人員。鑒于企業主要與這些低級別公職人員打交道,本文認為其中涉及的非正式禮物或費用的金額相對較小,因此,參照Ariane et al.(2007)、Clarke(2011)以及Mashali(2012)等人對微腐敗的定義,本文認為第二類與第三類問題涉及的均是微腐敗。考慮到管理者在回答第一類或第三類問題時可能出于自身名譽考慮等原因不愿意給予真實回答,進而嚴重低估企業打交道時間或者非正式支出占比的真實水平(Clarke,2011)。并且,在回答第一類或第三類問題時,管理者還需回憶具體“多長時間”或“多少份額”等字眼然后作出回答,這一過程容易產生系統性的測量誤差,從而影響結果的可靠性。第四類問題采用序數量表的設計會產生不可比偏誤(Desai and Olofsgrd,2011),基于某些無法觀測的因素,如文化等,不同的受訪者可能對于同一個概念(如腐敗)有不同的理解而給出不同的答案,造成對這類問題答案的不可比較。因此,Nguyen et al.(2016)指出通過設置企業是否參與微腐敗虛擬變量的方法對于微腐敗的衡量更加可靠。
鑒于此,本文將基于問卷中的第二類問題構建衡量微腐敗的指標,作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具體而言,根據歸納的世界銀行問卷中的第二類問題,企業會在申請供水、供電、通訊連接、進口、經營、建筑許可證以及稅收監管等七個方面被詢問到是否被要求支付非正式禮物或金錢。針對同一個企業,當它在申請供水、供電、通訊連接、進口、經營、建筑許可證以及稅收監管中任意一個方面對是否被要求支付非正式禮物或金錢的回答為“是”,則認為其參與了一項微腐敗,然后加總這七個方面的微腐敗得到企業最終參與的微腐敗范圍,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即為企業參與的微腐敗范圍(bribescope)(2)世界銀行將微腐敗定義為公共部門普遍存在的,公司或個人在尋求政府許可或服務時所發生的腐敗行為。值得指出的是,在世界銀行調查期間,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供水、供電以及通訊連接等公用事業部門進行私有化,以減少政府的干預,促進市場競爭。然而,對于供水、供電這類具有自然壟斷屬性的公用事業部門,公司或個人在尋求其服務時,同樣容易誘導微腐敗的產生。。
為使估計的結果穩健,本文從國家及企業兩個層面來選取控制變量。基于樣本數據的可得性,國家層面的控制變量主要選擇對數化的各國人口密度(ldensity);對數化的各國人均GDP(lgdppc);政府效率(governeff),數據來源于全球治理指數(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用于衡量各國政府在提供服務、監管與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效率,取值范圍為-2.5-2.5,數值越大表明政府效率越高;是否屬于轉型經濟國家虛擬變量(transition);各國所屬經濟發展水平虛擬變量,由于樣本中高達41.30%的樣本為中低收入國家,因此本文以該類國家作為基準項,依次設置代表低收入國家(占比21.92%)、中高收入國家(占比25.24%)以及高收入國家(占比11.53%)的三個虛擬變量low_inc、middle_inc及high_inc。
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主要有:企業年齡(age);企業是否出口虛擬變量(export),根據問卷中“企業的出口銷售額(包括直接出口與間接出口)是否大于0”的回答進行設置,如果大于0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企業融資虛擬變量(finance),根據“企業是否獲得貸款”的回答進行設置,如果回答為“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企業所有制虛擬變量,根據問卷中“不同主體掌控的企業份額的多少”的回答,本文將全部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及私營企業,依次表示為state,foreign與private,并以國有企業(state)作為基準項。如果回答的份額超過50%,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結果發現,本文樣本中國有企業占比2.53%,外資企業占比8.89%,私營企業比重最大,占全部樣本的88.58%。企業是否通過國際質量認證虛擬變量(ISO),根據問卷中“該企業是否有國際認可的質量認證(如ISO9000等)?”的回答來設置,如果回答為“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企業是否對員工提供培訓虛擬變量(training),根據問卷中“企業是否為正式工提供正規的培訓項目”的回答進行設置,如果回答為“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高管的工作經驗(experience),根據問卷中“高管在該領域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進行衡量。表1是對上述涉及所有變量的描述統計。
表1顯示,盡管本文清理后的樣本有117245條記錄,但是被調查者關于微腐敗問題作出回答的概率較低,能夠衡量微腐敗范圍的樣本僅有29109條記錄,占全部樣本的24.83%(3)其中,管理者對供水過程中是否被要求支付非正式禮物或金錢的回答率最低,只占全部樣本的8.08%;而對稅收監管過程中是否被要求支付非正式禮物或金錢的回答率最高,占全部樣本的80.14%。。在參與過微腐敗的企業中,每家企業至少與一個部門的公職人員發生過交易。其他變量的描述統計發現,樣本中36.62%的企業位于轉型經濟國家,27.20%的企業屬于出口企業,54.46%的企業獲得信貸融資,22.71%的企業通過國際質量認證,并且超過43%的企業向員工提供職業培訓。

表1 變量的描述統計
(三)實證模型的設定
為了檢驗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本文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llaborijct=α0+α1bribescopeijct+Xijctβ+σ0industryj+σ1countryc+σ2yeart+εijct
(1)
其中下標i、j、c、t分別代表企業、行業、國家及時間。llaborijct表示為國家c中企業i在t時期生產率的對數值。Xijc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industryj表示行業固定效應,用它來控制行業差異對估計結果有效性的影響;countryc表示國家固定效應,用它來控制國家差異對估計結果有效性的影響;year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用它來控制時間趨勢對估計結果的影響;εijct為相應的測量誤差。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的結果分析
現實中,企業是否發生微腐敗可能并不是一個完全隨機的行為,從而導致企業的微腐敗行為與企業的生產率之間存在潛在的內生性問題,直接運用傳統的OLS回歸得到的結果將是有偏的。并且,受訪者關于微腐敗問題較高的拒答率,可能會產生樣本選擇偏誤。基于此,本文嘗試利用工具變量結合兩階段最小二乘(2SLS)的方法對上述內生性問題進行控制。現有基于企業層面研究腐敗的相關文獻中,多是通過構造地區—行業層面的腐敗指標作為相應的工具變量,如Wang and You(2012)、Krammer(2013)等利用地區—行業均值作為企業腐敗的工具變量;Cai et al.(2011)、黃玖立、李坤望(2013)、魏下海等(2015)利用地區—行業的中位數作為企業腐敗的工具變量。參照上述文獻并結合本文所使用調查問卷的特征,本文根據生成的微腐敗范圍(bribescope)指標構建相應的地區—行業的中位數作為本文的工具變量(ivbribe)。Cai et al.(2011)指出在控制地區、行業固定效果后,地區—行業腐敗的中位數只與本企業的腐敗有關而不直接影響本企業TFP,從而滿足工具變量的獨立性條件。同理,本文構建地區—行業微腐敗范圍的中位數也滿足獨立性條件,具體回歸結果見表2。
表2第(1)列為不控制內生性問題的OLS回歸結果,此時發現微腐敗范圍對企業生產率并不產生影響。但Hausman內生性檢驗結果發現p值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只進行OLS估計的回歸結果會有偏。為此,在表2第(2)列我們首先進行一階段回歸來驗證工具變量的相關性。結果發現,工具變量(ivbribe)前的系數在1%水平上正顯著。對第一階段進行弱工具變量檢驗發現,Cragg-Donald Wald統計量為555.72,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表2第(3)列為對應的2SLS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在控制內生性問題后,企業參與微腐敗的范圍越廣,對企業生產率的負面影響越嚴重,假說1通過驗證。
對流入城市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實施服務和管理,寓管理于服務中,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參與城市建設,為他們將來返鄉創業積累經驗和資金。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提供的眾多服務中,就包括了“法律援助”服務。
(二)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中國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后,開展了一場建國以來最嚴厲的反腐敗運動,這可能導致本文樣本期間內企業的微腐敗行為受到影響,因此,本文首先以2012年為分界點,分別考察這一時間點前后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4)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具體回歸結果見表3第(1)、(2)列(5)篇幅限制,表3-表6沒有展開控制變量部分的具體回歸結果,感興趣的讀者可來信索取。。結果顯示,從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大小看,2012年前、后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負面影響確實出現較大差異,但該結果也表明,主回歸所得到的微腐敗降低企業生產率的結論穩健。為了驗證這一差異產生的原因是否與中國的反腐敗運動有關,本文在表3第(3)列對原樣本數據扣除中國企業進行2SLS回歸,結果發現,微腐敗的系數與表2第(3)列中的結果基本一致,再次驗證了本文主回歸結論的穩健性。

表2 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的回歸結果
進一步地,本文在表3第(4)、(5)列對扣除中國企業的樣本,同樣基于2012年的時點進行分時間區間回歸。比較表3第(1)與第(4)列,第(2)與第(5)列的結果發現,扣除中國企業的樣本與沒有扣除中國的樣本分時間區間對應的回歸結果非常穩健,也再次說明本文結論的穩健性。至于2012年前、后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負面影響出現差異的原因,可能與不同時間、區間內微腐敗的性質或表現形式發生變化有關。

表3 分時間區間的回歸結果
除此之外,為了驗證本文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嘗試將企業支出的非正式禮物或費用占企業銷售收入的份額(即第三類問題)作為衡量企業微腐敗的替代指標(briberatio)進行穩健性分析。相應地,構建該指標對應的地區—行業中位數作為工具變量(ivbriberatio),在等式(1)的基礎上進行2SLS回歸,具體回歸結果見表4。表4的結果顯示,利用第三類問題衡量的微腐敗指標同樣會顯著降低企業生產率,說明本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
(三)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的機制探討
表2的結果證實了微腐敗對企業生產率的負面影響,表明微腐敗雖“微”,但其危害卻不容忽視。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的路徑機制有關。結合研究假說部分的推導,本文主要從企業創新角度嘗試探討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的可能機制。鑒于涉及企業創新相關問題的調查集中在2002-2005年間,因此,本小節使用的樣本只包含2002-2005的33666條企業記錄。
具體而言,本文首先根據問卷中“企業在過去三年中是否引入新產品或者新技術?”的回答來設置企業是否進行創新的虛擬變量(innovation)作為本次回歸的被解釋變量(6)企業創新的形式多樣,通常被劃分為產品創新、流程創新、組織創新以及營銷創新四個方面。考慮到產品創新與技術創新之間的相關性,本文并不單獨分開設置產品創新與技術創新虛擬變量,而是統一設置為企業創新虛擬變量。,如果兩個問題中任意一個回答為“是”,則該變量取值為1;當兩個問題均回答為“否”,則取值為0。考慮到被解釋變量是標準的二元變量,適合采用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進行估計。同時,解釋變量微腐敗范圍(bribescope)已被證實存在內生性問題,所以我們選擇利用probit模型并結合工具變量的方法(即ivprobit)進行回歸。具體的probit模型如下:
Pr(innovationijct=1)=Φ(β0+β1bribescopeijct+Zijctκ)
(2)
其中Ζijct表示企業層面控制變量,除控制企業年齡(age)、企業出口虛擬變量(export)、企業融資虛擬變量(finance)、企業所有制虛擬變量(private和foreign)、企業是否通過國際質量認證虛擬變量(ISO)外,還控制企業規模(firmscale),利用對數化的價格指數調整后的企業總資產衡量;企業貸款能力(debtab),利用企業總負債與企業總資產比值衡量;企業是否獲得國外技術許可虛擬變量(technology),根據問卷中“企業目前是否使用從外資公司獲得許可的技術?”的回答設定,如果回答為“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ζijct為相應的測量誤差。具體回歸結果見表5。表5第(2)列的結果顯示,微腐敗會對企業創新產生顯著負面影響。

表5 企業創新機制
進一步地,將企業創新虛擬變量(innovation)加入等式(1)中再次進行2SLS回歸,得到的回歸結果見表5第(3)列。此時,企業創新(innovation)前的系數顯著為正,而微腐敗(bribescope)前的系數不再統計顯著,說明企業創新確實是微腐敗影響企業生產率的一種機制,從而證實假說2。
(四)分子樣本討論
1.分不同所有制子樣本
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獲得資源的過程中是存在顯著差異的,從而迫使那些無法獲得資源或者不易獲得資源的企業會采取一些非法的途徑,如微腐敗等行為,與政府建立聯系,去增加企業獲得資源的概率。國有企業的政府屬性,使其具有天然優勢,可以不用參與微腐敗就能優先從政府獲得各種政策優惠、資源以及享受各種優先辦事的權利。外資企業雖然缺乏國有企業的天然優勢,但其本身資金雄厚,并且各國為了引進外資企業,通常會出臺各種優惠政策,所以外資企業參與微腐敗的動機也較小。而私營企業無論是所有制性質還是資金規模都不具有優勢,所以私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更容易參與微腐敗行為。本文對樣本中三種所有制企業的微腐敗進行統計時發現,私營企業發生微腐敗最嚴重,無論是參與一項還是多項微腐敗,私營企業都是參與范圍最高的企業。因此,本文認為微腐敗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應該不同,對私營企業生產率的負面影響更大。為此,本文將樣本企業依次分為國有、外資與私營企業三個子樣本進行2SLS回歸,具體結果見表6第(1)-(3)列。表6第(1)-(3)列顯示,微腐敗對國有企業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并且在利用國有企業樣本回歸過程中發現,Cragg-Donald Wald統計結果存在嚴重弱工具變量問題,這可能與國有企業樣本數量過少有關。微腐敗對外資企業同樣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只有私營企業的生產率受到微腐敗的顯著負向影響。

表6 不同所有制的2SLS回歸結果
2.分不同行業子樣本
魏下海等(2015)在研究腐敗對企業開工率的影響時指出,制造業與服務業受腐敗影響不同。相比制造業,服務業受管制更多。因此,服務業企業參與微腐敗的概率可能更高,相應地,其受到微腐敗的影響更大。因此,本文將全部樣本分為制造業與服務業兩大類,在此基礎上分別進行2SLS回歸,具體結果見表6第(4)-(5)列。表6第(4)-(5)列結果表明,微腐敗對制造業企業生產率不產生統計上的顯著影響,而服務業企業則深受微腐敗的負面影響,這與魏下海等(2015)等的發現保持一致。
3.分不同腐敗程度地區子樣本
同樣地,本文認為位于不同腐敗程度地區的企業,其受微腐敗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對于腐敗程度高的地區,企業或公眾對于微腐敗習以為常,從而誘發企業或公眾參與更多微腐敗行為,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加深該地區的腐敗程度。而對于清廉的地區,企業或公眾對于微腐敗保持較高的警覺性,理論上,這些地區的企業或公眾發生微腐敗的概率較低。因此,本文根據透明國際歷年公布的腐敗感知指數,將得分低于50(含)分的地區設置為腐敗程度高的地區,而將得分高于50分的地區設置為腐敗程度低的地區,在此子樣本上進行2SLS回歸,具體結果見表6第(6)-(7)列(7)透明國際在2012調整腐敗感知指數的測算方法,為此,我們將2012年之前的腐敗感知指數調整為0至100,以與2012年后的腐敗感知指數保持一致。。表6第(6)-(7)列結果發現,微腐敗只針對位于腐敗程度高地區企業的生產率有負面影響,而對腐敗程度低地區的企業生產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
4.分不同經濟發達程度地區子樣本
最后,本文認為位于不同經濟發達程度地區的企業,其受微腐敗的影響也可能存在差異。經濟發達地區往往市場化程度較高,企業經營環境相對透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抑制企業的微腐敗行為。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市場機制往往不完善,從而為企業的微腐敗行為提供溫床,容易誘發企業或公眾參與更多微腐敗行為。因此,本文根據各國所屬經濟發展水平的虛擬變量,將全部樣本劃分為經濟發達程度低與經濟發達程度高的兩個子樣本。其中,經濟發達程度低子樣本主要包括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家的企業,剩余中高收入以及高收入國家的企業則歸屬于經濟發達程度高子樣本。表6第(8)-(9)列展示了兩個子樣本具體的2SLS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微腐敗只負面影響位于經濟發達程度低的地區的企業生產率,而對經濟發達程度高的地區的企業生產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
五、結論與不足
微腐敗所以謂之“微”,主要原因在于其行為本身涉及的利益規模微小。同時,由于其“微”,社會公眾司空見慣,甚至默認成為一種社會潛規則。如果放任這種錯誤認知蔓延發展,微腐敗終將質變成為大腐敗進而引發社會危害。本文的研究結論支持微腐敗也能成為“大禍害”的觀點。我們發現,微腐敗會抑制企業生產率。這說明微腐敗表面雖“微”,但其危害卻不容小覷。因此,本文的結論有助于扭轉學術界、企業及公眾對微腐敗的模糊認識,加深對習總書記有關微腐敗論斷的理解,在嚴抓“老虎”這類的大腐敗外,還必須高度重視看似“蒼蠅”的微腐敗,切實做到“老虎”、“蒼蠅”一起打,將微腐敗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蒼蠅”發展成“老虎”。
本文的研究結論除了給各國反腐敗斗爭提供“‘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政策啟示外,還存在以下幾點實踐啟示:(1)本文在衡量微腐敗變量過程中發現,企業在稅收監管方面發生微腐敗的概率最高,其次是許可證方面,最后是獲取基礎設施服務方面。這可能與企業避稅的動機有關。因此,各國政府在嚴抓微腐敗的過程中,應重點關注稅收部門,加強稅收部門監管的公正性與透明性,做到依法辦事。(2)在分子樣本討論中本文發現,私營企業因為所有制性質以及自身規模,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從而有更高的動機去參與微腐敗行為。反過來,私營企業是遭受微腐敗負面影響最嚴重的企業,由此形成惡性循環。鑒于此,各國政府應該為私營企業營造更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加大對私營企業的資源傾斜力度,使私營企業能夠享受平等的政策待遇。同時,私營企業自身在享受平等待遇的同時也必須做到依法經營、杜絕參與各種形式的微腐敗甚至大腐敗行為。(3)同樣地,在分子樣本討論中本文發現,服務業由于遭受監管較多,使得該行業的企業參與微腐敗的動機更強。因此,各國政府應當減輕對服務業的監管,簡化對服務業的各種審批流程、辦事程序,為服務業營造一個便捷、高效、寬松的外部監管環境。
在得到上述結論的同時,本文也存在幾點不足值得思考。首先是關于微腐敗的定義與衡量。由于微腐敗涉利之“微”,導致準確度量微腐敗十分困難。無論是本文采用的調查問卷的方法,還是其他文獻報告的衡量方法,都只是對微腐敗的一種近似替代,如何準確衡量微腐敗指標始終值得深究。其次,限于數據,本文在機制探討部分只討論了企業創新,可能還遺漏了其他潛在的影響機制。今后在數據可得性的條件下,這些遺留問題都將是進一步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