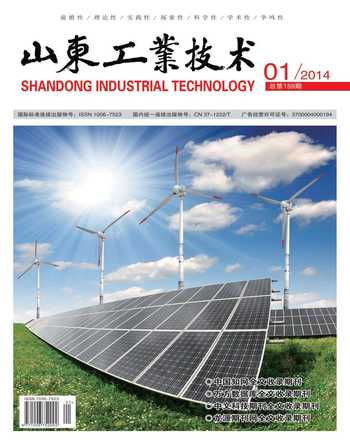我國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理論研究及實踐應用初探
郭暢
【摘 要】近年來隨著我國環(huán)境的迅速惡化,人們深深地陷入了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的境況中。資源浪費、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嚴重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經濟的發(fā)展。開展實施環(huán)境會計已是當務之急。基于此對我國環(huán)境會計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展開探討。
【關鍵詞】環(huán)境會計理論研究;實踐應用,問題;建議
1 我國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理論研究及實踐應用方面存在的問題
1.1 未研究出臺環(huán)境會計準則使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實施具有隨意性
由于環(huán)境會計自身的特殊性,企業(yè)環(huán)境要素的確認、計量和報告與傳統(tǒng)會計都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環(huán)境會計準則,制度和指導方針出臺,使各企業(yè)實施環(huán)境會計操作上不規(guī)范具有隨意性。企業(yè)環(huán)境資源具有社會產品所具有的效用性和稀缺性,具有再生性和不可再生性,應當對其進行確認和計量。而對于各企業(yè)而言,資源無價、低價的意識使得人們忽視了國家環(huán)境資源的真正價值,從而使環(huán)境資源產品低價。認為環(huán)境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具有價值,不屬于傳統(tǒng)會計核算的對象。依賴于天然的資源就更沒有成本的核算,很少有單位對企業(yè)環(huán)境、企業(yè)資源進行準確的核算和控制。大多數企業(yè)在具體核算與生態(tài)環(huán)境有關的業(yè)務時,都是在傳統(tǒng)會計核算基礎上添加一些環(huán)境會計要素項目,與企業(yè)生產經營業(yè)務混在一起,對于環(huán)境會計實務的會計處理顯得零星分散,沒有形成規(guī)范體系。這種核算方法不能單獨提供有關會計主體的經濟活動對環(huán)境影響的信息,有些環(huán)境因素不能合理地計量與記錄,對環(huán)境會計信息的披露也只能是傳統(tǒng)財務會計信息披露的一個部分,在對外公布的財務報表中,沒有統(tǒng)一的列示方法,在信息傳遞上存在很大的障礙。這些做法嚴重制約了我國環(huán)境會計的發(fā)展。另外,由于沒有環(huán)境會計準則和環(huán)境會計信息披露的規(guī)定可以依據,各單位也不會主動披露環(huán)境會計信息;即使有些企業(yè)已經意識到環(huán)境會計的重要性,也有披露環(huán)境信息的動機,但由于目前還沒有可操作性的環(huán)境會計準則,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實務處理極具隨意性,沒有規(guī)范的要求進行制約。
1.2 環(huán)境管理機制不健全使企業(yè)及地方政府實施環(huán)境會計不夠主動
目前我國 環(huán)境管理機制還不健全,也就是說還沒有完善健全的專門的環(huán)境法律法規(guī)對企業(yè)是否運用環(huán)境會計進行約束。使企業(yè)及地方政府實施環(huán)境會計不夠主動。
從企業(yè)實施環(huán)境會計方面的調研結果看,很多企業(yè)環(huán)境責任意識不強,對環(huán)境會計工作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往往只顧眼前利益,環(huán)境保護觀念淡薄,并沒有真正形成環(huán)境責任意識,重視經濟發(fā)展輕視環(huán)境保護思想較為普遍。目前大部分企業(yè)都追求利潤最大化,完全忽略了環(huán)境污染問題,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成本越低利潤越大,若考慮環(huán)境污染帶來的成本,則總成本就會增加,利潤便會降低。
1.3 未建立環(huán)境會計審核體系企業(yè)的信息披露真實性不確定
經過對上市公司的大量調研結果,由于我國沒有建立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審核體系,在很多企業(yè)的審計報告中,幾乎沒有涉及對于環(huán)境會計信息的審計,無形削弱了對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披露內容及真實性的約束。
企業(yè)披露環(huán)境會計信息的目的就是為利益相關者提供相關的信息,以利于其對企業(yè)作出正確的評價。企業(yè)在披露環(huán)境信息時的選擇性決定了所披露的環(huán)境信息不全面,只披露正面的信息,而弱化或消除負面信息。很多企業(yè)披露的環(huán)境會計信息尤其是貨幣化信息多為歷史數據,如排污綠化費用、環(huán)保投資額等,缺少對于與環(huán)保相關的負債、成本等信息的披露。披露的環(huán)境問題不全面使外部利益相關者很難對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信息情況做出切合實際的評價,進而會造成對企業(yè)經營能力的評估有所偏頗。披露的環(huán)境會計信息沒有經過審計,自然對其環(huán)境信息披露的真實可靠性難以判斷。
2 對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理論研究及實踐應用存在問題的解決建議
2.1 研究出臺環(huán)境會計準則使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實施更具規(guī)范性
我國應將環(huán)境會計核算和監(jiān)督納入有關法律法規(guī),完善會計法規(guī)并制定具體的環(huán)境會計準則,以法律確定環(huán)境會計內容、核算和信息披露等,使環(huán)境會計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
制定了環(huán)境會計準則,同時還需建立行業(yè)環(huán)境會計指南,環(huán)境會計發(fā)展是依托相關的規(guī)范和指南來進行的,環(huán)境會計指南在企業(yè)會計實踐中地位相當重要。建立環(huán)境會計指南的總體框架,包括環(huán)境會計的界定、特征、對象和分類,科目設置,主要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賬務處理方法,信息披露內容和形式等。 可根據能源、建筑、機械、食品等不同行業(yè)的特點,制定出不同行業(yè)的會計指南,并對環(huán)境保護活動進行詳細分類,將環(huán)境會計的外部報告機能明確化、環(huán)境保護成本精細化、環(huán)境保護效果和經濟效果體系化。
有了準則及環(huán)境會計指南引導下,企業(yè)對于環(huán)境會計的開展由被動強制便主動自覺,由核算及披露等的隨意性過渡到更具規(guī)范性,保證環(huán)境會計真正能夠在實踐中推廣,最終促進我國經濟長遠穩(wěn)定發(fā)展。
2.2 健全環(huán)境管理機制使企業(yè)及地方政府主動實施環(huán)境會計
我國要建設并實施環(huán)境會計體系必須從立法上入手,政府部門在環(huán)境會計體系的建設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相關部門要加快制定與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關系較密切的法律法規(guī)和環(huán)境管理制度建設。應設有專門的部門制定環(huán)境會計規(guī)范,這些法律法規(guī)應該不僅僅局限于國家立法層次,而需要把一定的權利下放到具體的部門和地區(qū)。因為環(huán)境問題在各個行業(yè)和地區(qū)間是有明顯的差異的,不能一概而論,并對企業(yè)的環(huán)境會計實踐進行管理。要加強企業(yè)及社會公眾的環(huán)保意識。要加強企業(yè)管理人員和職工的環(huán)保宣傳,樹立典型企業(yè)。政府要有明確導向詳細的規(guī)定出環(huán)境保護成本及環(huán)境保護經濟效果的算定方法, 為企業(yè)的具體操作提供可行性。
除了完善立法, 還應加強執(zhí)法。加大對違法者的懲處力度, 不僅要在民事上追究其侵權行為, 而且要追究其刑事責任。讓違法違規(guī)者受到法律的制裁,讓部分地方政府官員不能以犧牲環(huán)境、犧牲人民健康為代價去取得所謂的政績。地方政府在執(zhí)行法律法規(guī)時 也能更加明確自身在環(huán)境保護和可持續(xù)發(fā)展方面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自覺宣傳推動當地環(huán)境會計的開展。違規(guī)企業(yè)也將會在競爭中被淘汰,企業(yè)迫于競爭壓力和逐利本性,將會自發(fā)、自愿和主動地實施環(huán)境會計。環(huán)境保護意識的提高是推動環(huán)境會計體系建設的內在力量。當企業(yè)的環(huán)境意識已經由對社會的一種貢獻轉變成左右企業(yè)業(yè)績的重要因素,進而發(fā)展成企業(yè)最重要的戰(zhàn)略之一,就能夠使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在企業(yè)中占有重要地位。
2.3 建立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審核體系使企業(yè)信息披露更具真實性
企業(yè)最看重的是效益,從自身利益出發(fā),很難對環(huán)境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全面、如實地披露,信息的可靠性降低,因此要注重對環(huán)境會計信息的審計,將涉及環(huán)境的內容列入企業(yè)環(huán)境審計框架,審計的要點可以包括:環(huán)保節(jié)能工作的合法性、環(huán)境信息的正確性、資源環(huán)境對策的適當性、內容的全面性等。另外,由于環(huán)境資源的特殊性,對其進行監(jiān)管是可能需要國家審計部門和環(huán)保部門的共同合作,制定具體的審計準則來執(zhí)行。 制定專門的環(huán)境審計準則和行為規(guī)范,才能保證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的真實可靠性。
【參考文獻】
[1]張俊瑞,郭慧婷,賈宗武,劉東霖.企業(yè)環(huán)境會計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化工類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統(tǒng)計與信息論壇,2008.
[2]張猛.山東省重污染行業(yè)上市公司環(huán)境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D].山東大學,2010.
[3]王小穩(wěn).山東省上市公司環(huán)境信息披露研究[J].經濟論壇,2010(9).
[4]黃政.環(huán)境會計體系構建探討[J].財會通訊,綜合2013第2期(上).
[5]周守華,陶春華.環(huán)境會計:理論綜述與啟示[J].會計研究,2012,2.
[責任編輯: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