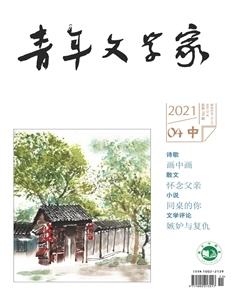施蟄存小說的“限知敘事”視角
張芃葳
新感覺派強調作者直觀或主觀的感受,不太注重對客觀性事物的描繪,力求將主觀的感受和理解映射到客體當中,以創(chuàng)造一種屬于作者個性化的新感覺。作為新感覺派代表作家之一的施蟄存融和了中西方文化,雜糅并融的創(chuàng)作風格被眾多文學研究者從社會、歷史等不同角度進行了闡釋。尤其是他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受容、小說形式與技巧上的探索等相關著述非常多。施蟄存十分重視文學創(chuàng)作的創(chuàng)新性,他的小說不論結構、情節(jié)、還是景物的描寫,都重視自身的觀察和思考。他的小說中多采用敘述視角內置化的形式,深入挖掘敘述主體的內在意識。
一、敘事視角的內涵
敘事視角是敘事情境的一個重要考察方面,顯示著敘事者與故事之間的關系。敘事者站在什么角度、處于什么位置來觀察故事以及敘事視角是否發(fā)生轉換都是敘事視角關注的問題。施蟄存的小說尤其重視敘事視角的選擇和轉換,通過視角的選擇和轉換能清楚地感受到小說中人物的復雜心理和人性的本質。選擇獨特且新穎的敘事視角可以產生一定的哲理意義,可以比較深刻地對人生反思與醒悟。這種視角可蘊涵著人生的道理或者是帶有哲學性的思想。因此,對敘事視角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敘事文本中不同敘事視角的選擇和期待視野的不同,的確都會引起讀者不同的閱讀反饋和情感體驗。因此,敘事視角在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和小說研究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根據觀察出發(fā)點的不同以及對敘事視野的限制程度的不同,一般將敘事視角分為“全知視角”、“限知視角”和“戲劇視角”三種基本的類型。其中“全知視角”比較常見,多指敘事者可以從任意角度觀察被敘述的故事,敘事的人能夠預知未來、通曉過去,任意轉換位置,像是無所不能的神仙一般;“限知視角”指故事完全按照一個或幾個人物的個人感受和意識來呈現,這里面敘述者基本等同于人物本身的感受,只突出轉述人物從外部接受到的信息和內心活動;而“戲劇視角”將視點嚴格限制在敘事者外部觀察的范圍。中國古典小說大多采用傳統(tǒng)的全知視角,而施蟄存的心理分析小說則從主人公的個人視角和心理出發(fā),多選取“限知視角”的敘事手法。
二、“限知視角”內置化的優(yōu)勢
施蟄存是我國現當代文學首位依托人物內心變化,將人物深層次的新的變化和人物思想分析,作為中心進行描寫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家。針對施蟄存小說的特點,我們可以分析出他的作品為什么大部分選用 “限知視角”的原因。在關于人物內心世界分析的小說中,施蟄存先生往往運用大量筆墨描繪人物的真實思想世界,如果依然和大多數傳統(tǒng)小說一樣采用“全知視角”,敘述者冷靜地站在故事之外,刻意制造敘述者與文本之間的距離,想必敘事效果不盡如人意。因此,內心思想分析小說敘事視角的選擇與設置必然會有所不同。“限知視角”很明顯的更適合在展現敘述主體不為人知的思想變化的過程,更利于發(fā)掘和深層次的展現人物的內在意識,發(fā)揮視角內置化的優(yōu)勢。施蟄存強烈追求主體意識表達的觀點受到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他在作品中有意識地對自身主體性進行要求,創(chuàng)作出逐漸成熟的思想分析小說,從而在敘事技巧上顯示出了他的個人風格。
施蟄存在創(chuàng)作內心思想分析小說時普遍通過故事中的某一人物的意識變化來反映事件,而這個人物大多是主要人物。舊故事的重新塑造或者平凡故事的創(chuàng)新講述使施蟄存的小說不僅僅虛構出完整新穎的故事情節(jié),更重要的是虛構出了小說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使用“限知視角”進行創(chuàng)作能夠無形中將人物和讀者拉近距離,讓讀者通過這種親密接觸大幅度提高親切感和對情節(jié)的可信度。而且,它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能將人物內心中靈與肉的矛盾與不著邊際的思緒與情感等充分地表現出來,這是其他敘事視角難以做到的。施蟄存思想分析小說對“限知敘事”視角的巧妙運用,使得他在敘事形式上走上一條新路,讓人體會到眼前一亮的新鮮感,揭露原本的人性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顛覆歷史的意味,這也就一下子解釋了一些相對陳舊的題材偏偏能引人入勝的原因。這些都與“限知視角”的運用具有直接關聯(lián)。
三、施蟄存“限知敘事”的運用和效果
在創(chuàng)作小說的過程中,施蟄存多選擇敘事視角,有意識地將人物視角內置。采用“限知視角”,便于表現所塑造人物復雜的心理沖突與微妙的心理變化。從敘事模式來看,施蟄存大多選用第一人稱“我”與“限知視角”進行搭配,但也不排除運用第三人稱進行敘事,對人物的描寫與刻畫不再把重點放在語言和動作的呈現,而是注重故事發(fā)展過程中人物內心的感受,大致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人物視角內置,呈現真實感受
《石秀》這篇小說是施蟄存以老題材寫新故事的典型,改編自《水滸傳》“楊雄殺妻”的片段。他一改《水滸傳》的全知視角,以石秀的眼光推動故事發(fā)展,將深藏于石秀內心最底層的潛意識全面挖掘開來,一改傳統(tǒng)的只講究所謂的關于江湖道義和忠義兩全的精神,通過人物視角的內置處理和整合,呈現出作品中最真實的感受,從而也將性欲本我、理性自我與道德超我的對比從一種表層的敘事推向了高點。尤其在結尾部分中楊雄與石秀殺潘巧云和迎兒的描寫,直接能透析到石秀變態(tài)的一面。他一邊慫恿著楊雄殺害妻子,一邊又認為自己愛著潘巧云;一邊“多情地看著”潘巧云,一邊又看著楊雄動刀時,感覺到心中的爽快。可以說,在這里通過“限知視角”直接展示人物的真實感受,給小說中矛盾的人物行為找到了一一對應的描寫依據。小說在描寫石秀故意地一次次觸碰潘巧云的肌膚,看她因悲苦而流露怨毒神情時的眼色都表現出了無比的歡暢,之后在把迎兒殺害后反而“覺得異常的安逸”。“覺得”一詞引出石秀內心的真實感受,這樣就一下子將讀者與小說主人公石秀拉近了距離,讓讀者感受到一個狠毒的石秀仿佛就站在面前的感覺。可以說施蟄存筆下的石秀與施耐庵在故事情節(jié)和敘述布局上并沒有太大差別。但是,遠觀我國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背景,施蟄存巧妙地借用了原作表現的外在意境,所還原的卻是原作的內在意境。這種外表與內在的結合,才算得上是一個形象的、更真實的石秀。
(二)獨白展開敘事,幻覺展示內心
獨白是展示人物內心和思想變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施蟄存運用得十分廣泛, “限知敘事”視角可將人物視點內化,獨白的運用就顯得更加合理。《在巴黎大戲院》就是獨白獨立成篇的典范,講述了一位已婚男子與女子在巴黎大戲院看電影的故事,全文都是主人公內心的變化。小說《四喜子的生意》也是以獨白為主的思想分析小說,講述了主人公四喜子作為拉車夫一天經歷的事情,通過人物的獨白可以串聯(lián)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是施蟄存在運用“限知敘事”視角過程中展示出的其獨有的敘事特色和個人風格。
此外,施蟄存對幻覺與想象的手法也在“限知敘事”下運用得十分熟練。只有當敘事限制在一個人物的視野之內、把重心放在人物內在的思想活動過程上,對幻覺和想象的運用才可以更加自如。小說《魔道》中,描述了“我”在火車上遇到一個穿黑衣的丑陋婦人,由于這個婦人外形帶來的沖擊和印象,使作品中的“我”頓時能聯(lián)想到在西洋文學中那些妖怪身份的老婦人在空中騎著笤帚捉別人家小孩的場景。除此之外,還會一連串地聯(lián)想到隔著窗欞在月下噴水的黃臉老婦人、美麗的王妃的木乃伊等等角色。而最后,“我”對黑衣的丑陋婦人的幻覺出現在竹林里陰森的黑影、玻璃上骯臟的黑色污漬、水邊洗衣服的村姑、陳夫人以及咖啡女身上,這些幻覺與想象讓“我”產生極度的恐懼、憤怒,甚至在潛意識中,會迸發(fā)出一股非道德的欲望和病態(tài)。由此可見,獨白與幻覺的運用是“限知視角”下的思想分析小說常用的手段,在施蟄存的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運用,形成了他獨特的敘事風格。
(三)敘事視角轉換,生動人物形象
在施蟄存先生創(chuàng)作的眾多小說中,既有以“限知視角”為主的小說,也有以戲劇視角為主的小說,但每一篇小說都有處于重要地位的敘事視角的融入。不過,從整體上看,為了更生動地塑造文本以及敘述的需要,許多小說都出現了敘事視角轉換的現象。例如,在小說《將軍底頭》里,全篇都以“限知視角”為主表現將軍內心的“俠膽”與“情愛”的沖突,用花驚定將軍的眼光去觀察世界。但是,開篇對時間地點與花將軍身份外貌的介紹卻選取了“全知視角”。不論是“他的臉是白皙的,須是美麗的,眼睛很深……”還是“原來將軍并不是純粹的漢族人……”這都是在全知全能的視角下對故事的時間、地點及人物進行交代,而后文又轉換為“限知視角”,重點描寫花將軍的內心活動的矛盾以及微妙變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轉換敘事視角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飽滿,是施蟄存小說的一大特點。
四、結語
以施蟄存小說的敘事視角為重點研究對象,在敘事學層面對敘事視角的內涵、分類以及在文本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概括,分析施蟄存這種對創(chuàng)作主體情感傾向和社會現實的探索,有利于我們更深刻地把握作者的內心世界和時代脈搏。本文選取“限知視角”,闡釋施蟄存小說的創(chuàng)作以及大多選取“限知敘事”視角的原因,選取施蟄存先生部分作品為例,分析“限知視角”的運用方式以及敘事視角轉換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施蟄存獨具魅力的敘事風格,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