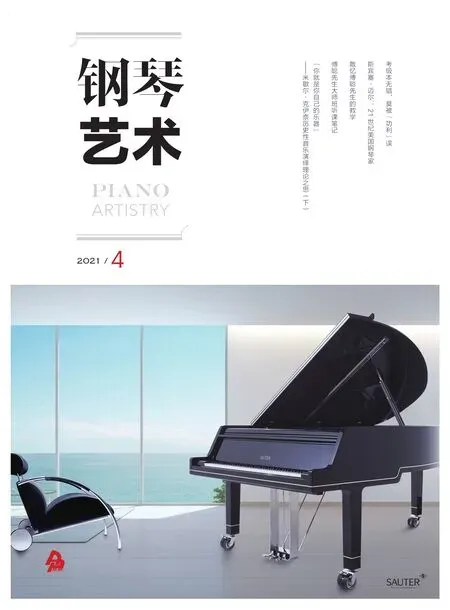考級本無錯,莫被“功利”誤
文/ 周銘孫

前兩天,我在微信的朋友圈看到全國政協委員李心草提出“調整音樂類考級方式或取消音樂類考級制度”的建議,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反響巨大。可見音樂考級這件事觸及的范圍有多廣泛!《音樂周報》的記者立刻對我進行了電話采訪,讓我談一談關于考級的由來:從籌劃到實施、從宗旨到發展……一直到我對考級的看法和意見。因為當時是突然接到的電話,我在毫無預告和準備的情況下,迅速整理思路,把我所知的,尤其是考級良好的初衷和本意、工作的開展、嚴格的標準,以及教材的發展等都在電話中作了介紹。之后,記者立即問我:“對取消考級怎么看,你是否認為考級應該取消?”這時,我才意識到關鍵的癥結在“取消”二字!其實,當時我根本還沒仔細拜讀過這條消息,只是感到“取消”有可能這么簡單嗎?因為牽涉的機構和人員太多了……我聯想到“如一個人生病了,哪怕再嚴重,也應先治療,可以吃藥或是開刀,但不能說就不治了”。于是,我仔細查閱了新聞,明白了是“建議考慮(對音樂考級)調整或取消”,原話是用商榷的口吻,而且是從兩方面說的,并沒有武斷地下結論說“必須取消”,但是很多人只看到“取消”二字就炸了鍋。
任何工作都是講究目標和效益的,這無可厚非。但“考級”是不是一件有益的好事?這才是決定它是否應該存在的根本!作為見證了考級從籌備到策劃,繼而實施、發展的過來人,我首先要說以下幾點。
一、毫無疑問,考級的本意是很好的!
我是從最初就參加了中國音樂家協會的考級工作的,三十年來幾乎每一步工作都親身參與并經歷。從1990年開始籌建、集中討論、編寫教材——確定分為十個級別,根據一般課余學琴細水長流的進度,大約一年提升一個級別,循序漸進、科學合理。
中國音協的考級作為第一家實施的全國性音樂考級機構(之前廣東、上海已先行一步有了考級,但那是地方性的,只面對本地區),標準是非常嚴格的。首先體現在評分表上,要求評委(考官)在每一首曲子上都有明確的評審記錄,每一個曲子都分為很好、較好、尚可、較差四個不同檔次,評委根據考生現場演奏的水平表現,在合適的檔位上打勾,并加以文字評語。當所有的曲目分別評判完后,會有一個總的結論,分別是:優秀、良好、通過和不通過。由于評委們都很認真,考生得“優秀”是極難的,演奏必須十分圓滿、完整,有足以成為別人榜樣的表現才可獲得,所以一般在為期三天的考級之中,每個考場能評出兩三個優秀就不錯了,因為優秀考生是要參加優秀考生演奏會的,而演奏會往往在北京音樂廳或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且僅此一場,不僅必須保證質量,而且人數有限,所以能被選上是非常光榮的事兒。要得“良好”也是很不容易的,彈得規范是必須的,如略有不足,也不能是大毛病,所以獲得“良好”也是足以讓考生與老師感到自豪的成績。而大多數演奏基本規范、表現尚可的考生,都屬“通過”之列。
在20世紀90年代初,考級剛興起的那些年,“不通過”的比例是很高的,程度未達標,明顯拔苗助長的,肯定通不過。尤其到了十級,更加嚴格,考生能彈出全部曲目是不夠的,還必須對音樂風格有一定的理解和表現,如果刻板無趣地演奏,就算是完整地從頭至尾彈下來,也通不過,因為十級是考級中眾望所歸的最高級別,通過者應為大家的楷模。所以評委把控得很嚴,都認為不能降低了考級的標準與水準,那時候,經常出現考高級別的考場通過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情況。現在,恐怕是很難想象、也很難出現的。
此外,考級對評委寫評語的要求也很嚴格,彈得好的考生,評語可以簡單些,如“好”“很好”就足以說明問題了,但對于較差的考生,尤其是通不過的考生,評委必須寫明情況和原因,指出毛病在哪里、應如何改進。這既是為了讓考生明確通過考級需努力的方向,以免繼續走彎路,也是考級本身所要達到的目的和宗旨,體現了考級根本的初衷和本意!
從我當年參加的中國音協考級來說,一直是非常規范、嚴謹的,而且中國音協的考級收費,一直由發改委管理,多年標準不變,一直到21世紀初,還是原價(物價已完全不同)。我感到中國音協能堅守初心,著實不容易。所以這個考級的口碑一直較好,以信譽與嚴格著稱。
綜上所述,大家可以大致了解到“考級的本意是好的”,根兒是正的!現在的問題并不出在根兒上。如果一切都按初衷走下去,沒有干擾,考級就會是一件很有益的工作,但是事情往往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二、問題出在哪里,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這就要談到考級的發展壯大,由原本的一家獨秀,逐漸變成了兩家、三家、四家……有了比較,有了競爭。其實有比較和競爭本不一定是壞事,考生們可以擇優選擇,考級單位也會優勝劣汰。例如,在中國音協舉辦考級之后的兩三年,中央音樂學院的海內外考級也辦起來了,而且十分紅火,當時兩家共存,考級標準都是嚴格而規范的。但隨著更多考級主辦單位的逐漸出現,其龐大的分支伸向全國的各個角落以后,競爭的態勢也開始變得激烈。尤其到了各地之后,承辦的單位不同,有的單位把考級視為一塊謀利的“肥肉”,為了招攬到更多的考生,甚至不惜降低標準去謀取利益。
例如,有的考級可以變通,考生報考八級但沒通過,即可算作七級通過!這就很可笑了,因為此考生原本如只有四級的能力,要報考七級肯定是通不過的,但他卻悟到了如果報考這個考級的八級,彈得再差也不要緊,因為可以降一級算通過七級,這豈不太容易了嗎?這樣,在主辦機構與考生互相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情況下,七級就自欺欺人地奉送出去了。但這位考生如參加另一機構的比較嚴格的考級,是肯定無法通過七級的。那么對于不求實際水平、只圖表面虛榮的考生而言,他會選擇哪一種考級呢?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再說說考級開始時的評審工作。每個考場必須安排兩個評委,而且都是本專業的資深教師。但是現在,有的考級單位,為了節約經費,把評委減少為一個。更有甚者,還要讓一個評委兼考幾種不同的樂器。俗語說:隔行如隔山。如讓一個英語老師去主考日語和阿拉伯語,我們不禁會問:你懂嗎?怎么考啊!但是有的主辦方就這么干。我雖沒有參加這種混搭的考級,但有一次在一個業余比賽中,我在評審鋼琴之余,忽然被要求評一組古箏選手的演奏,不知情者也許認為鋼琴和古箏都屬音樂類,評委應知其優劣。的確,是好是壞我們是分得出來的。但實際上,我們還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作為鋼琴評委,一般并沒有學習古箏的經歷,對于選手的基本功、具體的技法和功力的深淺與對錯等方面,并不能作出更專業精細的評判,只能根據一般的“音樂標準”給分。因此,我既不確定是給得偏高了還是偏低了,也不確定這樣的評分與古箏專業評委給的分相比,選手是得益了還是吃虧了?這樣的情況,對選手是否負責呢?
有的承辦考級的機構,會懇求評委盡量“手下留情”,以保證較高的“通過率”。還有的考級是由培訓機構承辦,機構本身有很多學員,當然這些學員是必須特別加以照顧——要求放低標準給予通過的。或者是其中的授課老師,也借機參與了評審工作,其數量巨大的學生,毫無疑問都被評定為通過。那么,考級活動如果都被這樣操作和降低標準,甚至不需要標準,那么考級除了走過場還有什么意義?考級的標準還是否存在?考級是不是已經形同虛設,完全成了某些人謀取利益的工具了呢?
在此要提出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作為考生和家長,你們是否愿意參加這樣的考級?當你獲得了一個“白送的”級別證書,很“光榮地”向人炫耀時,是否覺得它有用?你真的學好這件樂器了嗎?真的學到東西了嗎?通過音樂你提高了自身的品位和素質了嗎?你已經懂得并喜歡音樂了嗎?我認為拔苗助長,靠關系通過的結果,最后損失的還是自己!
所以,我們需要探討一下,如何發揮音樂考級應有的積極作用?是否有望解決?靠誰來解決?
三、解決問題還需大家提高共識,共同探討!
我認為所謂考級出現問題,其實不是“考級”本身有什么錯。音樂考級本為推動社會音樂學習的規范化與科學化,使廣大琴童與考生走上正規學琴之路,給大家樹立一個明確的標準,提供一套合理編排的教材,讓大家少走彎路。這種宗旨,何錯之有?
那么問題出在哪兒?我多年的觀察和感受是由于各種“功利”的存在與侵蝕!我最信服的真理就是馬克思教導的“存在決定意識”!看任何問題,都由此去對號入座分析一下,其實一切就清楚明白了。
所以從各個方面去分析,如明確音樂考級的本意是為社會音樂教育而努力的,堅持這一點,則肯定能走在正路上,把考級工作做得更好。反之,如把考級看作謀利的工具和手段,那就會把事情做歪了。這種情況我把它簡稱為“功利”,很多事都壞在了“功利”作祟上!
在此,我也只能“點”到為止,因為涉及太多方面的利益,同時也牽涉很多人努力為之奉獻的一份神圣的工作和事業,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前兩天,有一位資深的鋼琴老師很激動地打電話問我:“為什么有人說要‘取消考級’?我們辛辛苦苦地培養著學生,我一直在努力地鉆研著考級教材,為了教得更好,我感到特別有意義呀!”這代表了許多勤勤懇懇、規規矩矩的鋼琴老師的狀態。但是,有兩點要看到的是:其一,并不是每個人都一心只為“事業”,一袋好好的米面,放了一段時間為什么會飛出蛾子呢?其二,不必對“取消”二字過分敏感,人家不也僅是提出建議、提出問題,供大家討論嗎?我覺得“取消”沒那么容易,事實上也取消不了……但只看見“取消”二字就暴跳如雷,不也正是說明其中的復雜性嗎?
所以,有一些問題,也請大家不妨冷靜下來思考一下:
1. 作為組織機構或具體操作的機構,在組織安排與不斷擴展考級工作時,是否一直明確并堅持考級工作的根本目的與社會作用?是否始終把考級的規范化、把專家們制定考級標準的貫徹和落實放在第一位?我認為,質量是應放在利益之上的,這也是信譽和品牌的保證!
2. 作為廣大的鋼琴教師,是否通過考級,真正檢驗并由此提高了自身的教學水平?你的學生是否通過考級獲得了進步,同時找到了不足,明確了自身的努力方向?還是你利用了自己的關系,“幫”考生取得了級別證書?讓學生以此來感謝你,借此提高了自己的聲譽?
3. 作為學生與家長,更要明確為什么要學音樂?我想不應該是為了要一張證書吧?如根本學不好,勝任不了,一張紙能證明什么?有用嗎?真正好不好還是要通過演奏,真正面對面地比較才能證明實際水平。如果學琴的路沒走對,導致難聽或僵硬,最后沒有從學音樂的過程中獲得樂趣,反而“痛恨”或“反感”音樂,那才是最大的得不償失和勞民傷財呢!
總之,杜絕各種不同情況存在下產生的“功利”是很重要的。例如,承辦機構追求的“通過率”,以此追求規模的擴大;從師生來說,“功利”表現在一種獲得通過的名譽感或虛榮心,等等。
再回到本文開始:所謂考級“生病”了,不確切,應該說在某些方面被侵蝕了;至于“需要專家來診治”,也不確切,專家為考級編寫了教材,制定了標準,進而可以通過講課、音像等方式繼續幫助大家深入理解、掌握教材和教學上的實施。但“功利”形成的弊端,不是專家能解決的,而是需要有著不同位置與處境——也就是“不同情況存在”下的人們,達成一個共識,杜絕阻礙考級工作健康發展的各種不同的“功利”現象的出現。我想,這不是靠行政命令和規定能強行解決的,而是要真正明確——我們為什么要考級!
其實,按照考級的本意和初衷踏踏實實地堅持執行,考級本應是一件很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