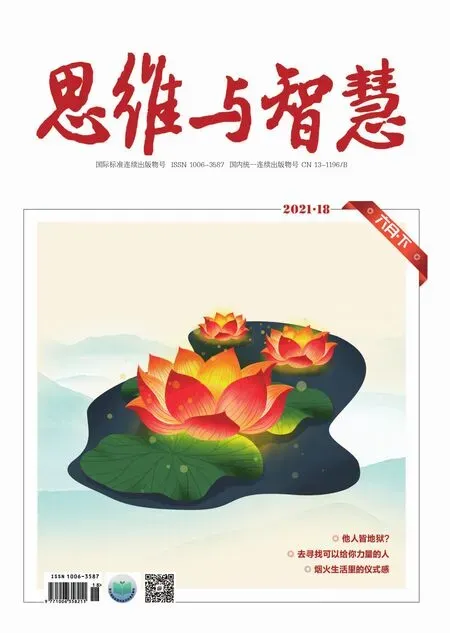春聯里的流年
●王宏志

今年春節我家不貼春聯。
就在這個寒冬,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根據老家習俗,晚輩們因為戴孝,我家從當年起三年不貼紅春聯,而要貼三年“孝春聯”。第一年是白色春聯,第二年是黃色春聯,第三年是深藍色春聯,顏色一年比一年深,第四年恢復貼紅春聯。也可以三年都不貼春聯。寫了大半輩子春聯的父親去了,我們以不貼春聯的方式來紀念他。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為鄰里鄉親書寫春聯,成了父親每年除夕的必修課。就像提前約定好似的,鄰里鄉親都是在除夕這天才來讓父親寫春聯。這天,父親一早吃過飯,收拾好桌子,展開筆簾,取出一大一小兩支“生活”(老家人把毛筆叫“生活”),擺好墨汁瓶、硯臺、鎮紙等,從不吸煙的父親還拿出盒紙煙,燒一壺鄉親們喜歡喝的磚茶,等候大家上門。
鄉親們陸陸續續來了,胳肢窩里夾著從大隊供銷社買來的紅紙,大多是整張紙。父親先詢問對方家里什么地方需要貼春聯,比如大門口、堂屋、廂房,甚至后門灶房、牛棚豬圈,都有不同規格;自己有沒有要寫的內容,如果沒有就由父親自由發揮。問清楚了,父親便幫著把整張紅紙裁成上下聯、腦(方言:橫批)、斗方,剩余的邊角料也不浪費,裁切成春條,寫上五谷豐登、年年有余、四季平安之類的吉祥話。
鄉親們一邊抽著父親遞過來的紙煙、喝著茶,一邊有一句沒一句地扯著閑話,間或夾雜著一些鄉村里特有的笑話。也有的人因為要忙家里的活計,放下紅紙的同時也放下一句話:“王老師,你看著弄吧,一會兒我來取。”龍飛鳳舞間,父親便寫完了一家,又開始寫下一家。寫完的春聯要晾干后才能拿走,這便成了娃娃們的活計,我和其他看熱鬧的孩子便來回穿梭著把父親剛寫好的春聯擺到院子里,用石頭瓦塊壓好,既防止墨汁漫流,也防止被風吹壞。慢慢地,院子里就一片紅哇哇中夾雜著黑色的字,濃濃的墨香便在院子中氤氳。在孩子們的眼中,這便有了年的味道。不知不覺,父親就忙到了天黑。總有鄉親顧不上來取,父親就差遣我打著手電筒,給人家送去。
父親給鄰里鄉親寫了大半輩子春聯,都是義務幫忙,不僅要貼上除夕一整天的時間,還要貼上筆墨、香煙和茶水,有時還要貼上紙張,但父親一直樂此不疲。
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時,我們自己家的春聯,父親也要細細思慮后才動筆。20世紀80年代中期,老百姓的生活漸漸有了起色,父母親也憑借勤勞的雙手,建起了讓旁人羨慕的磚瓦房,日子也日漸滋潤起來。1987年春節,父親為我家寫了這樣一副春聯:辭舊歲不忘昔日創業苦,迎新春喜看今朝生活甜。橫批是:勤儉持家。
那個時候,農村孩子考上大學很不容易,考上大學就意味著跳出了“農門”成了“公家人”,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這一年,我考上了重點大學,姐姐也將于春節期間完婚,1988年春節父親的春聯是這樣寫的:喜去歲鯉躍龍門國添英才家添彩,樂今春鳳攀梧桐喜慶恰如福慶多。橫批是:雙喜臨門。父親內心的喜悅之情躍然紙上。
我參加工作結婚生子之后,父母的牽掛又多了一分。那年春節,因有事,我正月初三才攜妻帶子回到老家,見到門上張貼著父親寫的兩米多長的春聯:日日盼團聚,臘盡除夕不見親;夜夜夢兒孫,望穿秋水何時歸。橫批是:朝思暮想。霎時淚流滿面。
多年后我喬遷新居,住上高層樓房,兒子也將踏入高等院校大門,父親高興地為我寫下春聯:喜去歲遷新居登高望遠,盼來年逢甘霖春華秋實。橫批是:馬到成功。
父親不善言辭,便把對生活的感悟寄托在了春聯中:思去歲遍嘗酸甜苦辣各樣味,想未來必有喜怒哀樂諸般情;待人真誠常禮讓心平氣和,處世厚道多寬容海闊天空。
在父親的眼里,那些印刷的春聯,雖然視覺效果好,但工業化的東西,總是千篇一律,寡淡得沒有個性。
在鋪天蓋地的印刷春聯中,我們家的春聯一直是由父親來書寫的。雖然少了花里胡哨的視覺效果,但樸素中飽含著濃濃的年味和父親對家庭深深的愛。
(常朔摘自《山西日報》2021年2月24日/圖 沐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