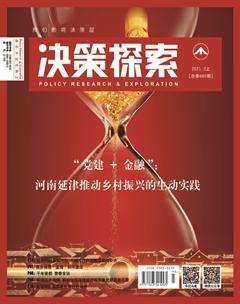數字貨幣殺入支付市場 “最后一公里”瓶頸待破
黃嘉祥
數字貨幣成為“地方兩會”的高頻詞。
繼北京市長陳吉寧1月23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推進數字貨幣試點應用”之后,廣東、上海多地在各自的“地方兩會”上均提及要推進數字貨幣試點。
1月24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全力推進深圳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打造數字貨幣創新試驗區。
4天前的1月20日,繼羅湖區、福田區之后,深圳龍華區啟動了深圳第三輪2000萬元數字貨幣紅包測試,數字貨幣在深圳的測試已按下了快進鍵。
實際上,自2014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便謀劃研究數字貨幣,6年磨一劍,終于在2020年試點落地。2020年10月,人民銀行聯合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紅包試點,標志著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數字貨幣試點正式開啟。之后,蘇州、雄安新區、北京等地相繼測試推廣,2021年或將迎來“數字貨幣大勢之年”,如今上海、成都等城市的數字貨幣試點也已提上了日程。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長黃震曾表示,央行推出數字貨幣,不僅僅是一個支付工具,它與數字金融和數字經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作為新經濟的“發動機”,數字貨幣將極大地促進相關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如果數字金融是數字經濟的皇冠,那么數字貨幣就是數字金融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從目前推廣的情況來看,數字貨幣普及和落地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一方面是在技術上尚須更新修正,另一方面是應用場景缺乏和用戶習慣有待培養。
從數字貨幣的推廣方式來看,雖采用了類似微信支付當年發紅包方式推廣,但推廣速度和力度均不及微信支付,距離全面推廣落地還需邁過諸多關卡;如何與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共存,也成為數字貨幣推廣路途上的一道考驗。
掀起新支付之戰
在當下各地政府競逐數字貨幣試點的熱潮中,深圳無疑拔得頭籌。
2020年10月以來,人民銀行相繼聯合深圳羅湖區、福田區和龍華區啟動數字貨幣大規模測試,發放總額分別為1000萬元、1822.65萬元和2000萬元,每個紅包金額為200元。
同時,數字貨幣還在蘇州、北京、雄安新區等地進行了測試,2021年更是加快了推廣的步伐。
數字貨幣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數字形式的法定貨幣,與商業銀行存款貨幣相比,其性質相當于現金,本質具有支付功能。
一定程度上,數字貨幣無形中掀起了新一輪的移動支付戰爭,數字貨幣的推廣方式,與當年微信支付的推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微信支付誕生之前,支付寶在國內移動支付市場占據絕對的先發優勢,直至微信支付的出現才改變這一局面。
這場移動支付的戰爭從2014年開始打響。2014年伊始,彼時已擁有6億用戶的微信上線了“新年紅包”產品,并借助春節長假引發了廣泛傳播,打響了騰訊和阿里的移動支付市場之爭。
為了爭奪移動支付更多“入口”,騰訊在入股滴滴之后,率先灑下大量補貼,在滴滴(原名嘀嘀)打車與快的打車之間的補貼大戰中,成立僅一年的微信支付以14億元人民幣的補貼為代價,憑借社交入口和出行的高頻場景,將微信支付的用戶數拉升至1億。騰訊投資美團后,后者也同樣成為了微信支付搶奪線下市場份額的一大利器,依靠美團接入了各類商業業態的末端。
在之后幾年的時間里,微信支付還發動了一連串的攻勢,通過各種補貼,爭奪各種線上、線下消費場景,逐漸從支付寶手中搶下移動支付市場份額。2016年12月,馬化騰宣布微信支付在線下支付份額已全面超過支付寶。根據易觀數據,2013年支付寶的市場份額接近80%,2017年支付寶的市場份額逐漸下降到了54%左右。自此,形成了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兩分天下的局面。
從推廣方式來看,微信支付憑借騰訊背后的巨大流量及投資生態,搶占了團購外賣、旅游、生活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等各個領域的移動支付市場,打贏了這一場支付戰爭。
反觀數字貨幣的推廣,亦可看到當年微信支付爭奪移動支付市場的影子。從深圳、蘇州等地的試點來看,同樣是通過發紅包的形式來吸引用戶,促使用戶線下消費,目前其使用范圍已覆蓋生活繳費、餐飲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政務服務等領域,涉及范圍基本上與微信支付無異。
缺乏“互聯網基因”?
當然,數字貨幣的推廣與微信支付也有諸多不同之處,其沒有像騰訊這樣的互聯網巨頭,更沒有騰訊旗下投資生態圈,數字貨幣更多是和地方政府合作。
目前來看,數字貨幣更偏愛線下場景。在深圳三輪試點中,數字貨幣紅包均僅限線下使用,而在北京地區的試點中也僅限線下使用,目前只有蘇州在線上支付場景取得突破。
在蘇州數字貨幣試點中,京東數科成為首個與六大行均開展合作并接入數字貨幣電商平臺消費試點場景的科技公司。實際上,探索線上支付場景也是數字貨幣接下來試點的方向之一。
據媒體報道,成都將在1月27日開啟數字貨幣紅包活動,本次成都數字貨幣紅包共計發放5000萬元,政府發放3000萬線下消費紅包,而京東則發放2000萬線上消費紅包。
“數字經濟時代,各行各業都在進行數字化轉型,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也不例外,因此,從線上去推廣數字貨幣,培養用戶的支付習慣,獲得更多底層用戶的支持是大有意義的,順應數字經濟的潮流發力科技創新,這也是數字貨幣未來推廣的一大趨勢。”1月25日,小花科技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筱芮表示。
從推廣方式和速度來看,數字貨幣與微信支付相比,還缺乏“互聯網”基因。
蘇筱芮表示,從目前進度來看,數字貨幣僅由“技術部門”對外公開亮相,而由技術部門“自產自銷”,這在大型互聯網公司是不可能之事。從互聯網巨頭的擴張之路來看,技術部研發過后,還有產品部、市場部、運營部、品牌公關部、客戶服務部等一系列部門的協調配合,共同推廣科技產品。
“這主要是因為目前數字貨幣還處于小范圍測試狀態,并不具備大規模推廣的成熟條件。”蘇筱芮表示,數字貨幣是一種底層工具,這也注定其只有跟場景結合才能發揮最大價值。
蘇筱芮表示,盡管目前數字貨幣陸續接入各類商業場景,但都是第三方場景,并非自營場景。數字貨幣如果想要打破第三方支付壁壘,想要破除線下“碼牌林立”之現象,就需要遵循互聯網產品推廣的基本邏輯,需要致力于構建自營生態及場景,打造自身的生態圈。
對于數字貨幣來說,獲取新增用戶并非當下挑戰,如何留住用戶才是推廣中的一道難題。
一位中簽數字貨幣紅包的深圳市民介紹說,在線下使用數字貨幣紅包消費后就卸載了相關的APP,目前還沒看到其他可使用場景。
因此,數字貨幣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實現用戶留存,如何在少數科技公司于小額支付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的大環境下進行突破,這考驗著官方如何構建自營生態圈,如何培養起市場用戶的使用習慣。
與第三方支付共存之道
伴隨著數字貨幣試點不斷加速,必然會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支付業務帶來沖擊和挑戰,其與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方式如何共存,成為了當前的一個問題。
中信證券在近期的研報中表示,數字貨幣應用范圍擴大,預計試點區域有望拓展。相對于目前的第三方支付,數字貨幣具有消費便捷、安全性高、便于監控等優勢,近期測試頻率持續上升,技術成熟度不斷完善,預計未來數字貨幣應用范圍將進一步擴大。
實際上,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曾表示,微信、支付寶和央行數字貨幣不存在競爭關系。微信、支付寶和數字貨幣不是一個維度上的,微信和支付寶是金融基礎設施,是錢包,而數字貨幣是支付工具,是錢包的內容。
不過,多位受訪專家均表示,數字貨幣本身具有一個支付體系,且旨在打破第三方支付壁壘,必然會和其他任何第三方支付平臺形成競爭關系,而數字貨幣如何跟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有序協同,法律上還有待進一步明確。而微信支付、支付寶亦擔心數字貨幣推出之后,會快速替代前者。
實際上,在數字貨幣多地推進試點之際,第三方支付行業監管也在不斷升級。
1月20日,央行發布了《非銀行支付機構條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條例》),首次提出支付領域反壟斷,明確界定相關市場范圍以及市場支配地位認定標準,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同時,《條例》對支付功能作了重新劃分定位。
一位金融人士指出,《條例》的出臺實際上與數字貨幣加速推廣有內在的關聯,且近期監管層多次強調“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數字貨幣切入移動支付領域,亦是為了改變當前微信支付與支付寶兩家獨大的局面,承擔起涉及國計民生領域的移動支付。
1月25日,中央財經大學數字財經研究中心主任陳波表示,數字貨幣背后是以央行、商業銀行為主導的支付網絡,其背后的銀行自有生態體系跟支付寶及微信完全不同,所以數字貨幣是非常有特色的存在,但將來能占據多少市場份額,還是要由市場來決定,目前還很難做出判斷。
“數字貨幣的發展空間很大,但能不能成功,取決于央行怎么去推進,也取決于老百姓的認可程度。”陳波說。
同日,區塊鏈與數字貨幣研究者楊俊表示,二者將會在競合關系中發展壯大,第三方支付已深入各大消費場景且具有龐大的用戶群體,支付便捷性已體現得淋漓盡致;數字貨幣則處于初期,不論是用戶的接受程度和消費場景都有待進一步普及。數字貨幣以法幣數字化應用為使命,第三方支付則是以便捷的支付服務為根本,兩者因不同的定位將會長期共存。
對于數字貨幣與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共存方式,蘇筱芮表示,數字貨幣作為具有官方背景的金融科技產物,將承載更多具有國計民生性質的社會職能,后續不排除數字貨幣切入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這樣的官方場景,為官方平臺提供底層賬戶體系與支付功能,一方面能夠增強政府服務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夠提升用戶體驗,形成國家級大數據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