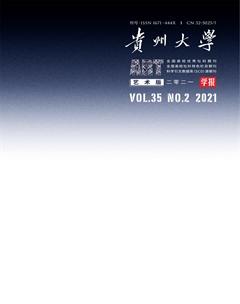社會轉型中藝術集聚的歷史演進與基本特征
榮潔
摘要:藝術集聚作為藝術生產的規模性叢集,與社會轉型具有一定的歷史同構性。以宋代年畫生產、明清畫派以及改革開放后的藝術區為代表,中國藝術集聚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不同歷史時期,基于觀念形態、生產驅動、物理空間三重維度表現出與社會轉型相適應的演進特征。具體而言,總體呈現出“文化傳統——物質效用——自我實現”的觀念形態變遷,“家庭生產——市場驅動——多重權力建構”的生產驅動轉型,以及“在地性集聚——流動性地域集聚——文化空間再造的聚焦型集聚”的物理空間演進趨向,反映出藝術集聚作為藝術及其行為的文化空間表征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互構作用。
關鍵詞:藝術集聚;社會轉型;空間再造;藝術生產
中圖分類號:J0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444X(2021)01-0008-07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ysb.2021.02.002
作為觀念的上層建筑之一,藝術屬于文化的一種特殊形態,用以表達符號及意義。這種對符號和意義的詮釋作用于人的精神需求,其產生和發展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和制約,并借助于政治、道德、法律、哲學等“中間環節”反作用于社會生活。[1]可見,藝術及其行為并非孤立存在的,它始終置身于一個由市場語言和非市場語言共同建構的多元文化生態之中。作為藝術及其行為的文化空間表征,藝術集聚表現為藝術生產的規模性叢集。依循藝術與社會系統之間的密切關聯性,藝術集聚的形成與變遷同樣處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權力機制所構建的綜合場域之中,社會轉型所引發的社會形態變革必然促進藝術集聚的歷史演進與形態變遷。
社會轉型是一個系統性、綜合性、漸進性的演變過程,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根本性變革推動了社會結構、經濟體制、社會形態的整體轉化從而引發的社會質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視角來看,社會轉型即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繼而向信息社會的歷史演進過程。[2]以生產及所應用的知識為中軸,社會轉型又可劃分為丹尼爾·貝爾所稱的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等社會形態及概念序列的演變。[3]事實上,對社會轉型的概念界定根據中軸原理及首要邏輯價值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但從本質上來講,無論哪一種概念序列,都包涵著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結構性轉變這一核心歷史價值,體現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與社會轉型的歷史演進相適應,藝術集聚在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整體轉化中不斷變遷,并基于觀念形態、生產驅動和物理空間三個維度與社會轉型表現出顯著的同構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藝術門類的多樣性,廣義的藝術集聚可根據生產內容而細分為美術集聚、音樂集聚、影視集聚等具體樣態。相較于產業性、政策性較強的音樂和影視集聚,美術集聚則表現出更為深刻的歷史性、自發性和普遍性。本文所研究的藝術集聚主要考察以美術行業為主體的狹義的藝術生產集聚,具體范疇包括宋代年畫生產、明清畫派等傳統藝術集聚,以及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藝術區等當代藝術集聚。
一、傳統農業社會的藝術集聚:宋代年畫的民俗空間生產中國藝術集聚發端于宋代,是古代城市在不斷進行自我演化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社會產物,具有典型的農耕文明的文化經濟特征。宋代之后,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生活漸趨多元,城市功能開始由原來的政治中心向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復合空間轉型。當社會具備了相應的市場條件與社會環境時,藝術集聚便會應運而生。以宋代年畫生產為代表,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審美意趣的世俗化,催生出藝術消費需求的大眾化及市場化,從而形成了以家庭為基本單位、遵照文化傳統與習俗而形成的一種具有高度地域特征的藝術生產系統。
(一)觀念形態:文化傳統與習俗
以年畫生產為代表,農業社會藝術集聚的觀念形態深深植根于文化傳統與鄉規民俗之中,表征為集體性的觀念呈現。年畫是我國特有的民間工藝畫種,是傳統社會世俗生活中用于構筑理念世界的圖像化表征系統,它以迎接新歲、納福履吉為目的,成為社會集體價值意義表達的物質載體之一。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商業市鎮和商品經濟繁榮發展,畫工技藝的提升與活字印刷術所推動的雕版年畫生產群體的擴大為年畫創造了規模化生產的可能性,而百姓審美趣味世俗化的轉變以及藝術的生活化融入又使年畫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商品而產生出普遍的社會性需求。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年畫開始由宗教崇拜物轉而成為世俗文化生活的重要商品之一。無論是農事風俗畫、時事新聞畫、戲曲年畫,還是景觀畫、器物畫、廣告畫等,都是反映世俗生活的觀賞對象,與之前的門神畫及各種神像紙馬相比較,世俗年畫與民眾日常生活的關系更為密切,從而更為廣泛地延展了年畫的社會性意涵。
年畫因民俗而產生,以服務民俗為目的,它以圖形和文字的符號組合方式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民俗空間的文本敘事機制。這種民間性既表現在生產主體與消費主體的全民性,又體現于藝術內容和意義表征的生活化。因而,作為中國傳統藝術集聚的最初形態,年畫的生產集聚,正是民俗與年畫相互融匯并賦予年畫社會性意義建構的空間體現。
(二)生產驅動:家庭作坊式的社會化建構
宋代年畫生產集聚的驅動要素主要來源于地方性的傳統工藝以及依附于家庭的手工業生產,是建立在對地域性文化資源傳承與保護之上的生產交易行為,具有典型的小農經濟的特征。世俗年畫與民眾日常生活的密切聯系,催生了廣泛的心理認同和市場需求,從而為年畫的社會化生產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從生產方式來看,年畫生產是在畫匠繪制出圖像模板的基礎上以手工業作坊的形式進行的規模化生產方式,是一種以復制為主的民間工藝。年畫的這種生產屬性為大規模的民間性生產提供了可能,于是出現了以家庭作坊生產為主的民間藝術集聚。
“當時的北宋中央、地方、私人、書房,無所不從事雕版印刷工作,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制作之精,不但超越前代,就是以后的明、清兩代也難能相比。”[4]在宮廷,年畫受到了統治階層的普遍認可與推崇。在民間,木版年畫大為盛行,出現了以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為核心的年畫生產集聚地。在商業、交通發達的都城汴京,專事生產“紙畫”(宋代年畫泛稱紙畫)的作坊出現并已初具生產規模。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京都汴梁,已遍設年畫作坊,大量印制木板年畫”[5]。
這種早期的民間藝術集聚主要以家庭作坊為主體而進行生產,家庭作坊同時也是畫店,打出一個名號,家庭成員各具所長,分工明確,可謂家家畫店,人人畫師。以山東楊家埠木版年畫生產集聚為例,就有“家家印年畫,戶戶繪丹青”[6]之說,“畫店世代相傳,名號永久不變”[7],反映出家庭作坊式版畫生產的盛況。周汝昌先生曾以詩文描繪楊柳青的年畫印賣景象:“楊柳青中,家家繡女竟衣紅。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8]
盛行于民間的家庭作坊式藝術生產方式,依賴于農耕文明的傳統社會結構而形成,在藝術風格與內容方面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同質性特征。
(三)物理空間:在地性集聚
從空間的具體形態來看,由于農耕文明時期的藝術集聚是以家庭作坊為主體的社會性生產,這一生產方式及社會化程度使之在物理空間形態上呈現出基于地區文化市場的地域性特征,并以空間融入的方式介入農業社會的生產與生活。
宋代年畫生產集聚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分散性與在地性,孕生于傳統手工業生產和文化技藝、文化資源的空間融合,是一種具有地方專業性的群體性集聚形態。隨著商品經濟和市井文化的進一步繁榮,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南、北、中三大年畫群落,即以蘇州桃花塢為核心,輔以湖南灘頭、廣東佛山、四川綿竹、福建漳州等地形成的南方年畫生產群落;以天津楊柳青為核心,輔以山西臨汾、河北武強、山東濰坊、山西鳳翔等地形成的北方年畫生產群落;以及以開封朱仙鎮為核心所形成的中原年畫生產群落。這些年畫生產集聚地都表現出民間性的地方專業性特征,依賴地方性的文化資源、地理資源和市場資源而形成。
傳統社會的在地性藝術集聚形態往往由偶然因素和歷史因素所促成,然而,一旦形成藝術生產的地方性集聚,就會借助于循環累積過程使這種空間集聚形態長期鎖定于某個地區,從而進一步強化地方專業化,延續藝術集聚地理空間的在地性。
二、農業社會轉型中的藝術集聚:明清地方畫派的藝術空間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改變了農業文明以土地為生產資料限局域獲取資源的生產方式,實現了跨局域的資源獲取,從而改變了時間與空間。城市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新興場所,而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又進一步推動了藝術集聚的形態轉型。在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進程中,都市成為現代性的載體與象征,蘇州、揚州、上海等地相繼成為國家經濟重鎮,并催生出以上述地區為活動中心的“吳門畫派”“揚州八怪”“海上畫派”“嶺南畫派”等地方畫派。這一時期的藝術集聚逐漸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以城市為中心、以商品化與大眾化為特征的藝術集聚形態,日益表現出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物質性、世俗性、流動性等現代性轉向。
(一)觀念形態:物質效用與世俗化
明清以降,政治改革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推進了社會關系與文化理念的變化,并迅速反映在繪畫領域。隨著政治經濟關系向資本主義方式的轉變,按勞取酬的經濟機制在上海、廣東等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得以普遍確立,也推動了繪畫群體的觀念轉型。在工商業、金融業為主導的社會環境中,“興利”“言富”的價值論顛覆了傳統的等級秩序和價值觀念,對金錢和利益的追求成為公開、合理、正當的價值選擇。
在這種觀念形態的作用下,以往為官僚士大夫服務的文人畫創作理念和較為私密的書畫交易方式,已經難以支撐畫家們正常的生活與創作;藝術品的商業運作模式由狹小的社交圈內部交易轉向社會化、商業化軌道,并以直接或間接的交易方式進入流通領域;繁榮的商品經濟和推崇儒雅的社會風氣促進了文人畫的商品化發展,書畫的經濟功能不斷加強,迎合市場需求進行創作與銷售的商品化趨向逐步形成。于是,畫家在一種主動與被動相交織的情境中發生了觀念轉型,并開始以職業畫家的身份參與到繪畫的商品化、世俗化的生產與消費之中。
這一時期,藝術品的價值已不再拘泥于政治教化及文人自娛,而成為一種大眾性和世俗性的商品。如果說高雅的文藝是屬于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專屬品,那么帶有一些“庸俗”感的藝術作品則更多地涉及城市中的小市民,顯示出對普羅大眾個人命運的關注。在社會逐步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個人與藝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藝術逐漸從高高在上的階級權屬中退出,慢慢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是,藝術消費對象的改變重構了藝術的市場需求,而為了適應這種以市民階層為消費主體所形成的新的市場需求,畫家的創作走向、價值取向以及審美意趣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重構。藝術觀念的轉變直接作用于以藝術家為主體要素的藝術集聚,并決定了藝術集聚生產方式及空間形態的轉型。這種觀念轉型從吳門畫派、揚州八怪到海上畫派、嶺南畫派,隨著商業社會和藝術市場的不斷發展而表現出逐漸加強的態勢。
(二)生產驅動:商業發展與“準市場化”
如果說宋代年畫生產集聚由生產與生活相互雜糅的家庭生產組織形式所驅動,具有典型的小農經濟特征;那么明清畫派作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藝術集聚現象,則在商品經濟與文化分工得以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受到了“準市場化”的驅動。
商業作為一種具有交易服務性質的行業,在實現商品交換的經濟活動中助力于其他生產性領域的發展。城市的繁榮、市民階層的出現、藝術市場的完善,使得所在空間呈現出城市化、商品化、分工化等現代化轉型的時代特征,而這些現代性特征同時又培育了藝術集聚新生命形態的出現,促進了明清畫派在蘇州、揚州、上海、廣東等經濟發達城市的崛起與興盛。
以海上畫派為代表,五口通商后,上海作為現代化城市快速崛起,繪畫市場的商業化和市場化程度也隨之提高。以“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豫園書畫善會”為代表的美術社團,和以“九華堂箋扇莊”“古香室箋扇莊”為代表的箋扇店,為畫家提供品定潤格、推介售畫的中介服務,對畫家的宣傳、扶植以及作品行銷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以《申報》《神州吉光集》為代表的報刊媒介則登載潤例、推廣作品,運用新興的印刷技術和宣傳媒介提供全新的銷售渠道,進一步推進了繪畫的商品化趨向;[9]以王一亭、嚴信厚、朱佩珍、虞洽卿、李薇莊、席子佩、杜月笙、黃金榮為代表的富商階層的直接贊助與支持,又為吳昌碩等大批畫家提供了優厚的創作與銷售環境,促進了藝術消費與藝術生產之間的良性循環;潤例制度的形成使書畫交易活動更加有章可循,書畫價值由審美價值轉向商品價值,并確立為一種市場規范;而逐漸壯大的市民階層在重商主義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匯的社會氛圍中,成為一個龐大的書畫消費群體,決定了書畫作品旺盛的購買力與需求量。
可見,海上畫派的藝術集聚已經具有鮮明的商業化特征,箋扇店、美術社團、報刊雜志、藝術消費階層等現代藝術市場體系在上海已具雛形,服務于藝術品的流通、展示、宣傳與消費。這極大地促進了各地藝術家在上海的集聚性生產,從而成為藝術集聚的核心驅動力。但由于這種市場化發展在傳統社會末期依然屬于皇權控制下的民間文化市場,民間與宮廷尚未形成以價格為中介的統一的供需調節機制,因此又具有“準市場化”的性質。
(三)物理空間:流動的集中
以明清畫派為代表的藝術集聚在空間形態上與宋代的年畫生產集聚一樣,具有分散性與地域性特征。所不同的是,畫派的地域性集聚建立在藝術家跨地域自由流動的基礎之上,具有典型的主體流動性。這種自由流動的方向及強度由所流入地區的空間吸聚力所決定。良好的經濟基礎和藝術市場、濃厚的人文環境和文化底蘊、寬松的政治環境以及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等因素,共同構成了某一地區對藝術家的空間綜合吸聚力。其中,由于藝術家對市場的高度依附性,經濟基礎及市場條件成為最關鍵的決定性要素。
從地方畫派在蘇州、揚州、上海等地的相繼繁榮可以看出,明清時期藝術集聚的空間轉移與江南地區經濟重心的位移呈現出高度一致性。明代中期蘇州的蓬勃發展促進了“吳門畫派”的崛起,康熙后期揚州的經濟繁榮造就了“海內文士,半集揚州”的盛況,清末民初“十里洋場”上海的兼容并蓄孕育了海上畫派的形成。
在重商主義氛圍中,藝術集聚呈現出一種基于物質效用和市場需求的流動性特征,并在藝術風格方面體現出多元性。張鳴珂曾在《寒松閣談藝瑣錄》中記載:“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10]各地畫家挾藝來上海者,僅《海上墨林》所錄就有741人。這種流動性的地域性集聚聲勢浩大,文化之雜糅前所未有,從而打破了農業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限局域藝術集聚,呈現出以經濟理性為主導的跨地域藝術集聚。
三、工業社會轉型中的藝術集聚:改革開放后的文化空間再造后工業社會是一個由商品轉向服務的感性回歸階段,知識取代資本而成為社會運轉的中軸原理。文化生產與消費活動的意義不再僅限于繁冗工作之余的娛樂消遣,而轉化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隨著改革開放及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體制與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中國的部分發達城市率先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呈現出由生產轉向消費、以文化和美學介入社會發展與空間更新的全新發展模式。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之下,藝術家對農村閑置房屋和城市工業遺產的藝術介入,使得藝術集聚獲得了全新的生命形態,并以文化空間再造的嶄新姿態一躍成為促進產業轉型和城鄉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文化場景。
(一)觀念形態:自我實現與身份認同
改革開放后,藝術集聚觀念轉型的關鍵在于一種對康德所稱的“主體性”觀念的展開,“應該看到個體存在的巨大意義和價值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個體作為血肉之軀的存在,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的進展,在精神上將愈來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獨特性和無可重復性。”[11]在由集中統一的同質性社會向多元化社會的轉型中,藝術家作為社會結構中具有敏銳洞察力和感知力的群體之一,思想解放帶來的個人主體性話語回歸激發了一部分藝術家對新空間的探索激情。對藝術家特別是前衛藝術家來說,后工業社會的藝術觀念是對工業時代程式化、標準化的藝術觀念的解構與重構。他們崇尚自我表達、追求個性化的藝術理想,而藝術集聚恰恰為這一群體提供了身份認同的紐帶與自我實現的空間條件。這種源于共同的審美意趣與生命感悟所形成的心理認同構成了藝術生產的空間吸聚力,從而為畫家村等藝術集聚區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并在藝術家追求個性化藝術理想的身份建構中,被賦予價值認同與自我實現的意義。
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夾縫中,以圓明園為代表的畫家村作為一種特殊的生存現象與精神現象,呈現出一個非主流藝術群落在市場語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權利訴求及理想主義追求,描繪出理想主義的社會化敘事。“它既是人生觀、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的一種追索與‘探險,又是社會多樣性、包容性、異質性的轉折點和里程碑”,是一個具有人格共性的心靈共同體。[12]而隨后出現的宋莊、北京798、上海莫干山M50、成都藍頂、昆明創庫等藝術集聚區,雖然呈現出一種由政治、資本與社會所同構的綜合性藝術場域,但就藝術集聚的核心主體——藝術家而言,仍具有追求個性化與自我實現的價值意涵。這種觀念形態構成了藝術集聚的空間凝聚力與吸引力,是當代藝術集聚得以有機運行的根本價值指向。
(二)生產驅動:多重權力的闡發
畫家村、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等藝術集聚的新形態是計劃經濟下集中統一的同質性社會向市場經濟下多樣化、分散化社會轉型的產物,也是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變革期多重權力相互交織而形成的獨特文化景象。具體而言,當代藝術集聚的生產驅動呈現出由自發型向體制型的轉變。
改革開放初期,以圓明園、東村等畫家村為代表的藝術集聚由于與主流社會表現出格格不入的“異質性”,因而以一種自發性、地下性的姿態寄生于社會邊緣。藝術家對個性化藝術理想的追求以及對波西米亞式生活方式的向往,成為當代藝術集聚初期的主要驅動因素。
21世紀以來,隨著文化在國家戰略轉型中的地位提升,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政策扶持力度逐漸加強。藝術集聚與政治權力在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磨合之后開始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實踐場所。在政治權力的主導下,經濟、社會、文化等權力要素共同施力于藝術集聚空間,并最終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藝術生產方式促進了藝術集聚空間意義的制度化確認。至此,藝術集聚的主體結構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由過去單一的藝術工作室發展成為集工作室、畫廊、藝術中心等藝術機構于一體的集聚形態,并且逐漸與主流社會實現對接,其社會功能及文化經濟價值不斷凸顯。在政府“收編”與政府“再造”的過程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在全國范圍內快速推進。
至此,中國當代藝術集聚的生產驅動由自發集聚升華為一種有意識的體制性構建,完成了從自然生長到制度建構的形制轉變。藝術集聚不再是文化藝術的單向度行為,而具有了促進產業升級、增加就業、振興內城、改善地方形象等多元化功能。這種轉變反映出率先發生于經濟體制層面的當代社會轉型逐步帶動了政治、文化及社會的演變,并因此產生了一種社會整體性的聯動效應。從自發生長到體制規劃,藝術集聚與主流社會的關聯性日益緊密,由社會文化邊緣逐漸走向社會內部,成為社會文化和經濟運行機制中的一個環節。
(三)物理空間:文化空間再造
就實體性的物理空間而言,無論是宋代年畫生產以家庭作坊為依托的在地性集聚,還是明清畫派基于市場要素的流動性集聚,傳統社會的藝術集聚均具有分散而廣泛的地域性特征。藝術創作、流通、消費所占據的物理空間散點式地分布于城市或鄉村的社會空間安排之中,與其他功能性的生產與生活空間既相互雜糅又相互作用。與之相區別,工業社會轉型中的藝術集聚形成了固定而聚焦的獨立性空間。依托于舊工業廠房、倉庫碼頭、閑置的鄉村屋舍等特定物理空間,藝術集聚以一種空間嵌入的方式躋身于城鄉的空間建構之中,開始以獨立性的生命個體形態與整個社會空間結構進行互動。
在對原有空間的功能再造過程中,藝術集聚賦予歷史文化文本被重新進入、理解、詮釋、體味的可能性,從而使之在這個意義上具有了文化空間再造的價值意涵。具體而言,中國當代藝術集聚對物理空間的文化再造主要分為城市工業遺產再造以及鄉村閑置房屋再造兩種模式。
一方面,城市工業遺產再造,是維護城市多樣性、延續城市文化記憶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自20世紀中葉美國蘇荷藝術區誕生以來,工業化與后現代藝術相互融合的空間再造方式,賦予了工業遺產空間以新的生命活力,并逐漸演化為一種個性化的創作與生活模式,在全球得以廣泛運用。20世紀末,中國的一些大城市率先向后工業社會轉型,工業建筑的原生性功能因難以滿足城市空間的現實需求而日漸衰敗,日益淪為城市舊影。作為城市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工業廠房承載著工業時代一座座城市的深厚歷史記憶,是保持城市生命形態完整性、延續性、多元性的重要物質載體。而工業文化遺產所具有的租金低廉、空間開敞、光線充足、可塑性強、時尚復古等特征,對藝術家產生了強烈的吸聚力。以北京798、上海莫干山M50、昆明創庫、杭州LOFT49、無錫北倉門、西安紡織城等藝術區為代表,工業文明與當代藝術相碰撞,閑置的工業空間在藝術賦能下成為藝術集聚的新空間,衍生出獨特的文化符號,從而開啟了藝術與工業空間“合體”的中國實踐。
另一方面,鄉村閑置房屋再造模式,形塑農耕文明與后現代文明的空間結合體。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和城市化的持續推進,大城市周邊的鄉村地帶愈來愈呈現出空心化趨向,從而導致其原生性功能的退化。對于一些少數民俗古村落而言,鄉間屋舍更是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承載著傳統民俗文化的傳承與變遷。自然退化亦或人為拆建,均不利于鄉村文化的延續和活化,而以藝術集聚的方式進行藝術介入,則為鄉村振興和文化遺存保護提供了新路徑。以北京宋莊、嵊州藝術村、觀瀾版畫村、青海熱貢藝術村、杭州濕地藝術村、四川濃園藝術村等為代表,鄉村型藝術集聚打破了固化的農村文化空間結構,以城市所具有的新銳、先鋒、前衛的藝術理念重塑了農村原有的文化生態,從而使鄉村作為藝術家空間逃離的精神原鄉和城市文化資源的涵養地而煥發出新的生機。
結語
概言之,藝術集聚的演進與社會轉型呈現出一定的歷史同構性,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重構了藝術集聚的驅動因素及表現形態,而轉型過程中經濟、政治、文化所構成的綜合場域的不斷演變又決定了藝術集聚的空間與功能變遷,從而賦予藝術集聚以不同的社會意涵。當前,中國社會進入更為深刻的轉型時期,藝術集聚同時基于城市更新及鄉村振興雙重維度與社會轉型發生互構。然而,社會轉型中存在的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正在使藝術集聚陷入資本運作的發展瓶頸之中,而如何平衡藝術與經濟的關系,將構成藝術集聚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命題。
參考文獻:
[1]王宏建.藝術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25.
[2]魏廣志.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視角與實質[J].青海社會科學,2013(06):33-35.
[3]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M].高铦,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9.
[4]王樹村.中國年畫史[M].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2:11-12.
[5]河南省地方史志編篡委員會.河南史志資料叢編·河南土特產資料選編[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443-444.
[6]劉德龍,杜明德,牛亞慧.民俗[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8:188.
[7]張學亮.齊魯儒風——齊魯文化特色與形態[M].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87.
[8]陸云達.中國美術(圖文珍藏版)[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16:275.
[9]孫淑芹.近代海上畫派的商業運作模式探究[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1):138-141.
[10]曾繁森.中國美術史[M].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99:173.
[11]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3.
[12]于長江.在歷史的廢墟旁邊——對圓明園藝術群落的社會學思考[J].藝術地圖,2005(05):15-27.
(責任編輯:楊飛涂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