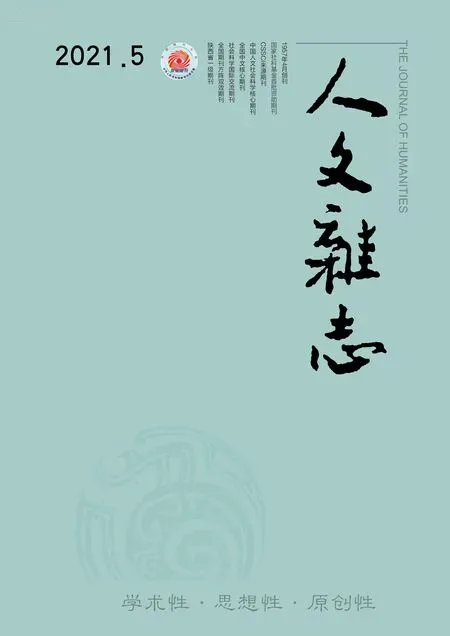領有與自由:拉埃爾·耶吉的異化理論
閆高潔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21)05—0087—08
一、為什么應當關注耶吉的異化理論
當下在大西洋兩岸的哲學界中活躍的柏林洪堡大學教授拉埃爾·耶吉(Rahel Jaeggi),是第四代批判理論的一位重要代表。作為著名學者霍耐特的弟子和曾經的助手,耶吉不但熟悉從阿多諾、哈貝馬斯到霍耐特的思想傳統,以及黑格爾、馬克思、海德格爾、阿倫特等歐陸人物的洞見,而且擅長調取北美哲學界的杜威、羅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學者的研究成果。通過靈活地運用這些素材,耶吉成功地介入了同時代的資本主義批判和實踐哲學的領域,也在學術的波瀾中確定了自己的位置。她的思想愈發受到目前學者的注意。
在與弗雷澤(Nancy Fraser)等學者一起構建的資本主義批判和方才出版的《進步與衰退》(Forschritt und Regression)之外,耶吉還撰寫了兩本知名的專著:《異化:關于一個社會哲學疑難的現實性》(Entfremdung:Zur Aktualita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以及后來的《生活形式批判》(Kritik von Lebensformen)。于此,《異化》的思想意義是首要的。在《異化》中,耶吉精彩地達成了消化以往的觀念與構造新的異化理論的任務。她不但展開了自己的思想路徑,而且推進了相關的研究。憑借《異化》,耶吉開始取得哲學界的普遍承認。霍耐特斷言,人們當下如果希望繼續利用“異化”概念來反思社會關系,就應當閱讀《異化》——知曉耶吉的異化理論。
“異化”這個被廣泛應用的著名術語,一度是20世紀思想舞臺的明星。在盧梭、黑格爾、馬克思、克爾凱郭爾、齊美爾等人物的影響之下,多樣的資本主義批判和流行的人道主義觀念,一度把“異化”概念抬升到極其顯著的地位。歐陸哲學界的盧卡奇、海德格爾、馬爾庫塞、弗洛姆、薩特、阿倫特等思想家,都闡述過自己的異化理論。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思想變化與范式轉換,“異化”概念幾乎不再為專業的學者所強調,甚至趨于被遺忘;這樣的傾向于我國同樣存在,縱然是稍晚的、隱蔽的。同時,伴隨著現實的市場經濟、文化生產和知識技術的發展,形成準確的社會診斷的需求依舊存在。面對這樣的狀況,耶吉決心借助晚近的成果,更新(而非重復)與拯救“異化”概念,構造一種同時代的觀念可以容納的、合理的社會批判學說。她認為,所謂的異化現象仍然需要并且能夠得到正確的把握。
在《異化》中,耶吉首先清算了以往的異化理論,說明了思想工作的條件、基礎與方向。進而,她借助圖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普勒斯納(Hel-muth Plessner)、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等學者的主張正面解釋了自己的異化理論。在我們的視角中,耶吉連結了“異化”概念和目前的思想事業,還勾勒了一種社會性的、解放性的批判。不過,她仍然需要補充關于“客觀的”社會機制與社會團結的論述。在以下的部分中,我們將更具體地表述這些理解。
二、耶吉的回顧、檢驗和重新構造
耶吉的異化理論不但具有展示自己思想成果的環節,而且具有反思以往的異化理論的環節。后者給前者標示了表現的場所和側重,也給前者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耶吉首先通過這樣兩種方式總結了以往的異化理論:建立有關的譜系,并且描繪它們揭示的現象。繼而,她指認了以往的異化理論所蘊含的兩種本質主義疑難:家長主義和主體主義。然后,她抓住了“領有”與“自由”兩個概念,憑借它們重新規定了異化。
在開端處,耶吉斷言,“異化”概念已經被給予了豐富的內涵,例如無力、束縛、支配、冷漠(意味著情感的“無同情”和活動的“無參與”)、內部的分裂、對自我和自我遭遇的世界的無關系。故而,與其說“自我異化”“對象異化”“世界異化”等稱謂指向若干互相排斥的狀況,不如說它們意味著異化的具體的方面。相應地,在“異化”概念和其他的說法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線:“甚至在初次遭遇這一主題時我們就可以發覺,‘異化是一個具有‘模糊邊緣的概念。”例如,在學術的行話中,“異化”和“物化”“失范”“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等詞匯就顯現出“家族相似”。我們知道,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以及盧卡奇的“物化”概念,當下于我國哲學界仍然是顯著的比較對象。
根據以往的思想,耶吉在自我一自我遭遇的世界視角中歸納了七種主要的異化現象。它們展現了“異化”概念不同的意義側重,尤其個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傷害的各種狀況。這樣的提煉盡管或許是不完善的,卻生動地刻畫了異化的面貌。這些情景包括:第一,某人為自我不能接受的欲望所擺布,非本真地、刻意地活動。第二,某人不能認同他參與的事務,或者剝離了自己的目標和事務的屬性。例如,勞動者為了生存被迫忙于既定的工作,市民為了攫取私利去結交“朋友”。第三,某人中斷了自己的社會參與。他無法同周圍的社會環境妥協—和解,無法將這些條件把握為自己的定在形式,被迫在思維與活動中同它們隔離和對抗。于是,他時常感到世界的陌生和自己的孤獨,像失去了家園與“根基”一樣。第四,人的、人與對象的關系之去個性化一物化(the depersonalization and reification)。于此,人的、人與對象的關系,不再是若干憑借人和事物的個別的特征建立的關系,已經變成了一種遭受外部的抽象的中介統治的關系。它們顯現出同一的、自主的、非人的形象。“金錢戰勝了情誼”,以及馬克思和盧卡奇強調的“先前并非市場交換對象的物或者領域的商品化”,就展現了這樣的紐帶。第五,面對現代社會的日益精細的勞動分工,“完整的人”消失了,個人的生命趨于碎片化、狹隘化、屈從化。第六,密集的藩籬與冰冷的牢籠制約了人活動的空間,人改造現成的社會機制的力量被扼殺了。官僚管治,尤其歐陸法系對審判者功能的安排(模板是自動售貨機器),就展現了這樣的狀況。第七,那些引起痛苦的、無意義的、不合理的情景。它們被顯著地反映在卡夫卡、布萊希特、加繆等藝術家的作品中:人突然變成了非人的甲蟲(《變形記》);神仙找不出善良的人(《四川好人》);人陷入了無盡的苦役(《西西弗神話》)。
相應地,耶吉考察了“異化”概念發展的脈絡。她認為,人們對異化的把握經歷過四個主要的階段。第一,盧梭的思想可以被視為所有異化理論的源泉:“盡管‘異化這一術語本身是缺席的,盧梭的著作卻含有以往的和現在的異化理論(在社會哲學的意義上)依賴的一切關鍵的主張。”盧梭勾勒了“自然中的人”和“社會中的人”的差異,將現代文明所塑造的人視為非本真的、不自由的“奴隸”,呼吁調整既定的社會機制。當然,盧梭沒有追求返回所謂的自然狀態,他希望人在社會中并且憑借社會恢復“天性”。
第二,黑格爾的思想標志著經典異化理論的轉折。早先異化理論的中心往往是回答“個人怎么在社會中喪失了自我”這一問題(例如盧梭的認識),黑格爾則把思想焦點變換為回答“個人怎么同社會分裂了”這一問題。黑格爾拒斥了關于單子式的獨立的人和他們的自治(Selbstherrschaft,autonomy)的想象——洛克、盧梭、康德等人物則表達了這些觀念。他認為,所謂的個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教育和國家權力中活動的個人。在現實的、必然的倫理生活之外,并不存在自由的土壤。揚棄異化,抑或自我規定(Selbstbestimmung,self-determina-tion)與自我實現,必須通過認同和參與具體的社會活動來完成。
第三,在關注人的生存的潮流中,克爾凱郭爾和馬克思分別在倫理和經濟的向度之上更新了“異化”概念。他們都依靠“領有”這一概念②闡發了自己的社會批判(例如,前者在《非此即彼》中,后者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當然,前者以個人的獨特性作為樞紐,后者希望重新形成“類的屬性”。他們由此勾連了“異化”和“領有”兩個概念——在洛克、盧梭、黑格爾等人物的領有理解之下。
第四,“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理論的傳統綜合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韋伯的社會學說、生存主義的境況反省、精神分析等資源,構造了新的指向社會總體的異化理論(間或通過“物化”概念)。海德格爾、阿倫特等思想家的異化理論呼應著它們。憑借這些革新,“異化”概念不但能夠容納豐富的社會狀況,而且更明確地連結了個人的日常生活。于此,以往的異化理論到達了一個輝煌的頂峰。不過,伴隨著更多的討論與推敲,它們也清晰地暴露了自己的缺陷。
耶吉沒有流連以上的環節,畢竟她的目標并非細致地盤點或者直接地應用此前的異化理論。耶吉迅速地進入了檢驗舊的異化理論的階段。根據以上的梳理,她認為,“異化”不僅是一個牽涉“事實”的記述性的概念,更是一個規范性的、批判性的概念。因而,“異化”正是一個典型的診斷性的社會哲學范疇。而為了繼續發揮“異化”概念、激活它的思想力量,當下必須檢驗人們習慣使用的判斷社會問題的法則:人們衡量某些狀況是否屬于異化的標準,究竟是合理的嗎?
耶吉發現,在今天的思想背景之下,舊的異化理論顯現出兩種決定性的本質主義缺陷:專斷的家長主義和抽象的主體主義。而質疑那些原初的、恒常的規定,反對隱蔽的或者公開的本質主義,“已經變成了哲學的‘常識的一個部分”。耶吉分別批評了這樣兩個分支:
第一,對照羅爾斯關于形式性的良善生活的論述,舊的異化理論顯現出客觀主義—完美主義—家長主義(objectivism-perfectionism-paternalism)這樣的屬性。在解釋多樣的異化現象之時,以往的思想家時常將他們規定的人的天性、精神邏輯、歷史規律等條件視為普遍的基礎,還時常將那些實際的情緒、觀念、欲望視為虛假的表象和異化的結果。進而,他們時常將揚棄異化視為遵循自己的設置重新創造完善的境況,或者返回“黃金時代”。在批判理論的傳統中,馬爾庫塞和弗洛姆的著作就體現了這樣的態度。我們還發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由于黑格爾、費爾巴哈和赫斯的影響,年輕的馬克思亦為專斷的家長主義所誘惑:他通過比較現實的“異化勞動”和合理的“類的特征”闡發了恢復人的本質的需求,以及反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必要性。
耶吉指出,根據現代社會的基礎觀念,個人應當理智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形式,并且自覺地成為它的最高的解讀者,而非倉促地順從外部的權威。然而,以往的思想家(例如盧梭和黑格爾)時常試圖完全地替代個人去診斷異化與揀選出路。他們時常示意,只有自己的認識才說明了什么對個人是正確的、更好的、真實的。于是,他們盡管誠摯地宣揚了“自由”“人”等概念,卻沉默地壓抑了創造性的意愿和多樣的生活形式。
第二,根據阿爾都塞與福柯對流行的人道主義觀念的抨擊,以往的異化理論難免具有抽象的主體主義。在這樣的思想中,普遍的“人類”或者特殊的“集體”被視為絕對的、原初的實質力量;它們既是異化的制造者、經受者,又是異化的克服者;它們將通過超越既定的狀況、重新領有被剝奪的本質,再次占據現實的主體地位。例如,費爾巴哈的著作就體現了這種決定性的知識結構(尤其在阿爾都塞的視角中):普遍的“人類”本該是世界的起源、中心和動力;然而,宗教竊取了它的權柄,把它的身份交給了上帝。薩特與“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亦陷入了類似的設置。我們還發現,在許多學者的把握中,盧卡奇對物化現象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審視也沒有擺脫以上的圖式。
耶吉指出,主體主義將“主體”概念把握為自明的開端,是不實際的。主體(subject)不是最終的源泉,而是現成的觀念與權力傳喚群眾的結果;它通過這些機制生成,也臣服于(is subject to)這些機制。例如,人們只有在得到一定的經濟秩序、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承認之后,才可以成為“正常的”經濟主體、法律主體和道德主體。因而,主體主義已經無法建立更具體的、更深刻的異化理論了。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中,這樣的圖式僅僅趨于重復與裝點舊的言辭,往往不能描繪人們與世界的復雜關系。同時,它磨鈍了“異化”概念批判性的向度:仿佛人的“命運”就是承受異化的壓制。
鑒于此前的異化理論與流行的本質主義思維的瓜葛,以及這樣的關系造成的缺陷,耶吉希望一邊分離合理的因素和舊的框架,一邊重新組織“異化”概念。我們認為,這樣的努力是正確的。今天的社會批判仍然需要接納關于切近的異化現象的討論,而非輕蔑地拋棄它們或者直接地假定它們并不存在。耶吉首先發現,“異化”這個解釋人們與世界的關系的重要術語,大致具有三種顯著的特征:
第一,異化標志著喪失力量與喪失意義,從而指向不自由的狀況。異化不但令自我和自我遭遇的世界變成了人們不能干預的、獨立的、壓迫性的實存,而且引發了若干消極的感受,例如無聊、迷茫和苦悶。這樣的交織以自我規定和自我實現的必然的聯系作為條件。自我規定與自我實現正構成了現代社會的思想核心。它們分別展現了“自由”這一概念消極的向度與積極的向度。它們不應當被視為兩種互相排斥的屬性。去除自我實現的自我規定(例如“返回田園”),以及去除自我規定的自我實現(例如僅僅按照父母的意愿度過人生),都是空洞的。
第二,異化一邊標志著支配,一邊區別于非自由抑或他治(heteronomy)。人們作為異化的經受者不是僅僅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而是自發地參與了相應的過程:“在一個角色中或者通過一個角色異化的某人,同時親自扮演著這一角色;為異化的欲望所指引的某人,同時擁有這些欲望——于此,我們倘若只談及被內化的強制或者心理的操縱,就難以辨識特定狀況的復雜性。”
第三,與其說異化(entfremdung)指向陌生(Fremdheit)抑或本該存在的關系的缺失,不如說它指向人們無法容忍的現成的關系抑或“無關系的關系”。故而,設想“一種在邏輯上、在本體論上或者在歷史上優先的關系”或者若干和諧的、完善的關系,并非建立“異化”概念需要的內在步驟。根據這種新的理解,“異化”概念其實可以抗拒本質主義的干涉與誘惑。
耶吉進而借助圖根德哈特的概念“意愿的作用能力”抑或“能夠指令自己”重新表達了“領有”概念。圖根德哈特的概念“意愿的作用能力”抑或“能夠指令自己”,勾勒了關于現代社會良善生活的尺度。它的內涵是:如果一定的生活形式允許個人持續地表述與落實自己的意愿(區別于沖動的任性)、籌劃與修訂(區別于固執地堅守)自己的意愿,那么個人就展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這種一般的標準不但避免了專斷的家長主義和抽象的主體主義,而且保存了人們仍然追求解放與自由的可能性。這樣的設置同時協調了主觀性和實在性的地位(抵制靜觀和盲動)。
耶吉斷言,以上的方向也適用于反思“領有”概念。參照以上的規定,領有不僅意味著占據—支配—利用現成的物質財富,更意味著處理事情—生產知識—解決疑難;它不是本質主義的“再次領有”(reappropriation),而是著手、改變與創造;它調節了人們的狀況、現實的世界和有關的聯系,反映了自我規定和自我實現的個別的需求,并未設定必然的目標與最終的和解。因而,領有標志著一種積極的、解放性的、無限的活動。它召喚當事人在所有的生活領域中持續地變革自我和社會關系。
于是,“領有”可以成為一個衡量人們與世界關系的基礎范疇:“‘領有概念關聯著一種建立同自我和世界的關系的方式、一種應對與指令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在這樣的視角中,“異化”概念也被給予了新的規范與意義:它標志著“一種對領有活動的損害(或者一種含有缺陷的領有實踐)”,展現了領有受到阻礙的局面,抑或自我和自我遭遇的世界的不適合的(inapropriate)關系。它不但保留了具體的個人自由成長的空間,而且把判斷異化的權力交給了思考境遇的個人。相應地,揚棄異化不再牽涉“恢復”“回歸”等說法,它僅僅指向轉變與掌握現成的事態。
無疑,耶吉的主張至此還是抽象的。她尚未回答一個決定性的問題:以上的洞見究竟具有怎樣的思想效果——它們如何改造了其他的觀念,如何幫助了人們認識自己的境況,如何支撐了新的異化理論?我們察覺,耶吉轉而借助剖析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推進了自己的工作。由此,她的異化理解不僅增添了生動的色彩,更獲得了細致的澄清。輕視這些段落是不正確的。
三、耶吉的場景解讀與概念雕琢
借助“講述故事”與分辨不同的觀念來開辟明確的思想路徑,是耶吉異化理論的特色。在重新規定“異化”概念之后,她根據個人(尤其女性學者)容易領會的事實構造了四種典型的生活場景,通過聚焦它們闡發了復雜的研究線索,從而發揮了自己的中心概念,連結了同時代的討論和自己的態度。在今天的哲學話語中,這樣的安排顯然異于哈貝馬斯、羅爾斯等學者習慣采取的言說方式——倚仗抽象的推演論證,排除鮮活的生活經驗。
第一種情況的主題是“無力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的感覺”,抑或領有。在故事中,一名新近締結婚姻、更換住所的青年學者察覺,自己的生活似乎突然被“外部的”必要性統治了:在完成心愛的工作之外,他不得不消耗精力來應付繁瑣的家務與交往。他聲稱,自己的生活異化了——而這樣的理解意味著什么呢?
耶吉指出,主人公的體會不以生活環境的變化作為內在的條件,也不以生活環境的陌生作為合理的原因。即使生活環境保持同一的狀態、主人公熟悉目前的節奏,異化的感受也能夠憑借現成的事態產生。同時,主人公的狀況區別于強迫、他治與非自由。主人公積極地營造了目前的生活方式,并且自發地促成了異化的困難,“外部的”力量從未完全地操縱他。故而,以往的異化理論終究不能處理這種混合的癥狀。耶吉認為,主人公的疑難其實揭示了領有受到阻礙的局面——領有意味著持續地調整自我和周圍世界的關系(在后來的《生活形式批判》中,這些規定則被給予了“實踐”概念)。“相反地,異化就是這一過程的停頓。”
第二種情況的主題是“角色行為”(role behavior),抑或自我。在故事中,一名青年編輯故作興奮地參與那些專業的會議;一名金融咨詢師,為了給消費者留下好的印象,分外精致地裝扮自身;一名新手播報員,為了爭奪人們的注意,刻意地塑造活潑的風格。他們似乎佩戴了虛假的面具,失去了赤誠的天性。
耶吉指出,主人公的處境區別于強制,也區別于偽裝一欺騙。他們沒有被迫承擔既定的角色,也沒有主動隱瞞自己的意愿。同時,借助某些比喻直接地宣稱“造作的自我”和“本真的自我”存在并且疏離,亦不能清晰地表述以上的狀況。例如,有關的批判不應當忽視戲劇角色和社會角色的差異,或者混淆表演和謀生、特殊的場所和一般的生活世界。戲劇角色和社會角色盡管具有類似的稱謂,卻是不同的規范集合。面對這些觀念,耶吉調用兩種思想更新了關于角色行為與自我異化的認識:普勒斯納的社會人類學,以及齊美爾的社會哲學。
普勒斯納認為,社會角色不僅體現了社會秩序,更促使人們“形成自我”。誠然,“社會強加的規定”和“本身的規定”這樣的說法并非無意義。可是,劃分“外部的法則”和“自己的法則”,不等于設定一種靜止的、純粹的本質和兩個互相沖突的領域。“外部的規定”和“自己的規定”其實是貫通的、變動的,個人可以根據特殊的需求反復地劃定它們的界線。在這樣的視角中,人抑或自我像洋蔥一樣,盡管囊括不同的層次,卻沒有穩固的核心。而齊美爾認為,社會角色是培養主體的活動能力的學校,意味著人的定在的“理想形式”(ideal form)。如果缺少這種制約性的裝束,那么人的實存就是空洞的、不實際的。例如,個人一旦逃避了可能的社會參與,就不能取得相應的生活教訓。
根據以上的思想,人抑或自我不是既定的,而是社會性的、變動的、開放的。馬克思也講過:“在真實中,它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當然,齊美爾和普勒斯納都沒有否認異化的實存。因而,與其說個人為社會角色所異化(by social roles),不如說個人在社會角色中異化了(in social roles):“個人通過社會得以生存,也受到社會的脅迫。”耶吉強調,角色行為造成的異化現象不能被視為非本真的規矩遮蔽了人的天性。它標志著自我與社會條件的共同的局限,同樣展現了領有凝滯的狀況。它也召喚了自我與社會條件的共同的發展。
第三種情況的主題是“作為內部的分裂的自我異化”,抑或認同。于此,耶吉推進了關于自我異化的討論。在故事中,一名女性主義者篤信自己的理念,希望成為一個自主的人。她反對服從既定的性別權力。然而,她同時察覺,在與伴侶戀愛之時,自身似乎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清醒的人,反而如同一個柔弱的、愚笨的孩童。她感到,“熱戀的自己”仿佛與“真正的自己”割裂了。
耶吉根據有關的描述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應當如何認識“某人不能認同他所懷有的意愿”這樣的狀況?其二,應當如何判斷個別的意愿的屬性——它是自己的或者外部的,主要的或者次要的?通過分別繼承和超越法蘭克福關于意愿等級的論述,耶吉解答了以上的疑問。
法蘭克福認為,個人的意愿可以被歸入兩個類型:要么是一級意愿,要么是二級意愿。二級意愿以決定堅持或者放棄一級意愿作為要旨。例如,“想要抽煙”就是一級意愿,“打消‘想要抽煙這個已有的念頭”則是二級意愿。耶吉指出,人們擁有而不能接受的意愿,例如“做一個可愛的女友”,便是無法收獲現成的二級意愿管制的一級意愿。它并非“客觀的”錯誤或者人們不能干預的“無意識”。當然,所謂的二級意愿,例如“別成了一個傻氣的女友”,不必然地是根本的、真實的觀念。依靠以上的結構回答第二個問題是不正確的。耶吉轉而重新解釋了“認同”這一概念。她指出,與其說認同標志著“穩固的自我”可以接納目前的意愿,不如說認同標志著這些觀念可以彼此結合、彼此匹配。故而,外部的意愿和異化的意愿,其實是無法為自我理解抑或一定的意愿整體所吸納的各種欲求;主要的意愿或者次要的意愿,則標志著這些觀念在自我理解抑或一定的意愿整體中享有不均衡的地位。耶吉強調,自我理解是變動的,它應當為了實踐、在實踐中形成鮮活的適當性。不適合的統一性將擾亂個人的規劃,“我們無法隨著它生活或者在其中活動。”我們發現,內部的分裂由此告別了本質主義的讀解。
第四種情況的主題是冷漠和自由。在故事中,一名語言學教授被瑣碎的程序、繁雜的競爭和空洞的交往擊倒了,為冷漠所俘虜。他喪失了關于科學探索和傳授知識的熱情,覺得這種宏大的事業是虛幻的、無意義的。他停止關心學術的品質和授課的技巧,變成了一個僅僅消極地、麻木地應付任務的人。在這樣的事態中,對象異化和自我異化再次一起出現了。
耶吉指出,以上的狀況首先異于自我轉型和興趣遷移,它意味著個人脫離了以往的關系。不過,所謂的脫鉤一分離區別于關系的消除,它終究產生了異化的關系抑或“無關系的關系”:“冷漠的態度導致的或者由此產生的與世界的分離,是虛假的;甚至在冷漠中仍然存在對世界的關系——一種防御性的、已經被證明含有缺陷的關系。”繼而,以上的狀況不等于“獲得自由”。法蘭克福和黑格爾已經說明了自由和冷漠的差異:法蘭克福主張,冷漠限制了人們的活動、損壞了人們的個性、磨滅了人們的生命性,不利于自我規定與自我實現;黑格爾則主張,冷漠僅僅維護了“內部的自由”——不實際的、抽象的、恣意的自由。真實的自由需要超越主觀性、包容實在性,通過歷史性的一社會性的運動顯現出具體的面貌。因而,個人應當積極地介入目前的日常生活。
我們察覺,憑借剖析生活場景,耶吉不僅展現了新的異化理解的概念內涵和實用性,從而推進了今天的社會批判,更奠定了一種新的倫理學說的基礎。畢竟,她對生活場景的闡釋,既揭示生活問題,又是規范性的(提供了一定的行為向導),既指向個人的活動,又是社會性的。經過耶吉的修訂,“領有”“自由”等概念,在構成了新的社會批判之外,也能夠重新支持關于人們的社會屬性、社會功能與社會地位的討論(例如關于勞動意義的討論),以及關于可能的政治改革、文化建設與社會轉型的討論(例如,在后來的《生活形式批判》中,她就借助以上的規定提示了一種批判性的倫理思想)。無疑,耶吉的澄清還可以幫助專業的學者深入同時代的哲學話題,促使他們更新自己的立場。《異化》的第三個部分作為延展性的環節加強了這樣的效果。
四、耶吉的異化理論具有怎樣的特征
根據以上的介紹,我們認為,耶吉的異化理論大致具有四種決定性的屬性。第一,它的要旨是重新安放自我和自我遭遇的世界的關系,抑或“人”和“社會生活”的關系。相應地,它的思想對象是寬泛的,囊括了工業的和智力的勞動、個別的和公開的交往等等。第二,它的方向是批判而非辯護。它的矛頭不僅指向社會關系,更指向流行的個人的錯誤態度。這樣的意識既是“社會批判”,又是“自我批判”。第三,它的基礎不是以往的(外部的)本質主義設想或者僵硬的觀念系統,而是若干形式性的、開放的、積極的規定。它的結果改進了“領有”“自由”等概念,確認了此前的異化理論的缺陷與貢獻,激活了關于直接的異化現象的言說,并且回應了現實的疑難和學術的討論。第四,它的精神是解放性的,而非保守的或者浪漫的。它的面向是變動的當下一未來。
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中,耶吉的異化理論顯現出兩種主要的思想價值。第一,這樣的反思可以抵抗兩種不實際的觀念:個人主義與浪漫主義。個人主義的意識將既定的或者想象的個人視為原初的、孤僻的、自主的行事者。它以個人的欲求、個人的自由作為首要的尺度,從而誘發了理智的任性(例如放肆和冷漠);它令現代社會的倫理事業(個人的社會責任)下降為脆弱的實存,甚至空洞的表象。由于自發地或者自覺地切分了“獨立的個人”和“外部的社會”,它往往加劇了領有受到阻礙的局面。浪漫主義的意識則將主觀性視為首要的法則,同時放大了人們對自己的狀態和某些事情的美化(例如“黃金時代”)。它回避了關于現實的社會條件和可能的對待方式的考慮,不利于人們參與并且成就具體的社會活動。它往往無法憑借綺麗的理念嚴肅地化解異化的影響。第二,這樣的反思可以抵抗教條主義的異化理解,尤其本質主義的模式。教條主義的異化理解沉醉于以往的觀念系統,輕視了目前的境況變遷與思想演進,不能滿足新的社會診斷的需求。它也無法領會同時代的社會狀況或者融入勃興的社會運動:“這種真實并不存在,它正在生成。”例如,人們如果草率地挪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內容來批評人工智能造成的異化危險,就容易形成顯著的年代錯亂。
相應地,耶吉的異化理論拒斥了通過逃遁與自我封閉應付異化的慣常路徑。在黑格爾、馬克思、阿倫特等人物的政治意識的背景之下,這樣的反思支持人們在社會中并且憑借社會去追求解放與自由,鼓勵人們嘗試逐步改變既定的境況與思想。它沒有迎合流行的粗陋的認識,沒有鼓吹消極的情緒或者陷入玩味異化的沼澤,也沒有否定通過政治性的手段消解異化的可能性。
我們認為,在目前的思想背景之下,引進與吸納耶吉的異化理論、清算舊的異化理解,是一項正確的工作——尤其在個人主義與浪漫主義于我國同樣活躍的背景之下。當然,耶吉的異化理論并非一種完美的批判。我們清楚,它起碼具有一處必然的——耶吉的思想方式造成的——弱點:由于堅持了個人的形式性的視角,它終究缺少(或許不能包容)關于“客觀的”社會環境的論述。這樣的破綻明確地表露為兩個裂隙:第一,在《異化》中,關于具體的社會機制的論述是極其貧乏的。耶吉并未深入現代社會的個別的關系(例如情感勞動和公共空間),她還懸置了德國的和西歐的特殊的狀況。第二,在《異化》中,關于真實的社會團結的論述,抑或關于個人的認同、聯系和組織的論述,也是極其貧乏的。耶吉沒有構造任何群體性的或者政治性的規范,亦沒有關注人們的交流、協作和行動。于是,雖然耶吉展示了一種社會性的、解放性的批判,但是她的思想仍然意味著一種抽象的、不完善的向導。這樣的紕漏同時損壞著“領有”“自由”等概念的魅力與實用性,進而瓦解著耶吉的異化理論的成果與合理性(例如社會性的向度和解放性的向度)。耶吉本人也知曉這種清晰的缺陷。顯然,在此后的研究中,她和其他的學者都應當根據相應的實踐需求來繼續改良現成的思想武器,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立足于自己的“羅陀斯島”,抑或本土的生活經驗。
責任編輯:王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