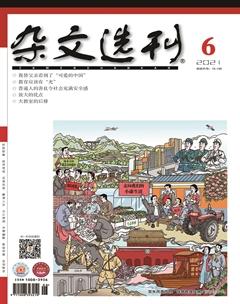她是……
吳任幾
她出生在上海的一條小弄堂里,一家人擠在九平方米的小房間里。
她怕她的媽媽。九歲的時候和一個同學相約周末一起坐公交車去玩,直到要去的當天還是不敢和媽媽提。于是她的同學那天在公交車站白白等了她一整天,從此再也不和她說話。
她學習成績一向優秀,但是從小高度近視。她的母親認為再接著讀書就會“眼瞎”,所以不讓她報考高中,沒經過她同意,幫她報了幼兒師范的中專學校。
她怨恨母親替她作的這個決定,拒絕了畢業后的分配,嘗試自考,兩次都失敗了。面對自己人生的缺憾,她選擇結婚,當時她二十歲,二十一歲就生了兒子。
她的丈夫有一天和她說:“樓下攤煎餅的人都是立志要開連鎖店的。”她明白這是在說她對人生毫無志向。她一邊照顧著懷里啼哭不停的嬰兒,一邊重新復習。這次她考上了。她瞞著丈夫自己出門找工作,才知道自考文憑在求職市場用處不大。
她給她的兒子寫了一封又一封長信,說了很多期望,記錄了很多溺愛的瞬間。可是,她的兒子總覺得過于尷尬,從來不讀。
她的母親晚年時患有重度抑郁癥,接下來的十幾年,幾乎每個半夜都會喚她起來扶自己上廁所。
她終于又考上了全日制的大學。畢業后,她終于如愿成為一名公立學校的英語教師。她給她的學生們寫信,幾年后出版成了一本書,雖然沒有太多人會去讀。
她丈夫辭職,借錢辦了工廠。失敗了,欠了不少錢。他們失去了自己在郊區的房子。他們又擠回了她母親的小房子。
她曾經和好朋友一起合編一本教材。當她拿到署有她名字的樣書時,自豪的感受無以言表。她鄰居家的小孩,在書店里發現真正出版的教材里,封面上只印了她好朋友一個人的名字。她卻一直沒去揭穿那個朋友。
三十六歲的時候,她擁有了像樣的住房,是她跑遍上海郊區才找到的一套能勉強買得起的。
三十八歲的時候,丈夫的姐姐和弟弟把她婆婆安置在她兒子的房間里,把她的兒子安排在了二十公里外婆婆的房子里。她知道這是兒子想要的獨立生活,所以接受了。
她給她兒子買了點新家具運到了房子里。她兒子認為這是她一如既往的入侵,連續幾個禮拜都拒絕和她說話;她整夜整夜地睡不著,高燒不止。
她三十九歲的時候,在兒子的強烈要求下,才開始舍得給自己消費超過兩百元的東西。她四十一歲的時候才開始真正擁有朋友。她現在每天都會接到她兒子給她打的電話。
她還是成天擔心。如果兒子因為工作太忙幾個小時沒有回復她的消息,她會心急如焚。她總是擔心兒子心情不好,在外面受了委屈……她,是我的母親。
她總是設法讓自己和自己愛的人,每天以“比昨天更體面一點”的方式繼續下去,突破生活企圖附加的道道重圍。
她是女兒、妻子、兒媳、教師和母親;正是因此,她便從來就不僅僅是誰的女兒、誰的妻子、誰的兒媳、誰的老師和誰的母親,她還有那么多未知的身份要去經歷……

那么,真正具有含義的詮釋只有一句——她,是一位女性。
【原載《文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