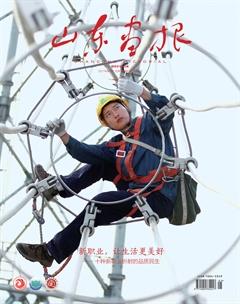建筑幕墻設計師:讓站得更高成為可能
崔秀娜



“建筑幕墻其實就是‘建筑的衣服,我們就相當于是建筑的服飾設計師。”今年38歲的張昌奇是典型的理工男,謙虛謹慎,但是提到“幕墻”,就好像找到了一把打開他心靈的鑰匙,讓他眼神清亮清亮的,話匣子一下子就打開了。
雖然經常工作到很晚,但是只要有空,他就喜歡開車在濟南的路上轉轉,看看哪里又有新建筑了。當看到自己團隊設計的幕墻在車窗前涌現的那一瞬間,他心中的幸福感滿溢。“這也算是我的‘小幸福‘小驕傲吧。”張昌奇笑道。
2007年,大學畢業后,張昌奇開始從事建筑幕墻設計工作,至今已有14年了。現在的他,已是某裝飾設計院的總工了。這14年,他親眼見證了建筑幕墻設計行業的飛速發展。據他介紹,傳統建筑的外墻是砌體加涂料或瓷磚,但因為這樣砌的墻體比較重,所以傳統的建筑大多只能做到十幾層。而現在的高層建筑,外立面幾乎都是幕墻,最常規的就是三大類:玻璃、鋁板和石材。
“正是幕墻的發展,才讓摩天大樓的發展成為可能。現在幾百米的超高層建筑的外立面都是幕墻,是玻璃、鋁板或者石材之間的組合。你在城市的一角,抬頭向上看,總能看到耀眼的玻璃幕墻,那遒勁的金屬骨架、幾何感極強的造型、高聳入云的氣勢,都讓人領略到現代幕墻的魅力。”
1984年,中國第一座現代幕墻高層建筑——長城飯店建成。至此,幕墻技術在中國快速發展。1999年,88層、420.5米的上海金茂大廈建成,成為當時上海的地標性建筑,整個大廈的外墻全部都是大塊的玻璃,在陽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似銀非銀、深淺不一、變化無窮的色彩。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時很多人都以出入金茂大廈為時尚,因為它就是摩天大樓的代表。2009年,中國國家地理出版《天際線增刊》,封面照片就是陽光下熠熠生輝的金茂大廈。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座座城市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當你極目遠望,它們遮蓋了遠方的天際線,于是“天際線”一詞被重新定義。當一幢幢具有視覺壓迫感和震撼力的“鋼鐵巨獸”平地而起之時,“城市天際線”這一概念從此便與摩天大樓緊密相連。
“都說城市是鋼筋水泥的森林,但在現代都市,抬頭向上看,你看到的幾乎全部都是幕墻,而不是鋼筋水泥。”張昌奇笑道。“現在,中國是世界上幕墻需求量最大的市場,也是發展最快的市場。截至2018年,世界10大高樓排行榜中,中國就有6個。”
在張昌奇的辦公桌上,我們看到了他的小團隊為某單位設計的幕墻圖紙,足足有150頁。“這還是比較普通的幕墻,沒有很多復雜異形,如曲面等設計。我們曾經設計的湖州市吳興區文體中心的設計圖紙足足有1000多頁。”
那么幕墻設計的原則是什么呢?怎樣才算是一個設計合格的幕墻呢?據張昌奇介紹,幕墻設計要綜合考慮結構、功能和美學三方面功效。結構方面即幕墻結構設計要滿足力學計算要求,要經受得住風荷載的考驗,不會被風吹壞;功能方面即幕墻要在水密性、氣密性、保溫性能上達標,不能漏水、漏氣,并要滿足遮陽隔熱保溫的要求,減少建筑能耗;美學方面即建筑幕墻要有良好的外觀視效和內觀視效。
“所有的標準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一定要達標,即幕墻一定是可靠的。幕墻設計是建筑設計的一個從屬專業,那么幕墻設計也一定要符合建筑設計最根本的標準,那就是安全。只有幕墻是安全的,才能考核其他美學方面的標準。否則都是空談。”
在張昌奇看來,幕墻設計是一個需要豐富知識儲備的行業。既需要有美學知識、土木工程專業知識,又需要有機械專業知識,更需要力學專業知識。用什么樣的玻璃?幕墻玻璃該做多大面積?怎樣呈現出更好的室內室外效果?怎樣進行可靠的連接等等,這些都是需要幕墻設計師細心考慮的問題。
“我很喜歡建筑這個行業,喜歡看到自己團隊設計的圖紙變成現實的感覺。這種參與感讓我覺得無比幸福。”提到自己的職業,張昌奇的眼中滿溢自豪。
在做幕墻設計師這14年的時間里,他做過很多個項目,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2016年湖州市吳興區文體中心的幕墻設計。2014年,他所在的公司剛成立幕墻設計中心不久,當時業內大體量的曲面異形幕墻建筑還不多見,公司之前所接到的這方面的案例也很少。而湖州吳興區文體中心則恰好就是非常規的場館類異形曲面幕墻。
“我們團隊的壓力很大,但壓力就是動力。”
為了保證幕墻曲面順滑效果,他們自己摸索研究,利用當時先進的BIM技術對建筑進行形體分析,將一個個曲面拆解出來,從而能夠將曲線逐個梳理,剖面逐個研究,根據幕墻面板的曲率范圍、尺寸大小以及異形板的控制對整體幕墻進行系統設計,最終詳細地繪制了圖紙。工作中,還充分利用幕墻繪圖與BIM技術的協同設計。
“現在看來,也正是那時,鍛煉了我們對異形曲面幕墻的設計能力。當時的熬夜、加班都是奮斗前行的必經之路。”
他一直記得當時在600多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廈從上往下看的瞬間。“那是與云端連在一起的感覺,仿佛伸出手就能觸摸到藍天。我喜歡我的工作,因為它讓我明白,站得高是可能的,更讓我明白,站得高就能看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