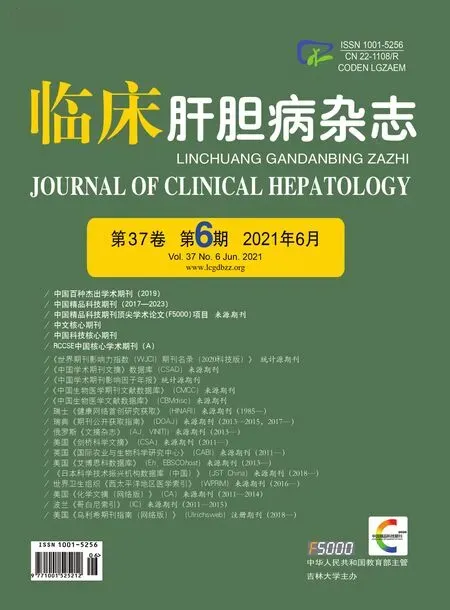紅細胞分布寬度/血小板比值、血小板/淋巴細胞比值、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對慢性丙型肝炎肝硬化代償期的預測價值
楊 娜,何 華,趙天業,陶雪蓉,吳燕華,姜 晶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 臨床研究部,長春 130021
丙型肝炎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流行。2006年全國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1]結果顯示,我國HCV抗體陽性者約760余萬,防控工作不容忽視。在 HCV 感染后 30年,肝硬化發生率約 5%~15%,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中肝癌的年發病率為0.5%~10%[2-3]。慢性HCV感染導致的肝硬化是肝癌發生的重要環節,80%的HCV相關肝癌歸因于肝硬化[4]。但是丙型肝炎肝硬化一般起病隱匿,早期無特異性癥狀,大多數患者發現時已出現門靜脈高壓相關并發癥[5],肝硬化相關死亡已成為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多項研究[6-7]證實肝硬化是一個可逆的過程,因此,應重視肝硬化發生的監測、早期診斷與治療,以改善患者預后,降低肝癌發生率。目前,基于血清學的指標如FIB-4、APRI已被廣泛應用于肝纖維化分期的預測[8],具有成本低、簡易等優點,在臨床實踐中已經逐漸取代肝活檢[9]。與這些指標相比,基于血常規檢測計算的指標如紅細胞分布寬度/血小板比值(RPR)、血小板/淋巴細胞比值(PLR)和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除經濟易得之外,計算也更為簡單,可作為肝硬化監測的補充性、非侵入性指標,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和肝癌、結直腸癌、胃癌等消化道腫瘤的預后評估[10-14]。既往也有研究[15-18]報道RPR可能是預測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發生的一個有效指標,PLR、NLR可能與肝炎病毒相關肝硬化的進展相關,但結論尚不統一,且其與早期肝硬化發生之間的相關性研究鮮有報道。因此,這些指標與丙型肝炎肝硬化代償期的發生發展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研究。本研究主要通過比較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和丙型肝炎肝硬化代償期患者的血清學指標,分析RPR、PLR、NLR與肝硬化發生發展的關系,為完善丙型肝炎患者肝硬化監測指標,預測發生風險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在2019年9月—12月、2020年9月—12月分別在丙型肝炎發病較為集中的扶余縣2個鄉鎮對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開展肝硬化和肝癌篩查。納入標準:(1)根據2020年疫情防控管理相關要求,自備一次性醫用口罩或現場發放,并全程佩戴;“吉祥碼”為綠碼、現場測量體溫<37.3 ℃且無干咳等可疑癥狀;(2)當地常住居民,35~79歲;(3)既往有慢性HCV感染病史;(4)無其他嚴重疾病自愿參加并且能接受肝彈性檢測和上腹部超聲檢查者。排除標準:(1)已明確診斷為肝癌或其他癌癥的患者;(2)合并HBV、HIV或任何其他病毒感染者;(3)合并其他肝病者,如酒精性肝病、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和自身免疫性肝病等;(4)出現門靜脈高壓相關并發癥者。慢性丙型肝炎的診斷標準參照《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19];丙型肝炎肝硬化代償期的的診斷標準參照2019年《肝硬化診治指南》[20]。
1.2 研究方法
1.2.1 問卷調查及質量控制 采用統一的調查問卷,由調查員與被調查者面對面進行調查。調查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性別、年齡和BMI等)、生活習慣(吸煙、飲酒、體育鍛煉等)、肝臟疾病史(既往HCV、HBV等病史)、一級親屬肝癌家族史和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療情況等。吸煙定義為每天吸煙 ≥1支且持續時長超過6個月,吸煙量以吸煙指數(吸煙包年數)表示,計算公式為:吸煙指數=每日吸煙支數÷20×吸煙總年數。飲酒的定義為每天飲酒 ≥50 g且持續時長超過6個月,并計算每周攝入乙醇量,公式為:乙醇量(g)=飲酒量(ml)×酒精濃度(%)×酒精密度(0.8 g/ml)。體育鍛煉定義為每周至少3次,每次至少30 min。在調查現場即完成所有調查表的審核,問卷回收率為100%。
1.2.2 血清學指標檢測 在清晨空腹條件下,采集受試者外周靜脈血,采用邁瑞BC 5800(血細胞分析用溶血劑,南京邁瑞)檢測血常規指標,采用羅氏生化儀(羅氏檢測試劑盒,上海羅氏)檢測肝功能指標。采用HCV核酸定量檢測試劑盒(PCR-熒光探針法,湖南,圣湘生物)對患者血清HCV RNA進行定量檢測,HCV RNA 含量大于50 IU/ml的樣本判定為核酸陽性。根據血清學指標計算RPR、PLR、NLR、FIB-4指數和APRI評分[19]。
1.2.3 Fiber scan和超聲檢查 肝硬度檢測采用Fibro Scan儀(ECHOSENS, 法國)由經過專業培訓的臨床醫師進行檢測。測量方法:患者仰臥位,選擇右腋前線與右腋中線間的第7~8肋間,每人進行10次有效測量,最終取中位數作為肝硬度值(kPa)。成功率>30%或偏差>中位數的1/3視為無效檢查。
超聲檢查采用邁瑞M9便攜式多普勒超聲系統(中國,深圳),由超聲專業工作滿3年以上的主治醫師進行檢查。檢查方法:清晨空腹,采用多種體位進行系統性掃查,記錄肝臟形態大小、肝回聲、占位情況、脾臟大小及有無腹水等。
1.3 倫理學審查 本研究方案經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18K061-001,臨審第(2019-225)號,19K043-001。所有研究對象均在自愿原則下簽署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一般人口學資料 共納入968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其中男506例(52.3%),女462例(47.7%),平均年齡為(59.03±7.61)歲,其中肝硬化代償期患者123例,占12.7%。
2.2 慢性丙型肝炎肝硬化發生的單因素分析 僅高齡組(>60歲)與肝硬化發生有關(χ2=11.543,P=0.001)(表1)。
2.3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與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患者血清學指標比較 與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相比,丙型肝炎肝硬化組患者的WBC、淋巴細胞數量、中性粒細胞數量、血小板、血紅蛋白、白蛋白等指標均降低,AST、ALT、GGT、TBil、紅細胞分布寬度、FIB-4指數、APRI評分均升高(P值均<0.05)(表2)。
與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相比,丙型肝炎肝硬化組患者的RPR升高,PLR降低,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NLR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2)。因此,僅繼續探究了兩個復合指標RPR、PLR對于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代償期發生的預測價值。ROC曲線結果顯示,RPR、PLR預測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發生的最佳截斷值分別為0.081和91.11,曲線下面積(AUC)分別為0.806(P<0.001)和0.715(P<0.001),RPR對肝硬化代償期的預測價值優于PLR(圖1)。根據上述RPR、PLR截斷值將患者進行分組。

表1 慢性丙型肝炎肝硬化發生的單因素分析

圖1 RPR、PLR對于鑒別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代償期的ROC曲線

表2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與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患者血清學指標比較
2.4 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代償期的危險因素分析 將年齡和血清學指標中的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數量、白蛋白、血紅蛋白、總膽紅素、GGT以及RPR、PLR、FIB-4、APRI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中,結果顯示,年齡>60歲、白蛋白<40 g/L、RPR>0.081、PLR<91.11、FIB-4>3.25、APRI>2與丙型肝炎相關肝硬化代償期的發生有關(P值均<0.05)(表3)。

表3 慢性丙型肝炎肝硬化發生的多因素分析
2.5 RPR、PLR、FIB-4、APRI與肝纖維化嚴重程度的關系 根據肝硬度值將研究對象分為5組:F0~l(≤7.3,n=670)、F2(7.3~9.7,n=140)、F2~3 (9.7~12.4,n=61)、F3~4(12.4~17.5,n=54)、F4(>17.5,n=43)。結果顯示,對于不同纖維化嚴重程度的患者,RPR、PLR、FIB-4、APRI在組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4);隨著肝纖維化程度的加重,RPR、FIB-4和APRI均呈現逐漸升高的趨勢,PLR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Ptrend值均<0.05,圖2)。

圖2 RPR、PLR、FIB-4、APRI與肝纖維化嚴重程度的關系
3 討論
由HCV引起的慢性感染是世界范圍內肝硬化的主要病因之一,如果抗病毒治療不及時,感染15~30年后可逐步發展為肝硬化,最后導致肝癌的發生[2]。由于肝纖維化發病隱匿,大多數慢性肝病患者在肝硬化出現失代償之前是無癥狀的,因癥狀就醫時已處于失代償期[21],預后情況不容樂觀[22]。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抗HCV藥物在我國臨床應用并不廣泛,并且扶余地區的丙型肝炎高發區是農村經濟不發達地區,患者均未在感染早期給予抗病毒治療。雖然2009年在該地區實施的HCV流行病學調查和抗病毒干預后,有半數以上患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療,但由于HCV感染時間久,預計未來10~20年扶余地區HCV感染所導致的肝硬化和肝癌疾病負擔將呈不斷上升趨勢[23-24],因此有必要在該地區的HCV慢性感染的高危人群中進行肝硬化篩查,以提高肝癌的早診率,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25]。

表4 RPR、PLR與肝纖維化嚴重程度之間的關系
RDW和血小板的變化均與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慢性肝病的發展有關。肝硬化患者伴隨肝臟功能下降,會進一步影響造血原料在肝臟的儲存、代謝和合成,使骨髓造血功能紊亂,影響紅細胞的生成,導致RDW升高[26];同時,慢性肝病患者機體內存在長期的炎癥反應可能會影響鐵代謝和促紅細胞生成素的產生,導致紅細胞生成障礙[27-28];再者,肝硬化患者的脾功能亢進加速了紅細胞的破壞,促使骨髓釋放出更多的未成熟的紅細胞,引起RDW升高。血小板減少與肝硬化的發生相互促進,促血小板生成素(TPO)主要由肝臟產生,肝硬化患者的肝臟代謝和合成功能降低,影響TPO產生,從而導致血小板減少[29]。此外,血小板能夠分泌多種生長因子促進肝臟再生,如肝細胞生長因子、血小板減少進一步加重了肝臟的破壞,促進了肝硬化的發生[30]。因此,與單個指標比較,兩者的綜合指標RPR(RDW與血小板比率)升高更為顯著,可能對肝纖維化及早期肝硬化的發生和進展有更好的預測作用。最近研究[15,31]表明,RPR可能是預測肝臟晚期纖維化、肝硬化的一個有效指標,特別是在慢性乙型肝炎、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中,RPR值升高與晚期纖維化風險升高相關。本研究發現,RPR升高(>0.081)與丙型肝炎肝硬化的發生相關,RPR對于預測早期肝硬化發生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He等[32]研究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同樣也發現了RPR對于識別丙型肝炎肝硬化具有較高的預測能力。
機體的炎癥和免疫反應在慢性肝炎發展至肝硬化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PLR、NLR作為血常規中的綜合性炎癥指標,能夠反應全身炎癥反應程度,具有簡便易得的優點,被用于廣泛的評估炎癥性疾病,尤其是包括肝癌在內的惡性腫瘤患者的預后[33]。既往研究[16,32]顯示,丙型肝炎肝硬化的患者PLR顯著低于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本研究聚焦于早期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分析結果也顯示,與慢性丙型肝炎組患者相比,肝硬化代償期組患者的PLR值更低,且PLR降低是肝硬化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與Li等[34]的研究結果一致,但該研究并未給出PLR的截斷值。從機制上分析,肝硬化患者的脾功能亢進及肝炎病毒感染產生的骨髓抑制,導致了血小板數量下降和淋巴細胞的減少。而本研究發現,相對于慢性丙型肝炎組,肝硬化組血小板的下降程度比淋巴細胞更為顯著。目前關于NLR與肝纖維化進展之間的關系尚不明確。在本研究中,雖然肝硬化代償期組患者的中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數量均降低,但是NLR在2組之間卻無統計學差異,且在不同嚴重程度的肝纖維化患者中,NLR的值也沒有差別(該部分數據未顯示)。Abdel-Razik等[35]發現,在丙型肝炎患者中,與輕度纖維化(F1~2)的患者相比,晚期纖維化(F3~4)的患者中NLR值更高,提出NLR升高與肝病的不良進程相關。而一項系統綜述[18]顯示,對于慢性丙型肝炎患者,NLR可能與纖維化分期不存在相關性,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一致。
肝纖維化是從慢性肝病發展至肝硬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是病毒感染、慢性炎癥的發生后肝臟中發生的各種病理過程的結果,可以代表慢性肝炎向肝硬化演變的過程。因此,對肝纖維化的早期發現并進行嚴格的隨訪至關重要。但在早期肝硬化中,常規的影像學檢查可能導致假陰性結果[21],而非侵入性的血清學指標可以為監測纖維化的發生提供更多的信息。本研究按照肝纖維化程度將患者分成5組,結果發現,隨著纖維化進程的發展,RPR、PLR分別有隨之動態上升、下降的趨勢,因此,動態監測RPR和PLR有助于監測肝纖維化進展,以便對肝硬化進行早發現、早干預,以逆轉纖維化和穩定疾病進展,避免或延遲失代償事件的發生。
在本研究中,常規的評價肝纖維化、肝硬化的指標也與丙型肝炎肝硬化的發生相關,如白蛋白降低、FIB-4指數和APRI評分升高,與既往研究[32,34]結果一致。本研究未發現抗HCV治療對防止肝硬化發生的益處,考慮是大部分患者雖然接受過短效干擾素、長效干擾素或蛋白酶抑制劑的抗病毒治療,也達到了病毒清除(HCV RNA 陰性),但由于上述人群感染較早,治療較晚(近2~8年才開始接受抗病毒治療),因此抗病毒治療預防肝硬化發生的生物學效應尚未顯現。
本研究局限性在于為橫斷面研究,缺乏同一患者血清學指標的動態監測數據,不能確定丙型肝炎肝硬化發生與血常規中炎癥指標改變的時間先后順序,尚不能證實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僅提示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綜上所述,丙型肝炎肝炎患者年齡、RPR、FIB-4指數和APRI評分升高,白蛋白和PLR降低與丙型肝炎相關早期肝硬化發生相關。對于丙型肝炎感染者,除了監測腫瘤標志物、肝功能和肝臟影像學變化外,基于普通血常規檢測的指標RPR、PLR也是預警纖維化進展的指標,具有相對無創,依從性良好,經濟實用的優點,可用于監測丙型肝炎相關早期肝硬化的發生及肝纖維化進程,有助于實現肝硬化的早診早治,改善患者預后。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楊娜負責撰寫論文,趙天業、陶雪蓉負責整理數據,何華、吳燕華負責修改論文,姜晶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