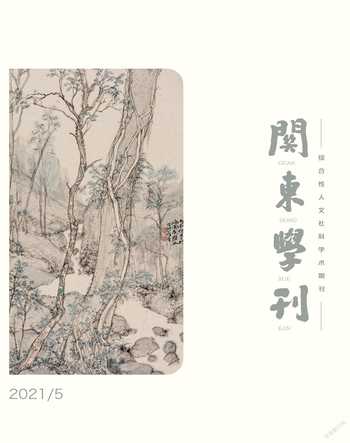東北地區城市間協同創新網絡特征分析
趙輝越 馬語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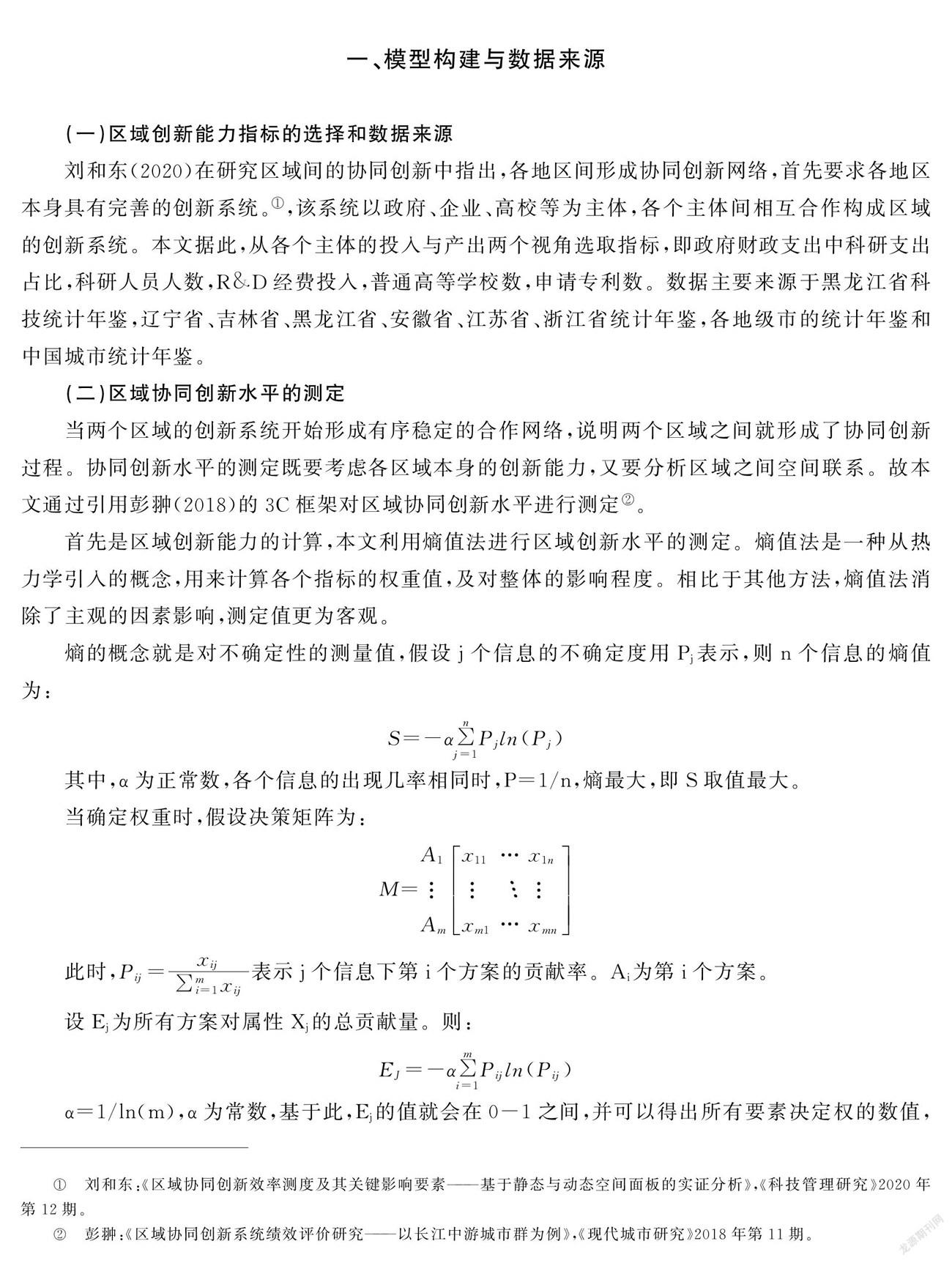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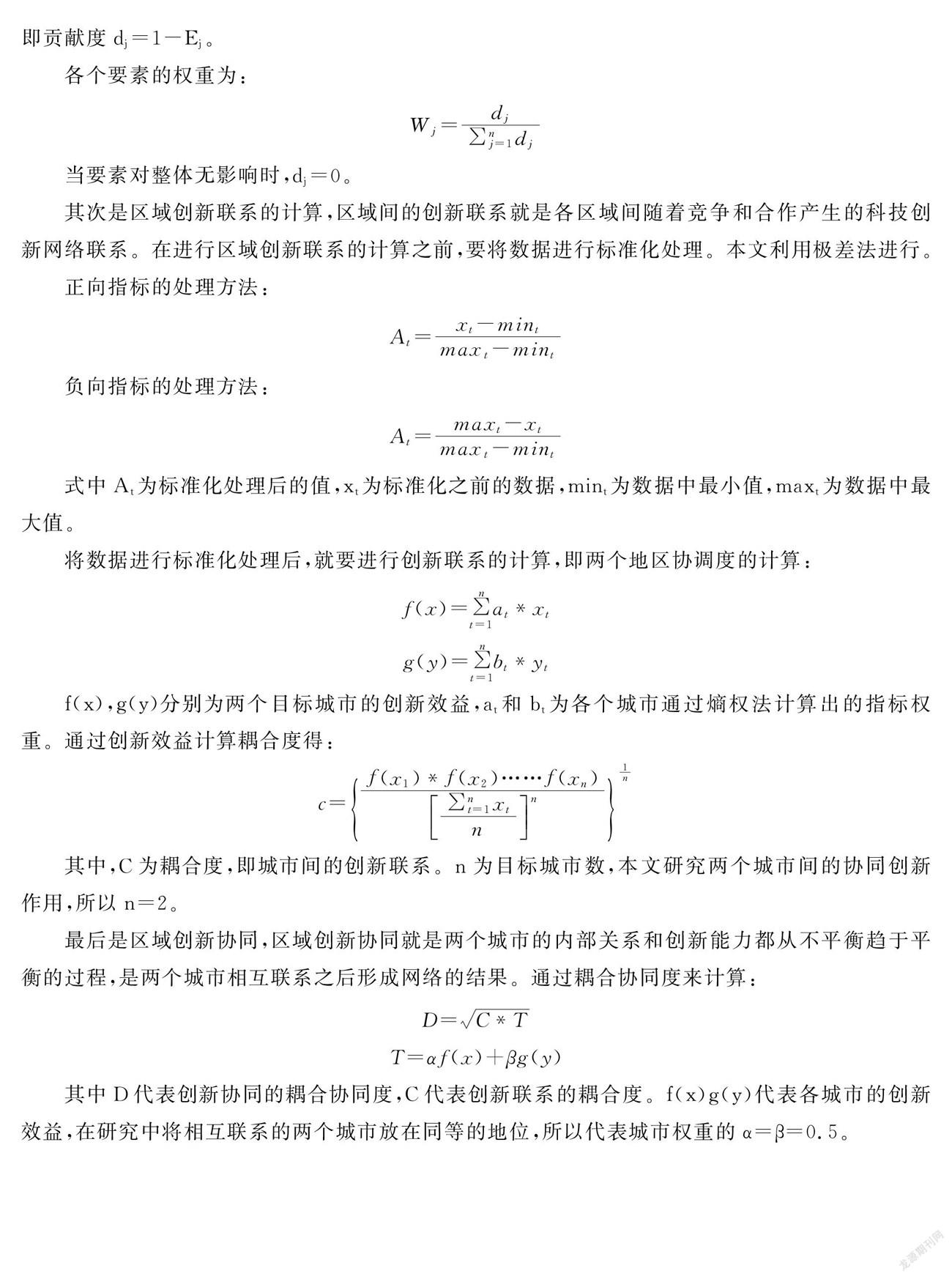

[摘 要]城市間的協同創新對一個區域的經濟韌性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作用。為分析東北地區城市間協同創新網絡的分布現狀,界定各個城市的發展地位和整個地區的創新網絡結構,在3C框架下計算各個城市的創新能力的基礎上,使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整個地區的城市間協同創新網絡強度,并與較發達的長三角地區作對比,為東北地區的協同創新發展提供理論依據。研究發現,東北地區創新動力不足、科研合作較少、副省級城市創新核心地位不突出、協同創新網絡構建的基礎設施條件差等問題導致各城市間的協同創新聯系強度不高。與長三角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為了提高東北地區協同創新的水平,要改善產學研關系,充分發揮“哈-長-沈-大”發展軸的核心作用,消除行政壁壘。
[關鍵詞]協同創新網絡;耦合協調度模型;網絡結構分析
[作者簡介]趙輝越(1976-),女,長春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馬語鍵(1998-),男,長春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長春 130012)。
一個地區和城市的穩定發展在全球經濟波動和自然危害頻發的當下尤為重要。2020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更是讓全球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在經歷過自然危害和經濟沖擊的國家或地區,有的基本抵御住了風險或者在經歷波動之后快速恢復并實現經濟的繼續增長,而有的則在沖擊和波動之后逐漸衰退[杜志威:《產業多樣化、創新與經濟韌性——基于后危機時期珠三角的實證》,《熱帶地理》2019年第2期。]。經過多年的研究,有學者總結了出現這種差別是由于各個經濟體內在結構的差別,并將其定義為經濟韌性。在此背景下,經濟韌性逐漸成了相關學科研究的重點。在過去的研究中,經濟韌性通常被解釋為面對沖擊的抵抗能力,危機過后的恢復能力[Martin R.,“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12,no.1(December 2012)pp.1-32.]。我國在2020年全球爆發疫情的一年間,成為了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這表明我國經濟韌性較強。但是經濟高質量的增長需要各個地區空間資源高效率的集聚和互補,協同創新網絡就是集聚互補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所以一個地區中城市間的協同創新網絡聯系強度對整個區域的經濟韌性的提升有重要作用[郭將:《產業相關多樣性對區域經濟韌性的影響——地區創新水平的門檻效應》,《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年第13期。]。
早在1965年Ansoff就提出了“協同”一詞,他認為協同就是多個獨立的個體為了達到同樣的目標進行資源共享而暫時形成的一個主體的過程。他還強調,個體在協同的過程中進行資源共享達到的成果要大于個體各自帶來的價值[Ansoff H I.,Corporate strategy:An analytic approach to business policy for growth and expansion,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1965,p.175.]。張志華(2019)提到創新活動的進行要不斷的突破邊界、尋求合作。協同創新就是企業跨邊界獲取資源、提高創新績效和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張志華:《戰略性新興產業協同創新網絡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實證研究》,《技術與創新管理》2019年第2期。]。趙波(2019)、陸云泉(2018)等學者在協同創新基礎上增加關系網絡的定義,他們認為協同創新網絡是參與創新的多個主體為了共同的發展目標而進行資源共享、整合,相互聯系的網絡系統。[趙波:《協同創新網絡,資源整合,主體互動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以江蘇戰略性新興產業物聯網企業為例》,《江蘇商論》2019年第7期。][陸云泉:《協同創新網絡與組織創新績效的關系》,《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劉珊珊:《協同創新網絡對協同創新績效影響機制的實證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Davis(2011)開始將地理學的知識運用到協同創新網絡中來,借助地理鄰近性理論將協同創新網絡應用到區域間的關系研究上來[Davis J P,“Rotating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Recombination Processes 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s”,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vol.56,no.2(July 2011)pp.159-201.]。王志寶(2013)將區域間協同創新分為狹義與廣義。狹義的區域間協同創新是科技創新活動在區域內合作開展,各個地區間為達到創新效益的最大化而進行科技合作以及構建科技創新平臺。廣義的區域間協同創新是更高級別的協同,區域內通過人口、環境等各個資源的協同發展以達到區域內的效益最大化。
現如今的學者在相關理論發展成熟之后,開始大量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協同創新網絡[王志寶:《區域協同創新研究進展與展望》,《軟科學》2013年第1期。]。孫天陽(2019)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對全國各地區的協同創新網絡進行研究,他將聯合申請專利量作為衡量協同創新的標準,結果發現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協同創新網絡強度同樣也高[孫天陽:《中國協同創新網絡的結構特征及格局演化研究》,《科學學研究》2019年第8期。]。同時,也不乏學者對我國長三角地區和成渝城市群的協同創新網絡進行研究[吳慧:《長三角區域產業協同創新一體化的社會網絡研究》,《華東經濟管理》2021年第1期。][呂丹:《“成渝城市群”創新網絡結構特征演化及其協同創新發展》,《中國軟科學》2020第11期。]。
城市間的協同創新網絡強度既是研究區域經濟韌性的核心問題,也是解決東北地區經濟鎖定的關鍵。所以本文分別選取東北地區與長三角地區的20個城市三個年份的城市間協同創新網絡強度進行對比,以期探究我國東北老工業地區協同創新的現狀,并為此提供針對性的建議。
一、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一)區域創新能力指標的選擇和數據來源
劉和東(2020)在研究區域間的協同創新中指出,各地區間形成協同創新網絡,首先要求各地區本身具有完善的創新系統。
[劉和東:《區域協同創新效率測度及其關鍵影響要素——基于靜態與動態空間面板的實證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20年第12期。],該系統以政府、企業、高校等為主體,各個主體間相互合作構成區域的創新系統。本文據此,從各個主體的投入與產出兩個視角選取指標,即政府財政支出中科研支出占比,科研人員人數,R&D經費投入,普通高等學校數,申請專利數。數據主要來源于黑龍江省科技統計年鑒,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安徽省、江蘇省、浙江省統計年鑒,各地級市的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二)區域協同創新水平的測定
當兩個區域的創新系統開始形成有序穩定的合作網絡,說明兩個區域之間就形成了協同創新過程。協同創新水平的測定既要考慮各區域本身的創新能力,又要分析區域之間空間聯系。
故本文通過引用彭翀(2018)的3C框架對區域協同創新水平進行測定[彭翀:《區域協同創新系統績效評價研究——以長江中游城市群為例》,《現代城市研究》2018年第11期。]。
首先是區域創新能力的計算,本文利用熵值法進行區域創新水平的測定。熵值法是一種從熱力學引入的概念,用來計算各個指標的權重值,及對整體的影響程度。相比于其他方法,熵值法消除了主觀的因素影響,測定值更為客觀。
熵的概念就是對不確定性的測量值,假設j個信息的不確定度用Pj表示,則n個信息的熵值為:
S=-α∑nj=1Pjln(Pj)
其中,α為正常數,各個信息的出現幾率相同時,P=1/n,熵最大,即S取值最大。
當確定權重時,假設決策矩陣為:
M=A1Amx11xm1 …… x1nxmn
此時,Pij=xij∑mi=1xij表示j個信息下第i個方案的貢獻率。Ai為第i個方案。
設Ej為所有方案對屬性Xj的總貢獻量。則:
EJ=-α∑mi=1Pijln(Pij)
α=1/ln(m),α為常數,基于此,Ej的值就會在0-1之間,并可以得出所有要素決定權的數值,即貢獻度dj=1-Ej。
各個要素的權重為:
Wj=dj∑nj=1dj
當要素對整體無影響時,dj=0。
其次是區域創新聯系的計算,區域間的創新聯系就是各區域間隨著競爭和合作產生的科技創新網絡聯系。在進行區域創新聯系的計算之前,要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本文利用極差法進行。
正向指標的處理方法:
At=xt-mintmaxt-mint
負向指標的處理方法:
At=maxt-xtmaxt-mint
式中A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值,xt為標準化之前的數據,mint為數據中最小值,maxt為數據中最大值。
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就要進行創新聯系的計算,即兩個地區協調度的計算:
f(x)=∑nt=1at*xt
g(y)=∑nt=1bt*yt
f(x),g(y)分別為兩個目標城市的創新效益,at和bt為各個城市通過熵權法計算出的指標權重。通過創新效益計算耦合度得:
c=f(x1)*f(x2)……f(xn)∑nt=1xtnn1n
其中,C為耦合度,即城市間的創新聯系。n為目標城市數,本文研究兩個城市間的協同創新作用,所以n=2。
最后是區域創新協同,區域創新協同就是兩個城市的內部關系和創新能力都從不平衡趨于平衡的過程,是兩個城市相互聯系之后形成網絡的結果。通過耦合協同度來計算:
D=C*TT=αf(x)+βg(y)
其中D代表創新協同的耦合協同度,C代表創新聯系的耦合度。f(x)g(y)代表各城市的創新效益,在研究中將相互聯系的兩個城市放在同等的地位,所以代表城市權重的α=β=0.5。
二、結果分析
(一)莫蘭指數結果
本文選用地理鄰接矩陣下的莫蘭指數來驗證東北地區以及長三角地區的創新能力存在空間溢出效應。
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發現東北地區的莫蘭值大多處于負值,并且都在10%以上的條件下顯著。這說明東北地區的創新能力呈空間負相關性,空間存在差異性,即創新能力強的城市在東北地區較為分散,并沒有為周邊的城市帶來足夠的創新外部性。這也意味著東北地區各城市之間的協同創新能力較弱。反觀長三角地區,莫蘭指數均大于0且都在10%以上的條件下顯著。這說明了長三角地區的創新能力成空間正相關,空間溢出效應明顯,即創新能力強的城市周邊的城市創新能力同樣比較強,存在創新能力的外部性。通過莫蘭指數的計算結果為下文分析兩個地區的協同創新做鋪墊。
(二)創新能力結果
首先是創新能力。如表2左半部分所示,為東北地區20個城市創新能力的數值,表中創新能力的數值是通過熵值法計算并取對數得到的。由表中數值可以發現,東北城市群選出的20個城市中,沈陽市的創新能力在三個年份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大連市。哈爾濱市和長春市的創新能力平均分值也同樣排在前位,但低于沈陽市和大連市。四個城市的創新能力平均分值普遍在12以上。四平市、延邊州、遼源市和綏化市創新能力較低,排在城市中的末位,創新能力平均分值在8左右。從時間角度看,各個城市在斷點的三年間創新能力都有所提高。從中可以看出,東北地區整體的創新能力有所提高,這是東北地區實行創新發展戰略帶來的結果。但是創新能力水平普遍偏低,科技成果轉化能力較弱,這仍然是整個東北地區的現狀。
東北地區城市創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東北是最早的工業基地,存在較多的大型企業,并且多數為重化工企業、資源型和傳統型企業。這些企業往往由于其壟斷地位導致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從而影響到整個城市的創新能力發展。作為創新主體的中小企業,在東北地區也很難發揮其主體作用。這是由于東北地區大型企業占主導,導致當地的中小企業主要以服務大型企業為主并提供配套服務,從而降低了其創新的動力。其次,政府的創新投入主要偏向副省級城市,這樣就會出現兩個極端:第一,除副省級城市以外的城市無論創新資源還是創新資金都會不足,導致城市的創新能力不足。第二,政府對副省級城市的過度投入會帶來過于豐富的資金和資源,再加之當地政府對高新企業的優惠政策,吸引大量企業涌入,這樣無疑會導致資源和產能過剩,創新效率低下的同時,還會帶走其他城市的資源。同時,政府會保證副省級城市高新企業的存活,使更多沒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得以生存,從而更多企業降低了創新的熱情。最后,東北地區的高校也主要集中在副省級城市,并且其他各個城市的人才吸引政策力度不夠,缺乏新鮮的創新血液注入,導致沒有較強的創新能力。
表2的右半部分,是長三角地區20個城市三個年份的創新能力。由表中的數值可以發現,上海市作為全國的金融中心,創新能力在長三角地區是最強的,其次是杭州市。除了作為省會城市的南京市和合肥市外,蘇州市、無錫市和寧波市的創新能力也較高。池州市排名最后,創新能力平均值在9左右。長三角地區的整體創新能力平均分值在11以上,處在較高的水平。從時間角度看,長三角地區三個年份中的創新能力也在逐年上升。這說明長三角地區在保持較高創新水平的同時,各個城市創新水平還在穩步提升。從此結果來看,長三角地區的創新發展戰略已經取得較大的成功。上海市、杭州市等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在整個國家城市中也是經濟較為發達、創新資源和創新投入較為雄厚的城市。無論是用于創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的政策傾斜還是創新創業環境都加速了這些城市創新能力的發展。創新發展環境不僅在當地培養了大量的優秀創新創業人才,同時大量人口資源也會不斷向當地涌入。再加上長三角的區位優勢和政府政策的傾斜,不斷吸引中小企業入駐。
通過對比表2中數據可以充分看出,東北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創新能力的不同。東北地區的四個副省級城市創新能力雖然處于領先地位,但是從表中的數據對比可以看出,東北地區副省級城市的創新能力在長三角地區中只能算在中游水平。東北地區創新發展戰略格局極為單一,“哈-長-沈-大”的發展軸覆蓋面積小,并且沒有起到龍頭作用。各個城市間創新能力發展差距大,資源分配不均。相反,長三角地區的上海市充分發揮了帶頭作用,并與其他城市連成一片,創新聯動作用覆蓋整個長三角地區,各個城市發展自身優勢產業,促進創新水平的提升。例如,浙江省利用自身的區位及經濟集群優勢建立的以油氣全產業鏈為特色的自貿試驗區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而東北地區當地的私營企業大多依附國有企業而生存,創新能力和動力都明顯不足。
(三)城市間協同創新結果分析
表3為東北地區20個城市三個年份的協同創新強度分布。聯系強度通過自然斷點法分為5個級別,一級聯系為最強,五級聯系為最弱。如結果所示,東北地區大部分城市協同創新網絡的聯系強度較弱,大部分處于三級聯系和四級聯系之間。與創新能力的分布一致,協同創新網絡的強度也呈現出以“哈-長-沈-大”發展軸為核心的分布,四大副省級城市與其他城市的聯系都比較強,尤其是四個城市之間的聯系強度一般都在一級強度。但是綏化市、延邊州等邊緣城市與其他城市聯系并不緊密。從時間上來看,整個東北地區的協同創新網絡的強度有所提升,中心城市保持較高聯系強度的同時,邊緣城市的聯系在2019年也有明顯的改善。
表4為東北地區三個年份的協同創新一級聯系強度分布。由結果可以看出,除了2012年沈陽市與大慶市的協同創新聯系強度在一級強度以外,2015年和2019年一級聯系強度都只在四個副省級城市之間。由于大慶市自然資源豐富,并且沈陽市的重工業發達,對石油等自然資源需求較大,大慶市關于自然資源的衍生產業較多,與沈陽地區的協同創新聯系自然較強。可到了2015年之后,國家限制了自然資源開采,兩個城市之間的協同創新聯系強度就降為了二級。從結果看,東北地區“哈-長-沈-大”的整體性雖然強,但是作為網絡中的核心城市,并沒有兼顧到邊緣城市。除去四個副省級城市,其余每個城市幾乎都有與其他城市存在五級強度的協同創新聯系,網絡的韌性可想而知。這三個城市與其他城市的五級聯系最多。到了2019年,結果雖然有些改善,但還是不能擺脫東北地區城市間協同創新網絡強度低的現狀。
表5為長三角地區20個城市所選三個年限中的協同創新結果分布。長三角地區整體上的協同創新網絡強度較高,普遍為一級聯系強度和二級聯系強度。長三角地區的協同創新網絡呈“一核心多中心”的分布狀態,即以上海市為核心,三個省會城市為中心與周邊其他城市構成了一個極具韌性的協同創新網絡。從時間上看,2012年,長三角地區的多中心狀態還沒有完全成型,僅僅上海市起到了核心作用。2015年,三個省會城市逐漸發揮了其地區中心的作用,與各個城市間形成較強的協同創新網絡,以上海市為主,三個省會城市為輔,寧波市等沿海城市、蘇州市等長三角中心城市一起構成了該地區的高質量的協同創新網絡,從而形成“一核心多中心”的網絡分布狀態。到了2019年,情況大有改善,邊緣城市的協同創新聯系強度顯著提高。
但是由結果可知,長三角地區也仍然存在著城市間協同創新聯系強度較低的現狀,尤其是距離上海市較遠的城市,其中以安徽省的三個城市滁州市、宣城市和池州市為主。這說明上海市的創新外部性還沒有覆蓋安徽省的大部分城市。而在2015年之后,協同創新網絡結構偏弱的城市開始有較大改善,但是安徽省的池州市與作為省會城市之間的合肥市的協同創新聯系強度仍然是五級,這說明長三角地區極具韌性的協同創新網絡中依舊存在著城市之間協同創新聯系弱的問題。
通過上述分析對比發現,東北地區相較于長三角地區的協同創新網絡分布還存在較大差距,即使東北地區近幾年的協同創新發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現實存在的制約條件仍不可忽視。
首先,東北地區的協同創新發展體系還不健全,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由于東北地區受計劃經濟影響較大,而且作為建國初期最早的工業基地,國有企業在東北地區占比較大,導致了政府對資源的主導作用比市場作用要強,這樣便缺少了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獲得一些稀缺資源的機會也就更大,更多的中小企業為了生存選擇依附于國有企業,創新對發展而言變得沒有那么必要,各個城市間的協同創新也就缺少機會。協同創新也變得寸步難行。創新作為發展的源泉被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環境、不正當競爭等所抑制,創新主體的創新動力和協同創新的意向明顯不足。
其次,創新投入要素不足,無法支撐東北地區大量創新活動和各城市間的協同創新。政府方面,東北三省政府的R&D投入均處于全國較低水平。創新意味著開發新產品,更新核心技術,發展高新企業,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科研資金的支持,資金的缺乏導致的協同創新不足會使整個地區的企業附加值低,企業多數以生產初級產品為主。創新資金的來源除了政府投入以外還需要企業自身從資本市場獲得。但是資本市場不發達也是困擾東北經濟發展的一大難題。在東北地區,融資方式主要以間接融資為主,金融機構的數量少,金融服務的質量低。東北地區銀行業主要是以政策性銀行和國有銀行為主導,導致資本市場同樣缺乏競爭,融資渠道少,效率低下。除了資本要素外,創新對人才要素的需求也同樣較高。雖然東北地區高校數量在全國各地區中排名靠前,但是畢業生數不能轉化成人才資源,而且,東北地區的人口流出還在逐年上升,加上出生率降低和老齡化加重,導致創新人才要素嚴重缺乏。
再次,產業創新能力差,集群度不高。以吉林省為例,作為老牌工業基地,吉林省在汽車和電子等行業具有競爭優勢。但是為了技術保密,在產品更新和技術研發過程中嚴重缺乏合作意識,這就導致了產業鏈短,與其相配套的上下游企業少,不具有形成規模經濟的條件。受到產業分散問題的影響,不僅產學研的合作程度不高,更影響著城市間的協同創新作用。不僅如此,產業鏈條短的問題還會使創新成果不能就地轉化,多數成果進入到其他產業類型豐富、創新成果需求更高的城市實現產業化。所以,產業結構問題也是困擾東北地區協同創新的一大因素。
最后,協同創新網絡的建立要求地區內形成一個足夠強大的創新合作體系,既要求政府、企業和高校之間加強創新合作,同時,也要有具有足夠韌性的其他網絡作為支撐。但是東北地區的其他基礎網絡也存在著諸多問題。根據東北地區鐵路交通圖分析得出,金融聯系網絡和信息關聯網絡也主要以四大副省級城市為主,并不能為整個東北地區協同創新網絡的構建提供較好的基礎。
長三角地區的協同創新網絡雖然已經富有韌性,建立了比較全面的創新資源共享平臺,但是在進一步加強協同創新網絡建設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行政壁壘依然存在。長三角地區雖然協同創新網絡強度很高,但是合作之外還有競爭,這樣的競爭無疑會導致資源和人才分配的失衡。其次,協同創新體系還有待提升。雖然政府間在許多科研活動和企業創新活動方面達成過共識,但是關于科技發展規劃,重大科研項目等方面的合作還有待提高。最后,由于各地政府的有利性和一味追求政績等問題帶來的排他性,嚴重影響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強度的提高。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比研究東北地區與長三角地區的協同創新網絡強度發現,兩個地區的創新能力和協同創新網絡強度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通過本文的分析,東北地區協同創新發展主要面臨以下問題:企業多數為政府主導,創新動力不足;東北地區城市間科研合作較少;副省級城市創新核心地位不突出;構建協同創新網絡的基礎設施條件差。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1.加強政府、企業和高校的聯系。首先,政府作為當地發展的領導者,要把握好自身干預科技市場的尺度,既不能過度干預又不能放任不管。尤其是在技術創新活動中存在市場失靈的現象,
所以需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引導和幫助。尤其是加強對相關產業發展方向的預測,加大對新技術的開發力度,努力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為留住本地科研人才、吸引外地人才,政府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為人才的生活和居住提供舒適的環境。其次,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是協同創新網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尋求多種融資渠道,建立合作共贏的科研共享平臺,加強科技成果的轉化。最后,高校要為科技創新提供技術支持和人才儲備,同時通過引進科技人才來解決重大科技攻關問題。總之,政府要加強產學研的合作創新,提供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制定有利于創新創業發展的政策,企業做好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高校建立數據更全面更有創新能力的科技創新平臺。
2.充分發揮核心城市的帶動作用,促進整個地區均衡發展。如今,東北地區“哈-長-沈-大”發展軸雖然整體性較高,但是遠不及上海在長三角地區的核心地位。所以,要建立富有韌性和強度的協同創新網絡就要加強東北地區協同創新網絡“核心-邊緣”結構建設以及加強各類要素之間的充分流動。首先,充分發揮四個副省級城市的核心作用,加強創新網絡建設,共享大型設備等創新資源、技術專利等創新成果。其次,邊緣城市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模仿增長極的發展路徑。。要解決東北地區均質化問題,就要讓邊緣城市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模式。最后,創新要素的充分流動是提高一個地區協同創新網絡強度的重要因素。建立覆蓋大部分城市的交通網絡、科技資源共享平臺、富有效率的融資平臺、完整的信息交流平臺等都是保證要素充分流動的必要因素。
3.減少城市間的行政壁壘,避免由于政績競爭導致合作不深入。城市之間合作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減少歧視,降低準入,將資金、人才和技術流動的成本降到最低。建立跨城市創新園區,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同時,東北地區不僅要在自身強勢產業上進行創新發展,也要在此基礎上推進傳統產品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發展,例如高端裝備制造、智能化汽車等。而高端智能化發展不能單純依靠東北地區自身,還要進行跨國跨地區的創新合作,建設一批國內外合作的創新產業園和產業基地。建設長吉圖開發區,以“一帶一路”和中韓自由貿易區為紐帶帶動東北地區整體合作創新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