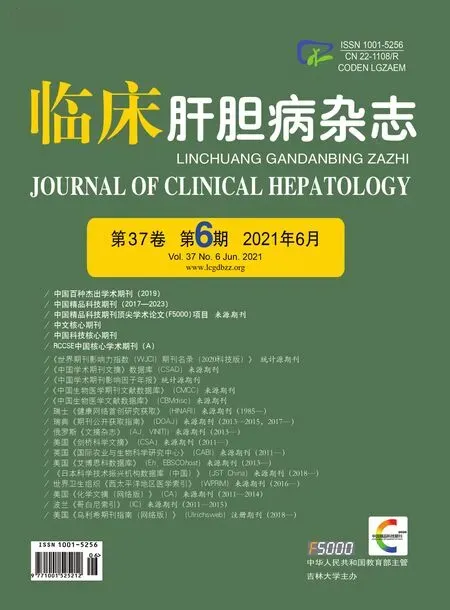ABCB4基因突變相關肝硬化誤診為Wilson病1例報告
華 磊,孫 權,許文彬,張 龍,王共強
1 安徽中醫藥大學神經病學研究所附屬醫院 神經內科,合肥 230061;2 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感染科,合肥 230031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48歲,因“檢查發現肝功能異常,肝硬化5年”于2019年8月7日入院。患者曾于2014年體檢發現“谷酰轉肽酶”異常升高,肝臟B超提示“肝硬化”,當時未訴不適,給予“護肝”治療,肝酶指標未恢復正常。患者因無明顯不適癥狀,此后未積極求診、治療。2019年7月初,患者出現鞏膜及皮膚黃染,于當地某大學附屬醫院就診,實驗室檢查提示:WBC 2.57×109/L,PLT 52×109/L;肝功能異常:TBil 67 μmol/L,DBil 33.2 μmol/L,ALT 58 U/L,AST 86 U/L,GGT 180 U/L,TP 54.8 g/L,Alb 31.1 g/L;血氨升高(123 μmol/L);凝血指標異常:凝血酶原時間19.5 s,國際標準化比值1.66,活化部分凝血酶時間51.9 s,纖維蛋白原1.6 g/L,凝血酶時間21.2 s;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指標均陰性,自身免疫性肝炎抗體陰性。腹部磁共振平掃、增強及磁共振胰膽管造影示:肝硬化,門靜脈高壓(脾大,食管胃底靜脈曲張),腹水及膽囊結石;肝細胞病理示:較符合自身免疫性肝炎(輕型)。初步診斷為自身免疫性肝炎,肝硬化失代償期。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后,肝功能各項指標無好轉,進一步檢查發現銅藍蛋白輕微減低(193 mg/L,參考值220~550 mg/L),24 h尿銅升高(218 μg/24 h,參考值<100 μg/24 h)。診斷考慮為Wilson病,被推薦至本院進一步診治。
患者入院無食欲減退、惡心、嘔吐、腹脹、黑便等表現。體檢:慢性肝病面容,雙側鞏膜及全身皮膚黃染,面、頸部見數枚蜘蛛痣,無皮膚、黏膜瘀斑及新鮮出血點,腹部平軟,未見腹壁靜脈曲張,壓痛(-),Murphy征(-),肝脾肋下未觸及,移動性濁音(-),雙下肢不腫。神經系統體檢未見異常。患者無肝炎病史及血吸蟲病史,否認藥毒物接觸史,無飲酒及吸煙史,無家族遺傳病病史。入院檢查,肝功能異常:TBA 117.7 μmol/L,TBil 63 μmol/L,DBil 38.3 μmol/L,ALT 69 U/L,AST 97 U/L,GGT 274 U/L,膽堿酯酶2251 U/L,TP 59.2 g/L,Alb 34.2 g/L,血氨72 μg/L。肝纖維化指標明顯升高:透明質酸970.22 ng/ml,Ⅳ型膠原322.52ng/ml。銅生化各項指標均正常:銅藍蛋白229.2 mg/L,銅氧化酶0.317 OD,血清銅12.52 μmol/L。兩次檢測24 h尿銅輕微升高:分別為110.43、122.98 μg/24 h;小便量為2.47 L、2.61 L。裂隙燈檢查示角膜K-F環(-)。腹部彩超結果提示:肝硬化,膽囊炎,膽囊結石,脾大,腹水陰性。患者以肝硬化失代償期表現為主,初步診斷為肝硬化失代償期(Child-Pugh B級),病因診斷考慮遺傳代謝性疾病。患者無遺傳性疾病家族史,復查銅生化結果正常,角膜K-F環(-),僅24 h尿銅輕度升高,因此Wilson病診斷證據不足。治療上暫時給予“護肝、改善膽紅素循環、降血氨”等,待明確病因診斷后,進一步針對病因治療。對癥治療10余天后,患者黃疸加深,復查肝功能結果提示膽汁淤積加重并出現“膽酶分離”傾向(TBA 338.2 μmol/L,TBil 65.7 μmol/L,DBil 43.4 μmol/L,ALT 40 U/L,AST 62 U/L,GGT 207 U/L,TP 55.7 g/L,Alb 32.0 g/L)。與患者及其親屬溝通并取得知情同意后,行肝硬化相關遺傳代謝性疾病基因篩查。結果顯示:ABCB4基因第6號外顯子雜合突變(圖1),ATP7B基因無突變。最終明確診斷為ABCB4基因突變相關肝膽病所致肝硬化。給予熊去氧膽酸治療,患者病情仍進行性加重,2個月后患者出現大量胸腹水,擬進一步行肝移植治療。

注:c.430C>T∶p.R144*,編碼區第 430 號核苷酸由胞嘧啶變異為胸腺嘧啶,導致第 144 號氨基酸由精氨酸變異為終止,為無義突變。
2 討論
ABCB4(ATP-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B, member 4)基因位于人類第7號染色體長臂(7q21.1),分布于肝細胞毛細膽管膜,編碼MDR3蛋白,MDR3蛋白可以將磷脂從毛細膽管膜雙分子層內側轉運到外側,與膽汁酸鹽和膽固醇形成混合微粒,增強膽固醇的溶解,在正常膽汁排泄中起重要作用。當ABCB4基因突變時,MDR3蛋白表達減少,膽汁中磷脂減少,膽固醇溶解降低,形成結晶析出[1]。另外,由于膽汁中磷脂減少,導致肝細胞和膽管細胞長期暴露于膽鹽毒性作用下而產生持續性炎癥和纖維增生,從而導致纖維化[2]。ABCB4基因突變形式多變,可引起進行性家族性肝內膽汁淤積癥3型、低磷脂相關性膽石癥、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慢性膽管病和成人膽汁纖維化/肝硬化等疾病[3]。約34%不明原因的成人膽汁淤積患者檢測到ABCB4雜合突變,并可導致明顯肝纖維化,但大部分患者無膽道癥狀[4]。早期使用熊去氧膽酸治療可改善膽汁淤積并延緩纖維化進程,改善預后[5]。
Wilson病為ATP7B基因突變所致的銅代謝障礙性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疾病,以肝臟、神經系統等器官組織受累為主。ABCB4基因突變相關疾病及Wilson病均是遺傳代謝性疾病導致肝硬化的重要病因。ABCB4基因突變引起銅過載及肝硬化誤診為Wilson病的病例鮮有報道。Shneider等[6]報道了1例2歲女性兒童肝硬化患者誤診為Wilson病的病例,患者銅藍蛋白為28 mg/dl,肝臟銅含量高達248 mg/g干重,起初診斷考慮為Wilson病,基因檢測確定系ABCB4突變所致膽汁淤積性肝硬化,另外該患者對熊去氧膽酸治療反應良好也印證該病診斷。
健康人中,銅離子主要經過膽道排泄,銅藍蛋白系銅離子排泄運載體,在Wilson病患者中,ATP7B基因突變引起銅藍蛋白表達顯著減少,導致銅離子經膽道排泄明顯減少,進而肝臟中淤積的銅離子大量增加,經尿液排泄銅離子亦顯著增多[7]。肝臟中銅及銅關聯蛋白積聚現象在膽汁淤積性慢性肝病中可以出現[8]。27%~54%成人不明原因膽汁淤積患者中,存在已知的基因突變[9],ABCB4突變相關疾病主要導致膽汁淤積,膽鹽排泄不暢,因此可以引起肝臟及尿銅含量升高。
本例患者早期僅表現轉氨酶指標異常,影像學提示肝硬化,無明顯膽汁淤積癥狀表現,待出現明顯黃疸時,檢查發現銅藍蛋白減低,24 h尿銅增高,因此被誤診為Wilson病。起初膽汁淤積未引起重視,治療過程中TBA快速上升,提示膽汁淤積加重,但由膽汁淤積引起銅代謝障礙在臨床中極少被觀察到,相關疾病很少引起臨床醫師重視,因而容易導致ABCB4突變相關疾病與Wilson病誤診。由此可見,依據銅超載相關指標,如根據肝銅質量增加,尿銅含量增加等條件診斷Wilson病存在誤診的可能。臨床工作中,對于不明原因的肝臟病變,若銅藍蛋白和/或銅氧化酶減低,24 h尿銅升高,則多提示為Wilson病。伴有神經系統錐體外系癥狀,角膜K-F環,相關家族史以及ATP7B基因檢測等可為明確診斷提供更充分的依據。排除Wilson病診斷后,需考慮膽汁淤積性肝病的可能,排除常見的膽汁淤積病因(如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藥物性肝損傷、酒精性肝病等)后,可進一步進行相關基因篩查,需重點關注ABCB4基因突變相關疾病,有助于明確病因診斷[10]。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華磊負責資料收集、分析及撰寫論文;孫權、許文彬、張龍參與收集資料,提供意見及修改論文;王共強負責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