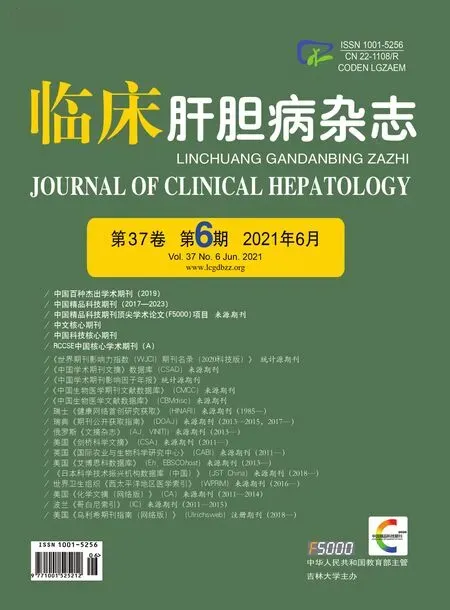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臨床特征、診斷與治療
徐 凱,吳傳玲,尹鳳嬌,李文登,胡 旺,劉處處,王海久,王志鑫
1 青海大學附屬醫院 肝膽胰外科,西寧 810001;2 浙江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鑒湖學院醫學教研室,浙江 紹興 312000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utoimmune pancreatitis, AIP)是以梗阻性黃疸為主要癥狀,胰腺淋巴細胞及漿細胞浸潤并發生纖維化,對激素治療有明顯療效的一類較為少見的慢性胰腺炎[1]。1961年首次由Sarles等[2]報道,1995年Yoshida等[3]正式將其命名為“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近年來發現IgG4相關疾病(immunoglobulin G4-related disease, IgG4-RD)幾乎全身所有部位均可受累,且證實AIP與IgG4陽性細胞關系密切[4]。國際胰腺病學會[5]于2011年明確提出AIP分為1型淋巴漿細胞硬化性胰腺炎(lymphoplasmacytic sclerosing pancreatitis, LPSP)和2型特發性管周胰腺炎(idiopathic duct centric pancreatitis, IDCP)。目前AIP發病機制不明,被認為可能與遺傳、感染、免疫等多因素有關[6]。
1 AIP的臨床特征
1.1 臨床表現 AIP無明顯特異性表現,以梗阻性黃疸較為多見,可伴有輕度上腹部疼痛,部分患者可出現新發的2型糖尿病及體質量減輕。LPSP主要好發于老年男性,男女患病率約為3∶1,平均64歲[7];除累及胰腺外,還可累及膽管、淚腺、涎腺、腎臟等多個器官組織,可出現膽道狹窄、硬化性膽管炎、干燥綜合征等[8]。IDCP發病年齡較低[9],無明顯性別差異及胰腺外表現,但更易出現腹痛及急性胰腺炎表現[10]。AIP與胰腺癌發病年齡、臨床表現的鑒別有一定重合,尤其是局灶性的AIP與胰腺癌難以鑒別,因此導致部分AIP患者因誤診為惡性腫瘤而行手術治療。
1.2 病理表現 LPSP以導管周圍淋巴細胞漿細胞顯著浸潤、胰腺實質旋渦狀或席紋狀纖維化以及閉塞性靜脈炎為特點,可見大量IgG4陽性細胞[>10個/高倍鏡視野(HPF)],并且免疫組化顯示存在大量IgG4陽性細胞浸潤[11-12]。IDCP是一種特發性胰腺炎,侵犯胰管及小葉[13],導管上皮和管腔中的中性粒細胞浸潤是特征組織學改變[14],進而導致導管破壞和閉塞,內可見少量IgG4陽性細胞(≤10個/HPF),免疫組化結果顯示IgG4陰性[15]。目前,病理學檢查依然是診斷AIP的“金標準”[16],具有準確率高的特點,但是操作也較為復雜。經超聲或CT等影像學引導經皮穿刺獲取胰腺組織,操作難度大,風險高,而鑒于席紋狀纖維化呈片狀分布,因此穿刺獲取胰腺組織可能會影響標本結構的完整性,導致AIP無法被檢出。
1.3 影像學表現
1.3.1 超聲檢查 超聲檢查具有無創、低廉、操作簡便等優點,在臨床上應用廣泛。AIP超聲表現為胰腺彌漫性腫大,呈“臘腸樣”典型征象。AIP的腹部超聲主要可分為彌漫型、節段型和局灶型[17]。彌漫型可見胰腺被膜不光滑,呈彌漫性腫大,回聲呈不均勻減低;局灶型多表現為胰頭局限性低回聲,病灶短徑/長徑≥0.5;節段型表現為胰尾體節段性腫大,伴回聲減低[17-18]。但總體而言,超聲檢查由于缺乏特異性,極易誤診為胰頭癌,因此目前只作為AIP的初篩檢查方法,無法進行定性分析。
1.3.2 超聲內鏡(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 EUS能夠觀測到胰腺實質、胰膽管的相關情況,適宜對胰腺內的病變血管作出評價,因此可通過EUS引導下穿刺活檢,排除胰腺惡性腫瘤,協助AIP診療。AIP典型的EUS以低回聲為主,內部可有點狀高回聲局部腫塊[19]。Palazzo等[20]在有關研究中指出EUS下可觀察到AIP主胰管不規則狹窄,呈現塌陷和正常交替的階段性改變,同時可見管壁增厚,高、低回聲增厚分別多見于1、2型AIP。可見EUS還能為AIP分型提供依據。
1.3.3 CT檢查 CT主要表現為:(1)胰腺呈現彌漫性腫大或局部腫大,呈“臘腸樣”外觀,胰周包殼、胰管貫穿等征象[21];(2)CT平掃成均勻等密度影,增強后呈較為均勻點片狀、漸進性強化,掃描動脈期強化程度減低,門靜脈期及延遲期逐漸均勻強化,與周圍胰腺實質呈等密度,邊緣未見強化[22];(3)病變部位胰管不規則狹窄,肝內膽管狹窄,狹窄部位以上膽管擴張;(4)AIP患者有假包膜形成,胰腺周圍環繞的包膜樣結構,平掃呈低密度,增強后輕度強化,但明顯低于胰腺密度[23]。張斌斌等[24]在調查中認為CT不僅能夠用于AIP診斷,還能用于評估AIP治療后的療效,激素治療后CT顯示胰腺呈進行性縮小或胰腺實質萎縮。
1.3.4 MRI檢查 包膜樣結構形成及膽胰管的改變是AIP特征性變化,MRI呈現為T1WI低信號,T2WI信號略高,增強后可見病灶強化程度降低,門靜脈期和延遲期呈漸進性不規則強化,出現延遲強化;由于炎癥滲出及纖維化形成,包膜結構增強后可見輕度強化,但均低于胰腺實質,包膜結構在增強后更易顯示[23]。AIP病灶在擴散加權成像圖像上表現為高信號,但表觀擴散系數呈較低信號[21]。2種方法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檢出AIP,但MRI檢查較比CT檢查而言,對AIP特征性表現具有更明顯的優勢。
1.3.5 PET/CT檢查 PET可反映病變器官的代謝情況,目前18氟-脫氧葡萄糖 (18F-fluorodeoxyglucose,18F-FDG)PET/CT在AIP中的應用報道較少,PET-CT能較全面地評價胰腺及胰外組織器官的病變程度。AIP的PET/CT為密度均勻、彌漫性腫大、輪廓平直的“臘腸樣”外觀,囊變、壞死少見[25];特征性表現為胰腺組織彌漫性或局灶性FDG攝取升高[26],可在一定程度上與胰腺癌相鑒別。此外,PET-CT可被應用于類固醇激素治療AIP的效果評價,治療后胰腺病變組織攝取程度較治療前顯著降低。
1.4 血清學表現 AIP患者血清學可伴有多種自身抗體陽性,但測定IgG4水平仍是LPSP血清學診斷標準。當血清中IgG4以135 mg/dl為臨界值時,其敏感度為65%,特異度為98%[27],應高度懷疑AIP。LPSP存在大量IgG4陽性細胞浸潤,而IDCP無明顯血清學自身免疫學標志物,因此IgG也可用于AIP的分型。Minaga等[28]研究表明,IFNα和IL-33水平在LPSP/IgG4-RD患者中呈正相關。這或許可為診斷AIP提供新的血清學檢測項目。但需要注意的是,胰腺癌往往也會引起IgG4升高,需結合血清CA19-9對二者進行鑒別。若激素治療后血清IgG4升高,則對AIP復發具有一定預測性[29]。
2 AIP診斷及鑒別
2.1 診斷標準 世界多地相繼提出結合當地的AIP診斷標準,但由于缺乏統一標準,可比性受到質疑。國際胰腺協會于2011年提出AIP國際共識[1],文中指出根據胰腺實質影像、胰管影像、血清學、胰腺外其他器官病變、組織病理表現及激素治療等6個方面確立分級標準(附錄1~2)。
2.2 鑒別診斷
2.2.1 胰腺癌 AIP近年來逐漸被臨床醫師所熟知,但仍屬于少見病[30]。誤診為胰腺癌可能會導致患者預后不佳,尤其是局灶型AIP與胰腺癌難以鑒別[31]。影像學顯示胰頭占位,胰腺彌漫性腫大,加之患者出現黃疸、體質量減輕等臨床癥狀,極易誤診為胰腺癌。CA19-9為胰腺癌特異性指標,但其在AIP中也可檢測到升高[32]。目前臨床上將血清IgG4>2×ULN作為參考,可明顯提高AIP診斷;CA19-9>100 U/ml可作為胰腺癌與AIP的參考指標[33]。聯合CA19-9與各項輔助檢查有利于減少誤診率,大大提高患者預后。
2.2.2 胰腺導管內乳頭狀黏液性腫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 IPMN) IPMN是一種胰腺囊性疾病,無明顯特異性臨床表現。當出現癥狀時,常以腹痛及黃疸為首發癥狀就診,部分患者可伴有腰背疼痛、脂肪瀉及新發糖尿病[34]。超過85%胰腺導管腺癌患者CA19-9高于正常[35]。IPMN典型影像學表現為主胰管和/或分支胰管不同程度擴張,囊性病變內有或無實性成分,磁共振胰膽管造影能較好地顯示胰腺導管交通,是IPMN的首選檢查[36]。
3 AIP治療
3.1 內科治療
3.1.1 激素療法 由于AIP的發病率低,目前尚無大規模的臨床研究能夠證實激素療法的有效性。2017年AIP治療國際共識[37]中強烈推薦對于所有未經治療的活動期AIP患者,除非有激素禁忌證,否則激素是誘導緩解的一線藥物。激素不僅能夠改善胰腺本身病變,同時也能解除膽道梗阻,減輕黃疸等癥狀,胰腺外受累臟器亦會明顯好轉,因此激素被認為是AIP的首選治療方案。梅奧醫學中心建議激素起始劑量為40 mg/d(4周),7周內減至5 mg/d,11周后停藥[32],但復發率較高。2013年日本專家共識[38]建議無激素治療副作用情況下,潑尼松維持量5.0~7.5 mg/d,持續治療3年,可降低AIP復發率。我國目前尚無對激素治療AIP明確規定。
3.1.2 免疫抑制劑及生物制劑 糖皮質激素治療AIP效果明顯,但復發率高,免疫抑制劑的使用可大大降低AIP的復發率[39]。目前臨床上硫唑嘌呤是最常用的免疫抑制劑,有學者[40]建議將其作為糖皮質激素治療后AIP的維持治療方案,并證實硫唑嘌呤能夠預防AIP疾病復發,安全有效。研究[41]證實,甲氨蝶呤對于LPSP同樣具有較好療效。Hart等[42]對116例LPSP患者采取利妥昔單抗治療,結果顯示約83%的患者完全緩解,并且在維持治療期間未見復發跡象。
3.2 外科治療 對于已明確診斷為AIP的患者應首選激素治療而并非外科手術治療。但局灶型AIP與胰腺癌鑒別困難,外科手術探查可明確診斷及達到治療目的[43]。出現以下情況時需及時手術治療:(1)梗阻情況嚴重;(2)對激素及免疫抑制劑治療不敏感;(3)拒絕接受激素及免疫抑制劑治療;(4)對激素治療有禁忌證;(5)持續不緩解的重度黃疸[8]。雖然外科治療AIP效果肯定,也有效降低了胰腺癌的漏診率,但手術難度大,風險高,并發癥較多,因此并不作為首選治療方式。
3.3 內鏡介入治療 目前尚無大規模臨床試驗證明內鏡介入治療AIP的有效性,但重癥黃疸患者可考慮行經內鏡逆行胰膽管造影術膽管引流減輕黃疸。對于輕型無感染癥狀的患者,單用糖皮質激素可有效緩解繼發于AIP的梗阻性黃疸[44]。有學者[45]發現,梗阻性黃疸的AIP患者在激素治療期間可行內鏡膽道支架置入術,以防止膽道感染引起的膽汁淤積及激素不良反應,且激素治療1個月后可安全取出支架。然而內鏡介入治療極大地增加了醫療成本及風險,仍需進一步確認其應用指征。
4 小結
綜上所述,AIP屬于自身免疫系統性疾病,發病率較低,臨床癥狀不典型。國際上雖已有多篇專家共識,但相關的輔助檢查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與胰腺癌相混淆,誤診率相對較高,因此臨床診斷過程中需要聯合多種檢查加以鑒別。組織病理學是AIP診斷的金標準,但操作難度相對較大。雖AIP血清學IgG4水平升高,但部分良惡性疾病也可出現,故依舊不具備疾病的特異性,尋找具有特異性的血清學標志物和無創的影像學方法成為今后的努力方向。相關因素的研究有助于研發治療AIP的新型靶向藥物,減少停藥后復發及藥物副作用,具有較好應用前景。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徐凱、吳傳玲負責設計文獻思路及撰寫論文;李文登、胡旺、尹鳳嬌參與數據收集,修改論文;劉處處負責參考文獻校對;王志鑫、王海久負責審核及查對。

附錄1~2見二維碼